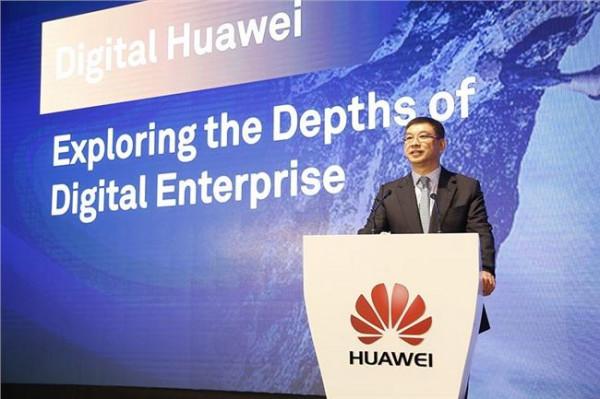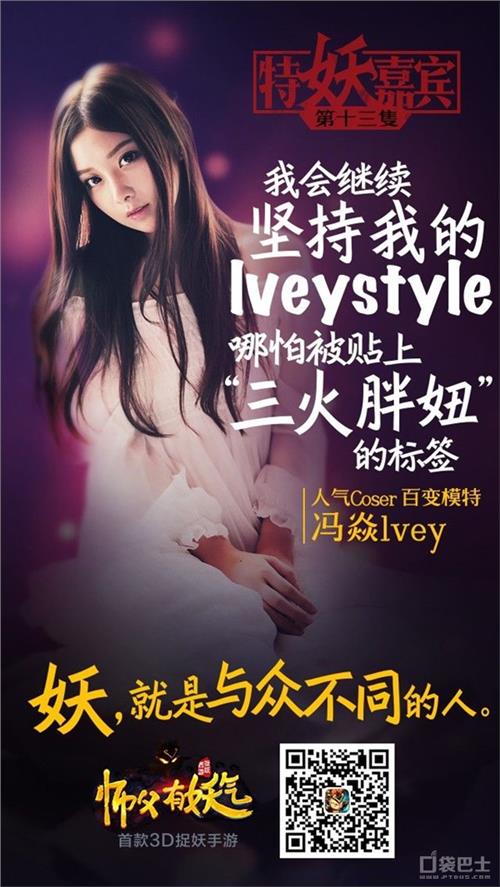电工冯焱 电工小子与漂亮女工的暧昧往事
我第一次随师傅进停电现场时既好奇又莽撞,一副对什么也不在乎的大大咧咧的样子,师傅很不放心,他在告诉我介质试验器、直流试验器等的功能的同时,还不忘一遍遍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在场地里乱走乱动,要听从指挥,按照刚考过的《安规》上的要求去做,不能出偏差……在他眼里,我哪里是一个合格的电力工人,分明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么!
刚开始,师傅只是让我干一些举杆、结线的简单活计,不让我操作,特别是一些大停电,他更是一边忙干活,还一边不忘监督我,生怕我给他惹什么麻烦,时间久了,我心浮气躁起来,原本干得津津有味的举杆、结线慢慢竟变得枯燥难挨起来,有一天我找师傅,说为什么总让我干这狗叼大饼子都能干的活计时,师傅笑了:你想操作?谁敢让你操作呀,神经兮兮的,出了事谁负责?你还是先把你那在变压器上做诗的毛病改了再说吧……我无言以对。
师傅常说我: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呀,干嘛总爱钻牛角尖,总爱在大家都忙的要死的时候却有闲情雅致吟诗作赋呀?最气人的是一次在变电所试验主变,我站在高高的变压器台上,刚结完线,放眼广袤原野,心情无比畅亮,不禁放声高歌,歌声那个抒情呀,连原本想制止的师兄也忍住了,偏偏总工这时候进入现场,看到这一幕双眉紧皱,他告诉所长:你把那小子给我叫下来!
我听说总工找我,以为有什么好事,乐得屁颠屁颠地跑去,没成想迎头一顿棒喝:你是工人还是歌星呀?要唱到歌厅去唱,谁告诉你停电作业时可以唱歌了?我高亢的情绪一下子萎缩了,嗫嚅道:我女朋友刚和我吹了,心里难受,喊两嗓子发泄一下,没别的意思……那你也不能到变压器台上去发泄呀?真要把你电着怎么办?这可不是儿戏呀!
总工依然严厉,但厚重的镜片后似乎有笑意闪烁,我挠了挠头,知道自己闯祸了。
还有一次为了提前送电,大家都在赶时间试验,我还是不紧不慢,干着干着就停了下来,冲着介质试验器发楞,师傅断喝:小子,不干活你在那儿瞎琢磨啥呢?我说在研究介损测试的原理,怎么总也想不明白呢?师傅气得直摇头:咱能不能干完活再想呀,你怎么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呀?我哦了一声,依然一脸惘然地慢条斯理地干着,师傅恨铁不成钢地瞪我,可是心里知道他没办法改变我。
要是赶上邻班那个漂亮的女记录员一起干活时,我可就来精神了,又是秧歌又是戏的,拼命的想让她注意我,可那该死的丫头似乎最烦的就是我,每次我找借口和她接近时,她总是不耐烦地皱眉,用眼角的余光打发我,三言两语惜时如金,不肯和我多说一句,我气的背后叫她“贼能装”,咒她这辈子嫁不出去,当然潜台词我没好意思说,嫁不出去给我留着岂不是好?但说心里话,“贼能装”虽然有些刻板,长得真是没说的,有一次我看到她脱下工装换上连衣裙的样子,眼睛都直了,灵感一下子就来了,感觉满场地都是诗,师兄在一旁笑我:又犯病了。
那时候好象她们班的班长也在追求她,有事没事总在她身前身后转,象条狗似的,看着我就来气,不过那小子年年是先进,业务又是“大拿”,长的也挺带劲儿,哪象我二等残废还是个落后分子,跟他简直没资格竞争。
有一次我厚着脸皮请“贼能装”去看电影,她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抽了:看你这个人挺爱下围棋的,也挺能钻研,啥时把这股劲用到工作上成为电力专家再请我吧!
说完一步三摇无比高贵地走了,我站在那儿连气带羞一口气骂了十几遍女子小人小人女子之类的脏话。 有一次我又看到她小鸟依人样跟在她们班长后面去干活,我心里恨道:你瞧不起小爷,小爷也让你知道一下厉害。我跑到附近的小卖店,往变电所值班室打电话,说找她,等她拿起电话后,我便拿腔做调说是她家的邻居,她父亲刚才突然得了急病,让她赶紧到医院去,她问是哪家医院,我胡乱编了一个,等我哼着小曲回到变电所时,看到“贼能装””正红着眼睛往外跑,我憋住笑,心说:这回看你还装不装? 下午,“贼能装”一脸气愤地把我喊了出去:上午的电话是你打的吧?什么电话?我装傻充楞。
你还不承认?我们班的人在小卖部都看到你了。哎,你可别胡说呀?你看到了是怎么着,人身攻击呀?“贼能装”看我那一脸无赖样,鼻子都要气歪了:瞧你那损样,呸,真让人恶心。
她恨恨地转身跑了,我盯着她的背影一脸坏笑:恶心?好,小爷我就好好恶心你一次。 机会还真来了,春检最忙时,我们都在停电现场吃饭,送饭车来后,大家便排着队领自己那一份,我看到“贼能装”领完饭后跟班里的女伴交代了一句什么就往卫生间去了,我偷偷凑过去,把在场地里捉的一条活蚯蚓悄悄地塞进了她的装菜的饭盒里,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躲到一边吃饭,眼睛却描着那边等着看好戏。
“贼能装”回来后和女伴说笑了一句就端起饭盒:今天吃什么呀?肉炒青椒?哟,怎么这块肉还会动呀?哎呀妈呀,这是什么呀?她突然大惊失色,一盒菜全倒在了地上。
女伴急忙过来一看,那条可能被菜香熏兴奋的蚯蚓正起劲地在饭盒里蠕动着,看着真让人作呕。这是谁呀?谁这么缺德呀!两个涨红了脸的女孩子大呼小叫着,我则吃饱喝足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找人下棋去了。 其实,电力试验工作既冗长又乏味,当时不知谁编的:高压一分钟,继电磨洋工。
意思是高压实验很快就能完成,而继电工作则要干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整天,我在高压,“贼能装”在继电,虽然我们早就干完了,可是还得等继电干完后送上电才能走,有时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闲寂难忍,有一天我就把自己平时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编了个顺口溜:一种人是韩晓颖,舞舞扎扎爱整景;韩晓颖是“贼能装”班的技术员,平时看到领导就兴奋,特别会来事儿,我一看到她大脑就缺氧。
二种人是王志合,傻了吧叽净干活。王志合那时是我们班新分来的电校生,农村孩子,整天也不说话,闷着头就知道干活。刚来我班班长介绍他时,我噗哧一声憋不住笑了,他爹妈是咋想的呀,怎么给孩子取了个臭豆腐名呀,王致和臭豆腐,多有名呀,他爹妈不会不知道吧,我后来一直就叫他臭豆腐,老伙计脾气好,也不生气,不过跟他在一起干活我最头疼,没累死先闷死了。
三种人是“贼能装”,一年也看不到一次笑模样。
当然,她可能是因为烦我才在我面前不笑的,估计在她们班长面前没少“千金一笑“,我一想到这些就有些闹心。 有一次停电试验我们班的发电机坏了,班长问谁去到继电班借,我自告奋勇,一溜小跑上继电,其实哪是光为工作呀,还想借机和“贼能装”接近一下,套套近乎,备不住还能看到她回眸一笑呢!
“贼能装”见我来了,一脸的高深莫测,她和韩晓颖扭过头不知在嘀咕什么,我有些心虚,毕竟她和我是“苦大仇深”呀,就在我担心她能否不计前嫌、网开一面时,没想到她们竟爽快地答应了,我大喜过望,深感自己过于小肚鸡肠,以小人之心度人家君子之腹,那一时我甚至觉得“贼能装”的思想境界就是比我高,和她相比,我还真有点不是东西了。
可是等我哼着小曲把发电机弄回班后却傻眼了,这在人家继电班嗡嗡叫的欢实家伙,到我们班后,却象死猪似的怎么也发动不着,师兄说你是不是借了个坏的呀?我一头大汗说不会不会,心里却暗暗嘀咕:贼能装呀贼能装,你这个死丫头该不会是在这种节骨眼上故意让我出丑吧。
这时候恰巧“贼能装”路过,见我撅着屁股在忙着发电,故意上前说怎么了?这么大个诗人连小小发电机也打不着,不会吧?我哪有心情和她磨牙呀,大家都等着发电工作呢!谁知这可恨的小女子还不依不饶:记得我们可敬的大诗人还编过什么几种人吧?我看呀,应该加上一句,四种人是臭诗人,一到干活就没精神!
大家在一旁都憋不住笑,我又羞又恼,突然一转身向值班室房后跑去,大家一时都楞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贼能装”有些慌了,也跟了过去,一看竟楞住了,在无人的房后,屈辱的泪水一下子从我眼里涌出,我竟象个委屈的孩子哭了。
这下子,“贼能装”反而笑了:哟,你还是个男子汉呢,瞧你那没出息样儿,也算个爷们?她回头见无人,突然把一条飘逸着清香的花手帕塞到我手里,然后狠狠地瞪我一眼:你就出息吧你…… 后来师兄告诉我,其实韩晓颖她俩只是偷偷把发电机下面的合风给关了,他早就发现,只是没说,想看看我的笑话,觉得怪有意思的。
啊!我瞪着牛大的眼睛,才知道我这总爱捉弄别人的人也有被人捉弄的时候啊。 那年底单位搞联欢会,所长让我和“贼能装”表演一个男女声二重唱,我是没问题,在变压器台上都敢唱,还怕到舞台上去唱?“贼能装”就犯难了,别看她长的漂亮,嗓子还真就不怎么样,我以为她会推辞,谁知她看看我竟答应下来。
排练过程很“痛苦”,我常常要为纠正她的唱腔而苦恼,她们班长献殷勤说自己有个同学在市文化馆,要不要找来给指导一下,我在一旁清了清嗓子,“贼能装”看了看我,就婉拒了。
联欢会上,我们俩合唱的是一首《青春的岁月象条河》,还别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她还真唱的有滋有味,所长和总工在下边摇头晃脑看的挺满意,总工还问所长:那小伙子叫什么?唱的真不错呀!
所长说您忘了,您还训过他呢,就是那个曾在变压器台上唱歌的小子呀!总工哦了一声说怪不得呢。 青春的岁月真的象条河,不知不觉就流过去了,许多年后,已离开调试岗位的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回到试验场地,看到了一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贼能装”已经是机电班长了,她的丈夫,原来的班长已升任所长了,见到我,她很高兴,对班里人说,别看这小子现在人模狗样的,想当年比谁都坏,我们俩还是死对头呢!
我说恨我当年没有追到你,否则你今天就不会这样说了,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呀!她笑着抬手欲打我,你这个坏小子,一张臭嘴还不改。 离开时,我看到场地里一群群和我们当年一样的年轻人在忙碌着,工作着,看到那些熟悉的仪器和设备,一种甜甜酸酸的东西在漫上来;看到“贼能装”还在指挥着试验场地的工作,我的眼前就又浮动起那个时候的我们,风华正茂、血气方钢,有多少个青春的日子我们把它交给了输电网,交给了停电现场,我们在风雨中抢修过设备,在严寒里坚守过落寞,在休憩的工余吹过牛、吵过架甚至动过手,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青春流逝了,记忆中,却还固执地保留着钢铁的痕迹,我紧盯着“贼能装”和她的工友们,我想对她说,即使如此,我也无悔呀,我想到我们在那年的联欢会上合唱的那首歌: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一支难忘的歌,一支深情的歌,痛苦和欢乐是那么多、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