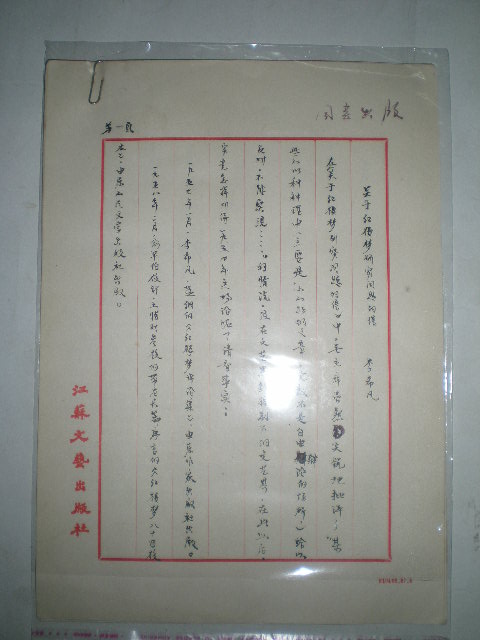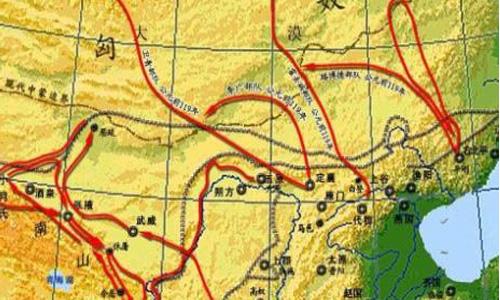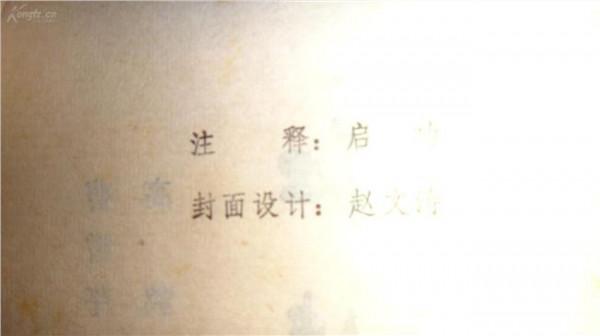李希凡的女儿 李希凡 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
贫寒少年爱好上马克思主义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
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务后就在书架旁逡巡,马列选集、鲁迅小说、苏联文学,开始了他的启蒙。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
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变化……“小人物”打响“可贵的第一枪”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
这个转折,既是李希凡本人的脱颖而出,也牵扯出5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轮文化批判,涉及了更多人命运的变故。那年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接下来的事情实属预料之外了。首先,毛泽东看到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压制革命力量”(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了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其个人功名而言,开始了风光得意的航程:1954年当年,李希凡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偶像的烦恼也总还是幸福的烦恼。
当年李希凡和蓝翎遭到的追捧也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普遍认为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就将“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林希翎”,定为自己的笔名。
而据李希凡说,他两年前为编“艺术史”申请经费,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慷慨地答应,笑说,自己当年可是李的“粉丝”。不听江青的话“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
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革命不息战斗不止。
多年来,李希凡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不仅对各时期的重要文艺作品,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等发表评论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历次的问题论争中来,比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批“鬼戏”、哲学上批杨献珍“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晖,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这位大人物的夫人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
“一个小人物”,在大人物们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阴影里,左右不是,诚惶诚恐。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
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
”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李希凡又红又正的地位罩上了阴影。
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毛主席啊毛主席如今,年近80的李希凡对“左”、“僵化”这样的标签,已无意反驳;但在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他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
李希凡称自己: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
‘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
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
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
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摘自《现代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