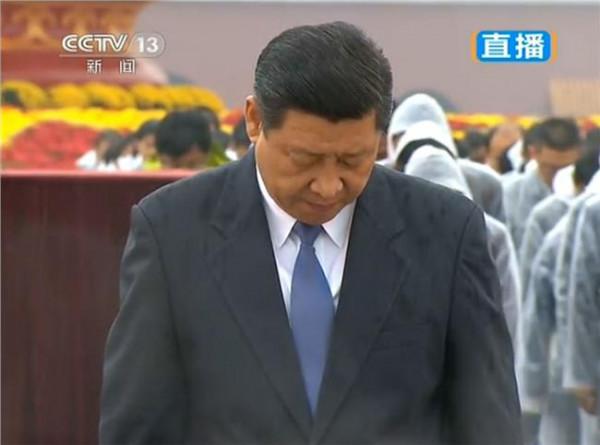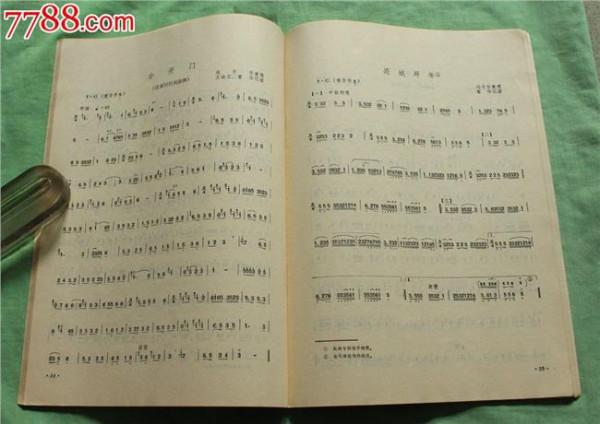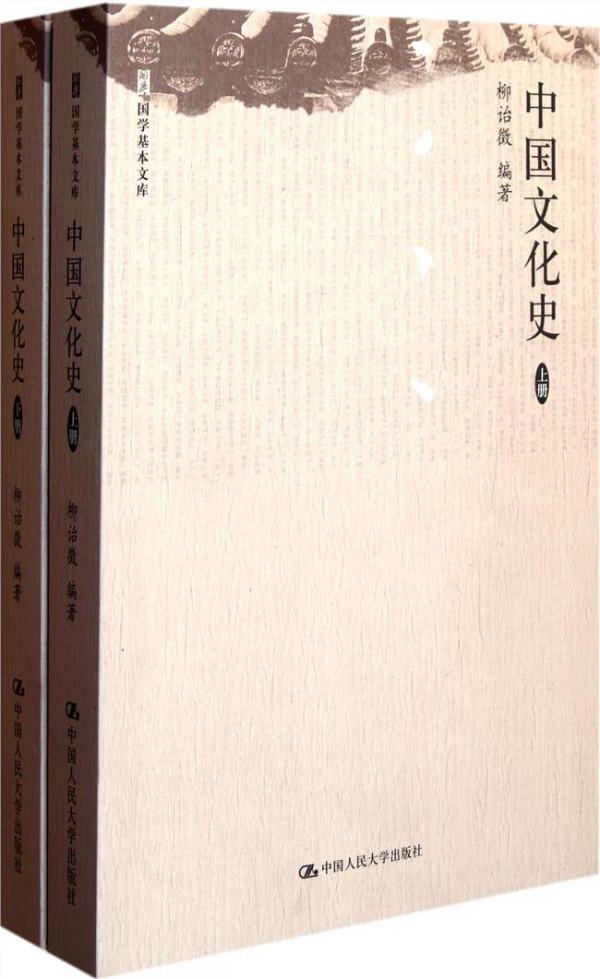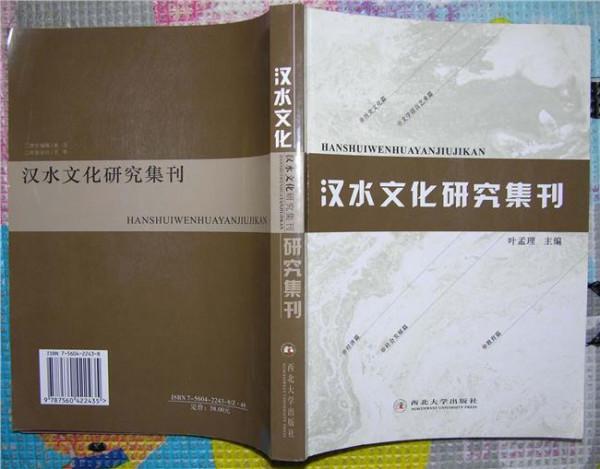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 冯天瑜:中华文化的未来
中国史家素有“述往思来”的传统,“通古今之变”、“神以知来”为学人所勉力追求。以笔者之愚钝,实难企及这种高妙境界。然治文化史者深知,描述往昔,仅完成任务之半,遵循历史运行轨迹所指示的方向瞻视前景,虽是一种探险,但不能回避。这种努力或许难得要领,却是人类追求未知领域的渴望。
中华文化的漫长历程,尤其是近现代走过的路,似乎报告着如下消息——
1、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世界的”与“民族的”二者的统一
未来的世界将是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工业化社会。以技术长足进步、信息迅速传递为推进器,世界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与深化,文化的世界性将纵深发展,各国人民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联系性将日益增强。中华民族当然不能自外于世界文明大道,而必须投身其中,广采博纳外域英华,以谋求文化的兴盛昌大。
文化开放,将是中华文化未来的生机所系。然而,文化的世界性又绝不意味着排斥、取消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普遍化(世界化)与特殊化(本土化)二者间的张力,是未来文化成长的动能所在。
民族、国家,都是历史的范畴,它们既非永恒的事物,也不会凭着人的主观意志而消亡。民族和国家虽在日益摆脱封闭性,但还将长期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民族国家时代还远未过去。
在一个可预见的历史阶段,人类的总体性进步,依赖于各民族的进步,而不是各民族的衰落;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要靠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发扬去丰富它,“将来世界大同,犹赖各种文化系统,各自发挥其长处,以便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合”。
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也是世界各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希望。中华文化健康有益的民族特征的发展,正是对全人类文化作出的一份宝贵贡献。在这一意义上,文化愈是民族的,便愈是全人类的。
我们应当从历史单线进化的错觉中摆脱出来,确立多元化与一体化对立统一的文化进步观。而未来的中华文化,既不可能是本民族文化的原型推进,或外来文化的整体移植,也不可能是中外文化的简单拼凑,而只能是两者的“化合”,是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性再创造。
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各个不同层面,如技术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观念层面,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有异,保持民族特性的程度不一,它们分别遵循自身的规律,在世界化与民族化纵横两坐标间划出各自的运行轨迹,然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对立统一中阔步前进,描绘出新的华章异彩,则是毋庸置疑的。
2、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现代的”与“传统的”二者的统一
毫无疑问,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沿着现代化方向奔进,不断改变落后、愚昧状态。这种现代化将是全方位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为表里的共同进步过程;在精神文明内部,又是知识系统与社会心理系统,也即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共同进步过程。
然而,现代化的文化大厦又是在传统的地基上矗立起来的,历史昭示人们:“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点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
”现实的及未来的文化离不开传统,也不能拘泥于传统,而是依托传统又超越传统,“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为达到现代与传统在新层次上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应当“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即借鉴“原型文化”,改善、净化现代文化,治疗今日文化所患的若干“现代病”;又以现代意识扬弃传统,发展“原型文化”中富于生命活力的部分,创造传统所缺乏而又为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新成分。
3、未来的中华文化将在迎接生态环境尖锐挑战中前进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人工造化,也即文化的锻造,离不开天地(也即环境)提供的洪炉。论及这座洪炉将给未来的中华文化提供怎样的铸造条件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颇不轻松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已逾十三亿,按人口计算的耕地面积仅及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而且耕地减少趋势还没有刹住;至于按人口计算的森林面积、淡水拥有量、主要矿物蕴藏量,都低于或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经济及文化教育水平,也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有相当距离。
而今后中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程度仍将较大。因此,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新矛盾的产生,可谓善恶并进、苦乐同行,盲目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一样是不足取的。任何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在规划中华文化的未来蓝图时,都必须正视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制约和中国发展前景的严峻性。
在人类找到新的能源和食物生产方式以前,中华民族只能追求有限度的、稳步的进展,任何企求生活质量发生戏剧化飞跃的设想,都是不切国情实际的,很可能还是适得其反的。
中华民族必须像爱惜眼珠一样十分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地处理人与生态之间相当脆弱的平衡关系,持之以恒地用力保护并整治自然—社会环境,以改善文化发展的生态条件。这就需要尽可能减少决策失误和改善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于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全方位进步的任务,又从生态学角度向未来中国人提出。
4、未来的中华文化包含现代性转换的多重内容
社会制度既是文化的基本构造部分,又是决定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把社会中各个阶级、各种职业的人们组合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相加之和,优化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不协调整体小于部分相加之和。
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该制度能否产生优化组合,以发挥尽可能众多的人的潜能,使社会整体表现出强有力的功能,促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产,并使文化成果的分配与消费趋于合理。
中华文化现实世界背景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立、两种文化体系的相反而又相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格局将保持下去,在两种制度中发展的两种文化,将进一步产生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中华文化现代转换多重内涵的基础。
资本主义文化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对资本占有者数量的扩大、劳资分配关系的调整、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和普及,资本主义文化又获得明显进展,并保持着经济、市场和技术上的优势。
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化也面临着难以解脱的困境。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组基本矛盾继续困扰整个社会。这一制度下的人们,包括最杰出的文化大师,都愈益感受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领域的贫困之间的强烈反差造成的严重危机。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指出,现代文化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伦理原则的崩溃”,现代“大多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部门里,只熟悉自己很小范围内的专门操作,而且几乎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完整的产品,自然他们就不会感到要对这个产品或对使用这产品负责,这种使用是好是坏,是无害还是有害,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行动与效果的分离,使人们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丧失了伦理原则,引起道德的崩溃。
英国作家查里斯·帕希·斯诺在《两种文化》一文中,则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有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割裂开来的倾向,两者不仅互不相通,而且彼此敌对、排斥,由此将导致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便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脱节乃至对立,造成人和社会的扭曲。
社会主义不是一座自天而降的乐园,不是哲人虚构的乌托邦、太阳城或大同世界,它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充满生机而又存在着种种矛盾的新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走过崎岖坎坷的道路,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中国为例,2000多年的宗法专制文化虽然留下丰富而深厚的遗产,却也带来因袭的重负;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因素,今日中国还吸收得很不充分,其消极因素的影响已经值得人们警惕。
而社会主义文化既受惠于这两种传统文化,又面临这两种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因而要谋求新的创造,此中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确处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统一关系,科学地整治文化生态,焕发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可以预期的。
人类社会进程,通常有一个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递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在经济形态上则有一个由自然经济经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递变的过程。世界诸民族,并不是都要完整地经历社会形态诸过程,如东西方若干游牧部族在先进的农耕文明圈的刺激下,直接由原始社会的氏族制阶段跃向文明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由宗法专制社会跃向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晚年曾致函《祖国纪事》杂志,指出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路径多样性的预见。
然而,世界诸民族却无法在经济形态上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直接从自然经济跃向产品经济。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社会,却不能越过商品经济阶段。而商品经济固然产生久远,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充分发育,并构成近代文化的经济土壤。
中国作为一个长期滞留在自然经济阶段的国度,发展商品经济有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不能关起国门完成,而必须广为汲取外域的、其中主要又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社会法治,以及其他优秀文化。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种种弊端,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当加以防范的。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20世纪初便提出过“节制资本”的设想,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今日中国人,更应当自觉采取有力措施预防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和观念领域的种种病灶。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获得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进展,其内容的丰富和新颖,都是空前的。它包括多重内涵:一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即一般所谓的“现代化”,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时下仍在完成这一未竟之业。
二是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三是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发展中国家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若干成果,从而赢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多重问题,也直接呈现在当今中国人面前,亟待我们解决。
上述三大转折,不仅提出经济的、社会的课题,也在深层次上提出文化的、精神的课题,要求我们综合古今中外智慧,加以创造性转换,促成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当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全面观照三大转变,以此作为省视中华文化传统的出发点。
从实现前两项转变的视角,必须汲纳传统中有助现代文明进展的成分,扬弃传统中不适应现代文明的成分,“五四”以来所做的此类分梳工作应当更细致、更切实地继续下去;从实现第三项转变的视角,则需要对古典文明原始综合的思维成就(如和谐观、中道观、阴阳平衡观及道法自然等思想)作创造性诠释,用其疗治主客两分、一味强调征服自然、宰治人生所导致的“现代病”。
一些站在科学及哲学前沿的西方学者,已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下意义,如科学史家萨顿1930年在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讲中说:“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科学史家李约瑟,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普利高津、汤川秀树等都有类似见解,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前沿性研究中,阐发了《老子》《周易》等中华元典包蕴的智慧的现代价值。
这种对古典的抉发,决非复古倒退,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式上升。
中华民族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中贡献过震惊全人类的文化,又没有在近代的挫折中甘于沉沦,而是顽强地摸索重新崛起的路径。可以确信,有着如此雄健的生命活力与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垦殖新生产力的丰厚土壤,汲取科学世界观的阳光雨露,一定可以重新赢得文化的原创性动力,创造出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现代世界的新文化。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中华文化的维新之命,寄寓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努力之中。
(本文撰于1990年初,收录于《中华文化史》一书。本报刊发前略有删节和修改,已经作者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