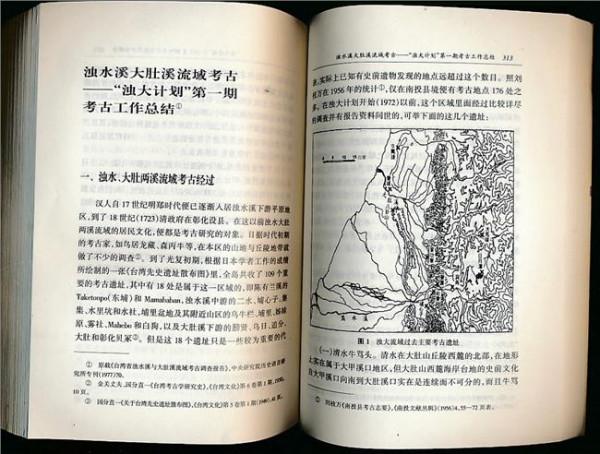我读李零 “不完全的真理”更误人——也读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
2007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闻知李零先生新近出版了一部煌煌巨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急急忙跑到书店并忍着痛花了48元钱买来此书,然后怀着浓厚的兴趣一口气拜读完此书的自序、导读一和总结一、二、三,本想着自己能像面对“于丹现象”那样,不置一词,淡然处之而已,然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妨也来说说李零先生的“丧家狗”之见。
话说时下“孔子热”热的炽热度着实让人有些眩晕,于丹的《〈论语〉心得》热销得也着实让人找不着北,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感觉终于沐浴到儒学复兴的春天阳光者有之,激于卫道愤然起而叫骂者有之,欣欣然艳羡着妒忌着搭乘《论语》热销的便车赶忙出书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者亦有之。
正如在过去“尊孔”和“批孔”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在“孔子”面前表演过各种各样的本相那样,现如今的中国人也在热闹非凡地竞相在“孔子”面前表演着各种各样的本相。如此现象,着实令人深长思之。
可以说,不了解孔子和《论语》火热的背景,便不能真切地了解李零先生写作《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的真实用意,因为李零先生的大作也正是乘着“《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的东风扑面而来的。单从书名来讲,该书之“丧家狗”的立意与视角便格外特别,颇能收让人眼前一“亮”、吸引眼球的效果。
而该书之所以值得关注,则在于此书的作者是一位颇具学术声誉的、“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因此,读者朋友是有充分理由让自己想当然地认为,于丹的心得与这位严肃学者的《读〈论语〉》之作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读者何以要“想当然”呢?因为“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所以才成就了于丹式的“明星教授”,而李零先生是真正靠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既不是糊涂的老百姓,也肯定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令人讨厌的“知识分子”,而是绝对“明白”事理之人,因此,李先生讲的孔子、读的《论语》也就具有百分之百的真理性,是不容置疑,句句在理的!
然而,“想当然”终究是“想当然”,一位严肃的学者也可能与“知识分子”一样,一本正经而严肃地“揣着明白装糊涂”。
先说李先生的“明白”之处。
1.在“《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的时候,李先生能够站在“丧家狗”的视角来解读《论语》,重新厘定孔子的本来面目和形象,无疑是别具意味或意味深长的,其意义就在于李先生无非是想给时下的孔子和《论语》热降降温度,让人们通过直接读《论语》来更清醒理智而明白地看清孔子的本来面目,如此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如此用心亦不可谓不明白。
2.李先生在书中想告诉我们的是,“孔子并不是圣人”,或孔子自己从不曾承认过自己是圣人,而欣然承认过自己是“丧家狗”,这在《论语》中确有明文为证,是任谁也否认不了的。
3.所谓的“丧家狗”,“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也就是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李先生对“丧家狗”一词语义的解释是很明白的,不愧是古文字学家。
4.我们应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或“人造孔子”)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并应区别对待之,这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而且,“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属于李先生的“个人爱好”,是任谁也管不着的。
5.我们要想认清孔子的本来面目,了解孔子的想法,需要“读《论语》”,“读原典”,“看原书”,这话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明白人讲的。
另外,李先生在书中表达的许多观点,我也是持赞同意见的,譬如,李先生读《论语》的一个感受是“孤独”,“孔子很孤独”,本人也有同感,所以在《旷世大儒——孔子》一书中以“人生孤旅”一语来总结孔子的一生。再譬如,李先生说:“道德不是讲出来的。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
”“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宣传孔子,……越是与其他宗教争胜,越是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之嫌。争它干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条最难学。
还有一条,也不好学,是这里的‘贫而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当然是抽象着学)。”“‘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有这些讲法,愚见以为,都透显出了李先生很精辟的见解。
由以上种种,笔者认为,李先生应该算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明白人,而且是一位明白的学者。然而,李先生并不止乎“明白”,他从“明白”处更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诚所谓“明白难,糊涂亦难,由明白装糊涂尤难”,而李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李先生的糊涂之处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立场的暧昧。李先生在书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红旗下的蛋”,过去本来是对孔子不感兴趣[1],也不爱读《论语》的,但现如今态度上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开始“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但这一转变显然不是刘邦的那种由溲溺儒冠到过鲁祭孔的转变,也不是那种由“当年的批孔干将”一变而为如今的“尊孔”“急先锋”的变化。
李先生过去不爱读《论语》,大概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的缘故,因为不喜欢所以就是不爱读而已;现如今可劲儿地一字一句地读《论语》,大概也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一个古文献学者从事的专业的缘故,但有一点不变的是,李先生从来都是自外于“批孔”或“尊孔”的时代潮流的,从李先生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而且李先生是一个天生“自由散漫”、“讨厌道德说教”和有着批评怀疑精神的人,这是李先生的可敬可佩之处,因此,在时下《论语》和孔子的热浪中,李先生偏偏也要读《论语》,目的就是“为了破除迷信”,破除将孔子称作“圣人”的迷信。
既然孔子不是“圣人”,他也就不能再作祟“救中国”乃至“救世界”了,不过,李先生又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而“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笔者仔细咂摸这话的意思,似乎又是在说“真实的孔子”可以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一样,或者李先生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假孔子”救不了世界,只有“真实的孔子”才能救世界?但是,如果说李先生读《论语》的目的就是旨在强调“真实的孔子”能够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的话,似乎也不对,因为李先生又明明说,“活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或“典型的复古主义者”,“真孔子”不过是一个“教书匠的祖师爷”而已,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是一只“可笑也可爱”的“丧家狗”,按道理讲,他连他那个时代都救不了,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这个世界呢?请原谅笔者的愚钝吧,读了李先生的书后,笔者似乎读不出李先生的真实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2.立场的偏狭。对一个人的评价理应客观公允,对孔子也一样,正如为李先生本人所佩服的梁漱溟先生所言,“过分抑扬,贤智不为”[2]。李先生在书中先是这样来评价孔子的:“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小百姓的人。
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段评语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但不知李先生为何后来又非要再讲一些属于“个人爱好”的、对孔子的愤激不敬之词,似对孔子又有抑之过甚之嫌,且不说孔老夫子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即使是对一个不喜欢其观点的论敌,乃至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敬)其人格,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教养,但李先生偏偏要标新立异,竟然说什么“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
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并在书中注释中引证了一段王朔先生的话:“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有朋友从外地来,能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三个人里准有一个人能教我。’‘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那没准还有人以为你都知道呢。’——这不是傻逼么?搁今天哪个宝贝说这么一顿大实话,谁会给他出书?还当祖宗敬着,招来一大堆更傻逼的人认真学习?”李零和王朔先生自然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爱好”,譬如说喜欢骂人,或者是喜欢读《论语》,但如果说有意在引导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对人的评价偏好的话,那么,这种说法,说的好听,是立场的偏狭,说的难听,李先生一方面讲“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一方面又一字一句地认真读《论语》,整个一个王朔先生所说的“那个”(笔者实在不愿意引那个原词,权且以“那个”代之),也不知李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是否没讲一句“大实话”,出版社才给出的书,但不管怎样,按照王朔先生的说法,如果说孔子“那个”,那么李先生就更是“那个”,当然,从“个人爱好”的角度讲,李先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那个又怎么样”!
再譬如,李先生“讨厌道德说教”,认为“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而“道德不是讲出来的”,这很好,但把“道德”仅仅看作是一种“生存策略”,这种道德立场就未免太过偏狭了,因为李先生完全不了解“生活”比“生存”意义更加宽广,道德是生活的必需,而非生存的策略,所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道德说教”的意义,更难怪李先生要把对他人或孔子“敬不敬”的问题只作为“个人爱好”来看待了,因为从“生存策略”的意义上讲,“不敬孔子”也许可以暴得大名。
3.解读的片面。当李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失败者”时,他忘记了孔子的成功之处[3];当李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时,他忽视了孔子的革命性贡献[4];当李先生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时,他有意在歪曲孔子的本来面目或真实形象。
前两点并不难理解,而后一点却极意误导人。何以如此说呢?因为李先生讲的是半句真话。当有人说孔子像“丧家狗”时,孔子欣然承认,说:“然哉然哉!”这是何等的豁达和坦然,这一豁达和坦然来自对人生际遇的深刻领悟和超脱,我想,对于这一点,作为古文字、古文献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李先生不会不了解,从这里我们能够读出的应是孔子那超乎个体际遇之上的、意义更为远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关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如此豁达和坦然,他的这份豁达和坦然足可以引发我们无穷的敬佩和深思,然而,李先生读出的却仅仅是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这句评语中的“只”字至关紧要,无疑是李先生根据自己的臆想而妄加上去的,加上了这个“只”字,李先生便可以轻轻松松地抹杀掉孔子思想及其“本来面目”的丰富性,而孔子形象的简化正可以让李先生一展文字学家解读《论语》的风采,因为只有在思想和形象的简单处才能见文字解释的真工夫,你看,对“只”是“丧家狗”的一个人和杂乱无章的一部书,李先生也能解读得头头是道,尽管过去从来没喜欢过孔子和《论语》,也许李先生现在和将来也不会真正喜欢孔子和《论语》。
就这样,李先生从“丧家狗”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就是:孔子只不过是一“丧家狗”而已,而且还捎带着不忘将“知识分子”损上一句,这是你们的“宿命”,你们只配做“丧家狗”,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真的是只在一字之间啊!
当然,这有点揣测李先生的意思,但愿如李先生所言,“丧家狗”一词“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而已。然而,“无所遇”就真的能完完全全地代表着“孔子的本来面目”吗?愚见认为,这种看法实在太过片面了。
4.读书人的自欺性。从孔子身上或从孔子的“丧家狗”的际遇上,李先生说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但愿李先生自己已摆脱这一宿命,不再是“以良知定是非”而注定只能做“丧家狗”的“知识分子”,不过,我相信李先生还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不然怎么会闲得无聊竟认认真真地读起了《论语》呢,而且是把《论语》“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然而,“以良知定是非”者搞不了“政治”,同样学者的良知也代替不了学术本身的问题。
孔子的“本来面目”无疑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经典文本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读者要想了解孔子的真相,的确应去直接阅读经典文本,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的是,即使是读同一部经典原著,不同的人从中可以得到的“真相”也可能是有差异的,而且是一种“视界的融合”。
在对经典的视角不同的解读中,也许一种读法比另一种读法更好,但很难说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读法,但李先生读《论语》却一再声称他“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他是通过“读原典”、“看原书”而得出结论的,而且,“一切结论”都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我李某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确解,我说孔子是“丧家狗”,他就只能是“丧家狗”,这不是代孔子立言,而是孔子自己就这么说,口气上颇有些不容辩驳的味道。
在我看来,正因为如此,李先生的所谓《丧家狗:我读〈论语〉》才更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而如果说李先生自己对自己对《论语》的解读确信无疑而并不觉得有什么欺骗性的话,那他的这一解读就更是一种读书人的自欺了。
暧昧,偏狭,片面,自欺,虽然打着“还孔子本来面目”的旗号,却只强加给读者一种片面的孔子形象!
的确,“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但,这无损于孔子之为孔子。
的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从来就不是凭空造作,就能创造人类的幸福的。
于丹的《〈论语〉心得》虽然热买得很火暴,但于丹的心得终究只是于丹的心得;而李零先生的《读〈论语〉》却是在“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而且讲的只是半真的话。两相比较的话,李零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而说的“半真的话”才更容易误导人们!
亨廷顿先生说:“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比完全的假话更有误导性。”[5]这话用于李著是再合适不过了!
唉!“孔子很孤独”!他真的“很孤独”,因为就连李零先生这样的“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也不是孔子的解人!
[1] 李零先生在《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的《前言》中说:“过去,老实说,我一直对孔子提不起兴趣。”
[2] 梁漱溟:《今日我们如何评价孔子》。
[3] 如张荫麟先生在《教育家的孔子》一文中尝言:“孔子最大的抱负虽在政治,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
[4] 这一点可以由李先生推荐我们读顾立雅的书来弥补。顾氏在其名著《孔子与中国之道》中说:“在政治上,孔子通常被称做保守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复古和增强世袭贵族的政治权威。事实上,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做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
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内,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中国消亡了。对于这一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李约瑟全名 [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评选]李约瑟:让中国古代科技扬名世界的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d/73/d73e23c9f21c443aa95055b363a945f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