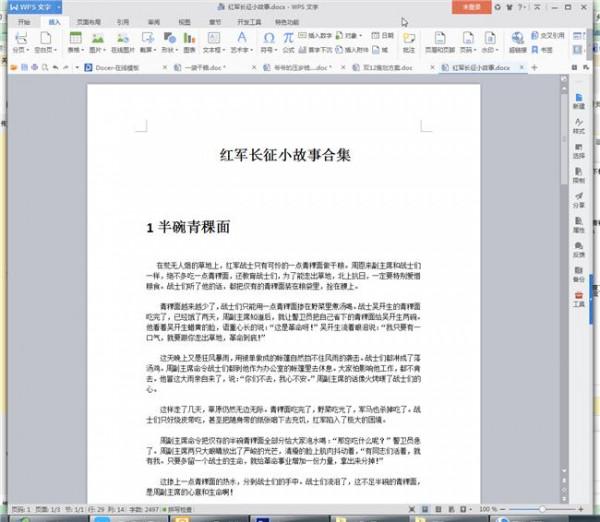粟戎生对越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升起的将星(二十二)粟戎生中将
粟戎生中将,1942年生,原籍湖南会同,生于江苏扬州。粟裕大将之子,侗族。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学习。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1月——1970年1月地空导弹部队任战士、班长、技师、排长,参加抗美援越和国土防空作战,在1967年击落美侦察机作战中荣立三等功。
1970年1月——1983年1月,在陆军野战部队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参谋、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
在连长任上荣立三等功。1983年1月——1983年5月,在总参炮兵研究所任研究员。1983年任步兵第200师师长、1985年任第67集团军参谋长。1983年5月——1989年1月,在陆军野战部队任师长、军参谋长,其间85年2月至86年6月参加老山防御作战。1989年1月——1993年1月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
1993年1月——1998年8月任第24集团军长。
1998年8月——2006年1月任军区副司令员。1990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9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06年1月于63岁退休。
《沙场点兵》电视连续剧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原型就是粟戎生。
粟戎生同志在工作中结合部队建设和作战训练实际,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并获得国家专利技术10余项。
1984年2月,共和国开国大将粟裕离开了人世,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在撒完骨灰之后,将军的长子粟戎生举起右手,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他以军人的姿态腰板笔直地站立着,噙着热泪深情地凝视着父亲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
粟戎生,侗族,湖南会同人,1942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1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控制专业,1999年晋升为中将军衔。历任地空导弹部队战士、班长、技师、排长,陆军野战部队排长、副连长、连长、参谋、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总参炮兵研究所研究员,陆军野战部队步兵第二○○师师长、第六十七集团军参谋长,总参军务部副部长,第二十四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曾为全军指挥自动化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
回忆起父亲战斗的一生,这位将门虎子深情地说:“父亲尽管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军队,但他的形象、他的声音、他的风范、他的精神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耳畔、脑际、心底。”
将门虎子因戎而生
粟戎生与父亲合影(右为粟戎生)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粟裕的长子粟戎生降生了。粟戎生说:“那时父亲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的反‘清乡’斗争。听母亲说,我生养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外公赞赏父亲的战斗生涯,为我起名‘戎生’,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后来,因有被敌人侦知的迹象,外婆亲自把不到两岁的我设法送到父母身边。”
粟戎生的幼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当时,部队办了一个保育院,部队打到哪里,保育院就跟到哪里。粟戎生就在这个保育院里。他回忆说:“我母亲告诉我,战士一副扁担挑子,一头挑着电台,一头挑着我。我两岁左右时,有马和骡子了,就被放在马背上骡子背上。再大点,我就到华东保育院了,也叫学校。校长是李静一妈妈,副校长是邓六金妈妈。后来学校随部队南下,一直到上海解放后才比较稳定了。”
粟戎生刚3岁的时候,粟裕与夫人楚青就带着儿子去河边游泳。粟裕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筒,塞给孩子说:“抱紧了,跳下去!”粟戎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父亲猛然抱起抛进水里。这可把小戎生吓坏了。粟裕就在岸上喊:“孩子,不要怕,自己游!
”抱着竹筒的粟戎生浮在水面上,只得自己乱扑通。楚青看在眼里急得不得了,责备粟裕说:“你也真是,就不怕淹着他?”粟裕说:“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要不老是学不会,你看怎么样?不是也没淹着吗!”
这件事在当时新四军内部传开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句歇后语:“粟司令教儿子游泳——扔进去不管!”
粟戎生说,父亲并不希望子女在安逸的环境中成长,哪里危险,哪里艰苦,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求子女去哪里锻炼。他常常这样鼓励儿女:“年轻人不要贪恋小家庭只想着坐机关。”做父亲的总是“利用”权力,坚持让儿女到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
“后来,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也跟着来到北京上学,上的是‘八一’小学,现在叫‘八一’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就一心想当兵,1961年考上哈军工,学习导弹专业。”军校毕业后,粟戎生没有进大机关,也没留在大城市,而是到了云南援越抗美前线的一个导弹分队。“前线的生活是很紧张的。敌情多时,每天要有4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就拼着命跑到战位。”从战士到排长,粟戎生一干就是四五年。
当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又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再一次“使劲”把粟戎生送到前线,并将自己的一首诗《老兵乐》送给了儿子:“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这铿锵的诗句,是粟裕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鼓励儿子驰骋战场、杀敌立功、为国尽忠的战鼓。粟戎生满怀信心地去了。
在北方执行战备任务,条件比南方更为艰苦。粟戎生说:“粗粮比例大,蔬菜供应较差;气候恶劣,干燥、严寒,需要有坚忍的毅力。我都顶过来了,一点一滴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
在北线,仗并没有打上。“我们连开进山沟里,一连打了3年坑道。我们作业的地段,石质不好,常常发生塌方,6米高的坑道,有一次塌到9米多高,有块大险石很难排除。身为连长的我让战士们离开,自己架梯子攀上去排险。
正在排除时,另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下,擦肩而过,正砸在脚下的梯身上,梯子断了,我摔了下去。如果落石再靠过来十几厘米,就肯定要砸在我的头上,我暗暗庆幸,幸亏没让战士上。万一砸了战士,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代啊。”粟戎生说,父亲曾反复告诫自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排险中,凡是遇上要排除哑炮,粟戎生总是自己上,等完全没有危险了,再让战士进来。让人庆幸的是,3年施工,全连没有发生过一起伤亡事故。
粟戎生当兵后,好不容易有次休假回家,状态不免有些放松,没有像在部队那样每天保持高度作战准备,所以背包也没打,内务也没整,就外出院子与人说话去了。粟裕看到儿子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就把他叫进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这是怎么搞的,鞋子乱放,没有个规矩!
”粟戎生说:“不是回家休假了吗?我平时不是这样的。”粟裕不高兴了:“什么是平时,现在就不是平时?!”粟裕要求他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都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准备,就是放假休息时间也要这样。
平时,父子俩谈话难以离开军事,是典型的“军事父子”。粟戎生当了团、师指挥员后,从研究地形地图到战术战略,父亲都一招一式地指点他,还经常出题考他——“如果你带一支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你应该首先考虑什么问题?”“摩托化部队在公路上行军,被空中敌人炸坏许多汽车,把公路堵死影响了部队机动,怎么办?”……粟戎生说:“当我能在军队中担负一定责任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父亲的培养教育,更加怀念爸爸。”
父子难舍戎武情
粟戎生在雪地中训练
粟戎生爱枪是出了名的,枪法也好。当军长时,只要下部队,他有一个不变的科目,就是要跟师、旅、团长们比枪法。他说和这些带兵人比枪法,不是要比个谁高谁低,而是要让这些带兵人知道差距。“我的枪法很准。能比过我的人很少。老比不过我他们就得练。试想,师旅团长们在训练场苦练还能不带动部队的训练吗?”说到这里,粟戎生微微一笑,“我给不少部队上过射击课,讲完了就打。随便他们选什么人,一般都打不过我。”
早在粟戎生5岁那年,父亲就送给他一支小手枪,说:“这是给你的礼物,你要好好地学会打枪!”这是一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小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作用。当时,年幼的粟戎生并不理解父亲送枪的用意。不过,那时的他对枪很是喜爱。父亲常说打好枪、爱护好枪是一个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学会使用各种枪,熟悉各种枪的性能是一个军人最基本的业务能力。
战争岁月里,粟裕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也总带着左轮手枪。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粟裕仍然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保持着对枪的爱好。粟戎生说,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父亲保留了好几支。
“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到家,赶上他有空,就带我们去进行实弹射击。父亲的枪法很准,常常同我们比赛。有一回,他嫌胸环靶太大,就用一节树枝插在地上,上面顶着半个乒乓球,然后让我和弟弟先打。我弟弟是区射击代表队的队员,但几十米外打这么小的东西还是头一回。弟弟没有打中,我也没打中。父亲笑了笑,接过枪,压上子弹,举枪瞄准,第一枪就打中目标。”
有一次,粟戎生擦拭父亲保存的几支枪时,将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取了下来。父亲很生气,把他批评了一顿,然后耐心地解释了随便分解瞄准部分对射击精度的影响。粟戎生说:“乘下一次射击的机会,我们对枪做了重新校正。”
粟戎生说,父亲一生喜欢保存4样东西:枪、地图、指北针和望远镜,其中,最喜爱的要数枪和地图了。
粟戎生记得,在父亲的卧室里,四面墙上都挂满了地图,门的背后还挂着一张台湾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父亲就挂哪里的地图。“父亲喜欢看地图,也要求我多看地图。他常说,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地图不仅要看,而且要背。
听很多与父亲共同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讲过,在战争时期,每到一个地方,父亲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布置检查岗哨警戒,从而做出紧急情况下的相关处置预案。所以,他所带的部队,即便在突发紧急状况时,也很少受到损失。”在工作实践中,粟戎生慢慢悟出了父亲给他反复讲要看地图、看地形的道理,那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严谨的态度工作才能负起应尽的职责。
粟戎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主要分管训练。他几乎每年都在大漠基地抓实战演练,先后组织了数十场对抗演练。每次演练结束,他都要抓住问题不放,点名批评。有人不服气,他就让人将战场监控的录像拿来回放,逐个讲评演习中暴露的问题。他指名道姓,讲评的大半部分时间是在讲问题,使在场的各部队指挥员们人人脸上都灰溜溜的……
每次对抗训练结束后,他都要给大家灌输这样的理念:训练讲评就要直接讲问题。训练场没有批评,战场就没有胜利。俄军考官对被考的官兵讲:我绝对不会给你高分,只会给你低分,因为我现在如果给你多一分,将来打起仗来你就可能带着几百人、几千人去送死。
这种态度多么值得我们思考。粟戎生说:“我参加过很多的演习,看到听过的演习总结如果有10页纸,有9页半纸是经验、成绩、体会,最后半页纸是问题,部队养成了只能听成绩的习惯,说一点问题就觉得受不了。”
2003年,15个国家的27位外军观察员到北京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观摩我军两支部队对抗演习。演习结束后,粟戎生将美国、以色列、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军事观察员的评价集中起来。人家讲我们的优点,他卷起来不怎么看;但对外军观察员指出我军的问题,他却专门打印出来反复剖析研究。
粟戎生下基层从不打招呼,主要是怕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他在多种场合讲过一个“一块牛肉两个蛋”的妙论:现在有不少部队,平时表现得都很牛,都会拿出部队的光荣历史,牛得很,但部队战斗力到底怎么样?真正参加一次对抗演练,看看吧,关键时候就特别地“肉”(指性子慢,动作迟缓),走不快、住不下、吃不上、打不赢。
所以呢,我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把特别“牛”和特别“肉”合在一起,纯粹是一块“牛肉”。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打仗的时候,不要成为敌人餐桌上的一块“牛肉”。
再就是“两个蛋”。总后规定用餐标准达到每人每天一个鸡蛋,部队大都能够落实。可同样是总部规定,在实战训练中每人每年一颗手榴弹,能落实的大概不到一半。一人一天一个鸡蛋能落实,一人一年一颗手榴弹为什么就落实不了?一支部队如果对吃的关注力度远远大于对打的关注力度,能够实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吗?能打胜仗吗?
如何打赢未来高科技局部战争,是粟戎生特别关注的问题。在当军长时,他就曾组织研制出一套能联通所属团以上部队的野战指挥自动化系统,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和大家一起研究高科技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打法,提出要以高科技对付高科技、以土办法对付高科技、以灵活的战术对付高科技……
有人说,反正在我这个任期内打不了仗,就是打仗也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粟戎生不这么看。他认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多数人都不会在部队干一辈子。但必须看到,部队战斗力的生成、保持、提高,是一代一代人像传接力棒那样传下来的,部队的光荣历史、好的作风,都是若干代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去考虑发展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去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那么,到将来打起仗来就晚了。他一再说,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责任,随时做好带部队去打仗的准备,并把打仗的本领一代一代传下去,保证一旦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部队在战争中能够稳操胜券。
父亲对粟戎生的军事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回忆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还曾到现场认真研究了长征中的许多战例,特别是“四渡赤水”前后的战例,从中深刻体会“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谛。“父亲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学习打仗,这是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辉煌战绩的重要基础。
父亲常给我讲战例,鼓励我努力学习战略战术。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战役的具体经验将失去其参考价值,但是在战争舞台上所体现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却会大放异彩。战争是一门不断前进发展的科学,我们军人一刻也不能停止思考。”
从八一南昌起义中普通警卫战士成长为共和国大将,粟裕身经百战,屡创战场奇迹,曾6次负伤。1930年2月下旬,作为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粟裕,与支队长萧劲光率领部队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敌人一发迫击炮弹突然打过来,在粟裕身旁爆炸。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战士们看到粟裕头部负伤,满脸是血,急忙跑过去帮他包扎伤口,并要把他抬下战场。粟裕苏醒后坚决不肯,刚说完“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又昏了过去。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把昏迷不醒的粟裕抬到后方医院。因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大手术,医生只好用纱布将其头部紧紧缠住。治疗3个多月后,粟裕伤愈归队。
在以后的日子中,战事一紧张,或者工作一劳累,粟裕就常犯头痛头晕病,疼得最厉害时,手都不能去摸。
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3分,粟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粟戎生在处理父亲骨灰的时候,筛出来3块弹片——大的一块黄豆粒那么大,小的两块绿豆那么大。后来,最大的一块送了军科,两块小的则被他留作了纪念。这些弹片在粟裕的颅骨里已经整整54年,这就是后来折磨他数十年的头疼病的根源所在。
“父亲在青壮年时期的战斗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积劳成疾,老年患有多种重病。1981年,他在已经患有高血压、心肌梗塞、胃癌等多种病史的情况下,又患了脑溢血和脑血栓。可他顽强地同疾病战斗着,丝毫没有减少对祖国安危的关心。他对我说,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看得到了,一旦打起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他把殷切的希望寄予革命的下一代。”粟戎生说。
1983年5月,粟戎生调任陆军野战部队师长。行前,他去医院向父亲辞行,“这时父亲的病情更重了,说话已很吃力,不能同过去一样对我做更多的嘱咐了。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还是和以往一样,父亲跟自己没聊家务琐事。“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粟戎生说,父亲生前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头痛的真实原因,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父亲去世前,留下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他的骨灰遍撒在他曾身经数百战的大地上,为的是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
我手上留的两块弹片,可以说是我全家的传家宝。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父亲给我们精神的东西很富足!”如今,尽管粟戎生已退休了,但他仍然关注着军队建设与军事训练工作,关心我军军队的发展,仍在为部队装备技术的改进贡献力量。
“部队推广的一首歌我特喜欢:‘身穿国防绿,胸怀祖国,万里江山,千斤重担交给了我。虽说艰苦,我心里欢乐,虽不富有,拥有山河。’我对‘虽不富有,拥有山河’这句话特别有感觉。在工作期间带着部队穿山越岭,过江过海,我觉得很豪迈。我买了本《地球科学概论》,抽空翻翻这书,总想把这大好河山弄明白了,趁现在身体还行,先旅游吧。”
“我是学工的,当技师的嘛,就是喜欢自己动手。那时我们的雷达、导弹出了故障,我常自己修。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拿到街上修不好,拿回来我再修,差不多还能修好。逛街时新鲜工具对我有吸引力,经常买一些回家。妹妹曾建议开一个修理铺,叫‘死马修理铺’,死马当活马医。
这名字很好,东西坏了拿到街上去修不好了,不值得修了嘛,就是‘死马’了,拿给我修。”在部队,粟戎生是一位让战士拥戴的将军;在生活中,在退休之后,粟戎生仍以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不变的是父子难了的真情。
2006年,粟戎生作为开国元勋子女参与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七军团东出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序曲”。谈起父亲当年的红色征程,粟戎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的3个多月,中革军委派出一支部队,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统治后方挺进。
这支部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第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我父亲当时任先遣队参谋长。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历时6个多月,行程2800多公里。
红军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这一行动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四川成都举行的“情系长征路革命老区慈善万里行”捐赠仪式上,粟戎生代表重走长征路的开国元勋子女讲话时,向老区人民和老区建设表达关注之情,呼吁社会各界多支持老区发展。
2007年8月1日,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上午9时许,南昌起义将帅子女一行20多人来到英雄城南昌的八一广场,在八一南昌起义英雄纪念塔下举行了隆重的献花篮悼念仪式。粟戎生一行默默地将花篮敬献在纪念碑下,把满腔的怀念都寄托在鲜花之中,他们向纪念碑鞠躬、再鞠躬!
南昌起义时,20岁的粟裕隶属于叶挺二十四师教导队,担任起义军革命委员会的警卫工作,主要负责起义军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的安全。
1927年8月1日凌晨,战斗打响时,粟裕和警卫战士们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外等候,护送教育团团长朱德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他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后来参加湘南起义到井冈山。在随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粟裕渐渐走上了军事指挥的岗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已成了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传奇将军。
粟裕离世前留下遗嘱:把骨灰撒在曾战斗过的江西、山东、安徽等8个省份,江西排第一位,粟戎生明白南昌起义在父亲心中的分量。1984年春天,在南昌八一桥下,粟戎生根据父亲的遗愿把父亲的部分骨灰撒入赣江,花瓣随波远去,那一瞬间,他明白了父亲的情怀。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老山防御作战)粟戎生部分照片及二十多年后祭奠老山牺牲战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