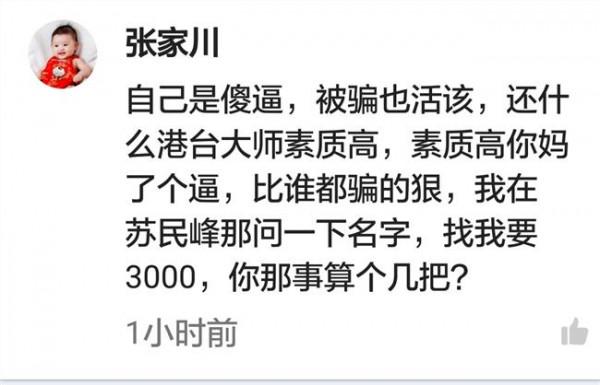张大春文集 张大春:从乡土文学看台湾文学与文化
核心提示:1977年,刚从文革迷雾中走出的祖国大陆,兴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与此同时,台湾也兴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大论战,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影响到了台湾的思想文化领域。本期《世纪大讲堂》邀请到了文化学者张大春先生为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场乡土文学论战的背景、实质以及对台湾文学和思想意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1977年,刚从文革迷雾中走出的祖国大陆,兴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而同年,偏安祖国一隅的台湾,也发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关于乡土文学的大论战,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汇集到了台湾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的台湾社会。
那么这场论战发生的背景与实质又是怎样的,它对以后的台湾文学,乃至台湾的思想意识,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有关这些话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台湾文化学者和小说家张大春先生,掌声欢迎。
嘉宾:谢谢。
主持人:欢迎张先生做客《世纪大讲堂》。
嘉宾:谢谢。
主持人:我们下面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张大春先生的短片。
张大春,祖籍山东。1957年出生于台湾眷村,二十几岁时,他已写出许多擒尽文学大奖的时髦小说。自此,他20年里遍玩小说形式,从《城邦暴力团》的"反武侠"到"春夏秋冬"笔记体的虚实交织,再到文艺理论的扛鼎之作《小说稗类》,还有被称为黑色幽默代表作的《四喜忧国》。今天,他集评论家、小说家、教师、电台主持人于一身,被梁文道称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
张大春:台湾眷村中会形成一些帮派团体
主持人:那么从刚才这个片中介绍,我们知道您出生在眷村,我到台湾去的时候还特好奇,还去过一次眷村。感觉到那真的对一个从那种环境中间出生成长的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经历,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描述一下,您生活的那个眷村,以及这个眷村对您的影响。
嘉宾:好的,早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眷村子弟江湖老》。这是很感慨的,因为眷村本身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一方面是语言的封闭,一方面也是国民党政府从迁台以后,所刻意营造的某一些政治氛围,或者是某一些思想钳制,正好具体地展现在这些马前卒,他们的身上。
这是所谓的第一代,当然我就是第二代了,1957年,1958年以后大量地出生。大概从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古早的眷村有一个基本形式,大概它分成几排,邻街的大概就对这个都市发展会比较敏锐一点,那么后边的就会稍微的钝一点。
可是我们那个眷村后头还有空军的眷村,空军的孩子就比较活泼,而且老实讲经济环境也比较富裕。所以我的那个环境又是属于一个特定眷村里头比较边陲的一个角色。
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只要住在边界上的人,他的适应力或者是他的观察力,就必须要不一样一点。另外一方面这些眷村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刚才讲江湖老。当你不能够取得较好的教育资源,多半就刚才我说的,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它跟这个社会之间的直接互动就来自于他们如何内聚,并且他们如何形成械斗团体,当然他们也很坚持某一些他们自己相信的正义。
在这个情况之下,帮派就会出现了。所以还好我住在最后一排,不然以我的火爆的个性,肯定是马前卒的马前卒。
张大春:在眷村的人有一种"漂泊的根"
主持人:张先生我们知道,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在他的生命意识中间,其实有两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根的意识,一个是漂泊的意识,我到眷村里头去走访的时候,我就特别地设身处地想像自己,假如我是在50年代中期出生在这样一个眷村,我的长辈离开了他们的根,漂洋过海,然后把孩子生在这个村里头,而且我的长辈不会告诉孩子,说孩子这个地方会是你的根,他会把一种飘零感,漂泊感会感染到孩子们。
嘉宾:我记得经常父亲会提到了任何一件事,就是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台词,说回去了,说哪一天回去了,哪一天回去了。所以他会有一个我们讲的想像的国度,这个国度既不存在于他所面对的现实,显然也不存在于他所追溯的过去,那么冀望于未来很显然是渺茫的,所以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漂泊跟根,在我的感受是漂泊的根。
它落在哪它就扎根,这个根扎着扎着它就觉得,我还可以再漂回去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在我的家庭也比较特别,我父亲非常注重文的教育,就好像你掌握了某一种文的教养,似乎就掌握了那个根扎定的地方。
主持人: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像您父辈这样的,被裹挟到台湾去的一批人。他们这些人有一些人,终生没有完成对台湾的归属和认同感,但是当大陆开禁以后,回到大陆以后,回到家乡以后,发现这个家乡已经是他乡了,因此又很悲惨的,或者很凄凉的,又回到那个他大半辈子没有认同的台湾,然后最后终老在那个地方,那么像你们这一代人,对台湾的归属和认同,这种情感最后怎么认定。
嘉宾:韩熙载就有非常著名的诗,"我本江南人,来作江北客。"等到到了江北发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的国家亡掉了,等到再好像想要回到江南,江南没有人认识他了,所以他再一想,江北还有人怀念我。所以大概我相信除了一个国族本身的概念之外,还有人和这个世界的熟悉关系,人际网络,或者是所谓的乡俗礼仪的界定,比如说我在某一个礼仪之中,我会找到非常稳定的人际关系,那么它又是属于乡俗之中,所以这个乡就会从东到西,西到东,南到北,在不断地迁徙和移居的过程里头,让这个文化变得更扩散,甚至无处不可以扎根,我常说中国人的韧性,不是因为安土重迁而来的,安土重迁永远接受漂泊和迁徙的挑战,而在这个挑战的过程里头,安土重迁的这个概念,就变成了在各个不同地方遍地开花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恐怕正是中国古代的许许多多,跟泊迁跟流离,甚至跟移居,搬家有关的母题,不断能够在各个时代感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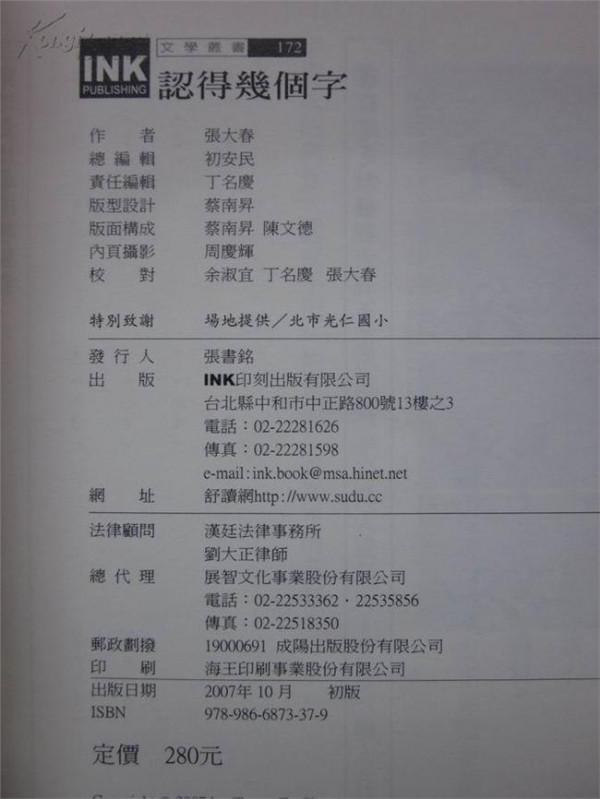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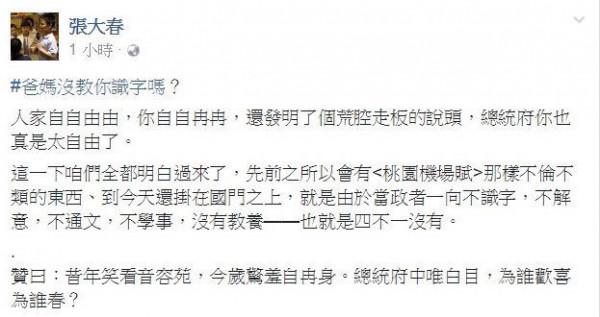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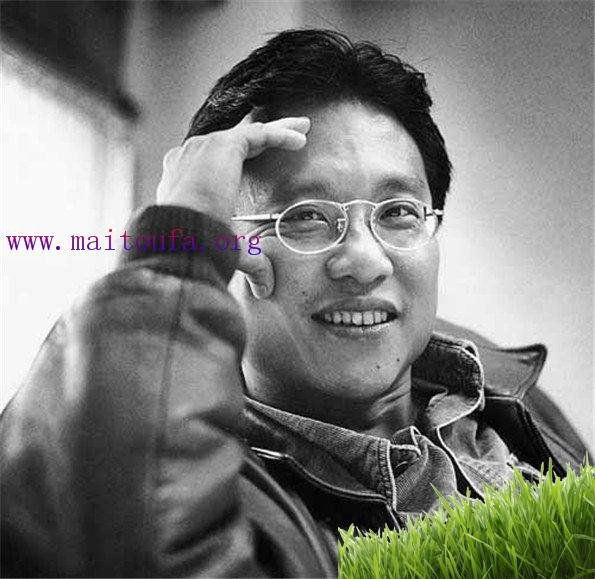











![>京剧演员李万春 李万春[著名京剧演员]](https://pic.bilezu.com/upload/d/48/d48a9a34f5c0c314b36b33ce994e05c6_thumb.jpg)
![>[北大校花潘春春人体]|潘春辉|夜火兰思思图片](https://pic.bilezu.com/upload/8/46/846762779a6e310fa781cfaa297600f7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