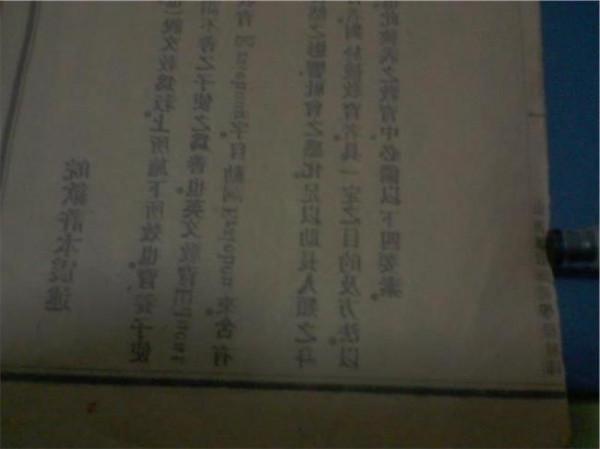任仲夷薄一波 任仲夷——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
我有幸在任老晚年所有接触。任老在我眼里,是一个普通又极不平凡的老人。普通得让我不知道写什么最能代表任老的特征,不平凡得让我不敢轻易动笔。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任老是在荔湾广场的“西关人家”,一个专营粤式茶点小吃的地方。
席间上了一种鸡蛋白做的包子,雪绒绒的煞是可爱。其他人都吃了,最后剩下一个包子,还有任老、王玄夫妇和我没吃,主人说再叫一碟,我们推辞了,任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把一个包子分着吃了。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感觉面对的是一位前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倒是觉得他们象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亲切。
这种感觉之强烈还因为任老和我爷爷同龄,而我爷爷当时刚去世不久。 那次饮茶是接待于光远于老来广州,席间我印象最深刻一句话是任老指着点心对于老说“我们开放个体经营的路子走对了,否则哪有这些东西吃,毛主席也没吃过这些点心。
”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无限情感,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概体会不出来了。时代的发展让老人也有点跟不上形势,王玄阿姨笑着说他们在外商活动中心招待客人,没料到结账的时候要四千多元,差点买不了单出洋相。
我跟别人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没一个把这当笑话听,倒是反问他们还需要自费请客吗?包括党内干部。 饮茶结束时,任老和于老无言对视握手长达数分钟之久。
两位老人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不过那时他们还不认识。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改革开放年代。历经磨难,他们学生时代所追求的理想没有改变过。如果说五四运动涌现了党内第一代精英,那他俩无疑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党内第二代精英。
两位老人都有极高的智慧,即使不从政,他们也会成为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或者商人什么的。能熬过险恶的政治风浪,也许不难,但坚持理想主义而自保实属不易。70年代末复出的老人们不乏明哲保身之辈,理想主义者始终没有成为主流。
可能家庭出身的关系,于老身上有种贵族气息,衣着很得体,完全不象个半身不遂的老人,饮食挑剔,非甜食不吃,就是那发型也时髦得和小泉有得一比。相比之下,任老九显得非常平民化,看起来什么都不讲究,一顶鸭舌帽、一件夹克衫、一根手杖,是他晚年的标准形象。
之后和任老一起开过一些小型的座谈会,任老每每都有鞭辟入里的发言。很遗憾,我不是文字工作者,没有记录的习惯。
把听任老谈话当作享受,没有想到传播的责任。在去年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之后,应人文学会会长郝元文邀请在南沙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带了录音笔,录下了任老的发言,摘录一段,让大家体验一下任老的语言艺术: “什么是和谐,从文字上解释,‘和’,每个人一张嘴嘛,‘禾’,粮食,都有饭吃。
‘谐’,皆言,都说话,都可以说话。” “什么叫和谐?如果老是强调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都是‘服从’啊。
你不服从不行啊,你不服从就不和谐啊。我认为少说了一个: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光服从党中央不行,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人民!六个‘服从’。党代会开后,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可,那也不行啊。
党才六千多万,人民十三亿,少数服从多数嘛。” 今年7月份时候,任老提出想和袁伟时老师到从化温泉宾馆聊聊“革命与改良”,委托高伟梧联系。我也去了,以袁伟时老师“司机”的身份沾光。
袁老师主要讲了晚清如何错过改良时机,导致政权垮台,任老发言不多。我和袁老师乘早起之机浏览了温泉宾馆的大概环境。 化温泉宾馆曾经是个很神圣的地方,一般人有钱也进不去的。以前的省委书记在这里建了七个政治局成员的别墅,虽然有正式名称,现在仍俗称某栋别墅为XXX别墅,从上自下从内到外,基本按级别安排,只有周总理的别墅例外,靠近出口。
也怪不得建设者拍马屁,那时候各省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建一套别墅是标准配置,有些省份建两套才特殊点。
那个年代经常有广州会议、庐山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北戴河会议……许多就是在这些别墅里开的。任老到广东就任之后,就把这个温泉宾馆开放了,只要花钱就可以住进来,商人们最爱用它来招待北方客户。
毛的行宫,百姓也能住了,给人感觉象改朝换代一样,所以现在“自改革开放以来”比“解放后”还流行。任老作为离休老干部,可以每年到温泉宾馆住几天,但任老夫妇有四五年都放弃了这个待遇。那次到从化温泉还选在最清淡的时节。
从从化回来之后不久,今年8月份去了一次任老家里,为了筹备一次在东莞开的会议。任老家在省委大院旁边的宿舍区,里面只住着现任和前任省委书记,大概一家一栋或者两家一栋,外观看去没什么修饰,和农民私宅差不多。
任老家里非常俭朴,狭窄的客厅里最显眼的奢侈品,就是墙上的平板电视,康佳牌的。应该挂上去不很久,因为刚听人说任老家里只有一台19寸电视。墙上还挂着一幅字“达观”,除此之外没有见到一般官员家里常摆设的古玩珍品。
王玄阿姨说想在后院种点菜什么的,我开玩笑地说,种花就好了,种菜是与农民竞争,王玄阿姨听了夸我说的有道理。王玄阿姨很会说话,有她在就不会冷场,从自己儿子媳妇、孙子、孙子的女朋友,一直聊到自己朋友。
任老话不多但很精炼,那天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句话“我不喜欢和你那些朋友玩,整天就知道打台球、打高尔夫球,我喜欢和他们(指人文学会)在一起,和袁伟时在一起。”王玄阿姨闻后立刻止住了自己的话头。
两夫妻的对话如果撇开具体内容,形式上和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女人话多,男人的话权威。我想起一句话“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 从聊天中得知任老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
任老来广东时,根据政策父母调动只能带一个孩子迁户口,他就只带了二儿子过来,大儿子留在辽宁。大儿子很想来广东,私下通过梁广大的帮助调到珠海,被任老知道之后,硬是逼着梁广大把大儿子迁回辽宁。
任老曾说过说他年轻时不讲民主,在家打小孩,我看他老了也“霸道”。任老的大儿子二儿子现在都已经退休,小儿子是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深圳的。 没想到几天之后,任老就在体检时查出了新的病灶,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老天爷已经给了任老远多于常人的生命,但是人民仍然不满足。我不太同意笑蜀的把任老定位在“一个永远的倾听者”,他的价值主要不是听,而是说。任老的听觉早就退化了,但是他的言说能力,在逝世前的日子仍然是高超的。
他说的对象不是老百姓,而是体制内的同仁。任老的政治智慧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的发言常常给人以顿悟的感觉。任老在体制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比民间的要大得多,尽管不是党内主流声音。任老逝世,使官员们少了一位良师诤友,这个地位是民间思想家无法替代的。
让人欣慰的是,任老病重期间,国家领导人们亲自或者委托他人看望了任老,任老带着希望而去。 在人文学会组织的一个小范围追思会上,我听到任老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大约2000年的时候,任老在秘书的陪同下去眼科医院看病,病人很多,电梯拥挤,等了很久上不了。任老对秘书说,人家要做手术坐电梯,我们走楼梯吧。于是任老和秘书一起爬楼梯,上到17楼!中途休息三次。我要连他的秘书一起钦佩了,换个人,可能自作主张打电话找院长出来接待了。
任老在我眼中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不平凡是他的智慧和高干经历,普通的是他的喜怒哀乐和忧惧。他已经是一个极具理想主义的高级干部,不能承担民间的对官员过于理想化的期盼。我们纪念任老,主要是希望全社会都了解任老所说“党内健康力量”的存在,携手走和谐改良之路,以达到任老所期望的“中国不能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