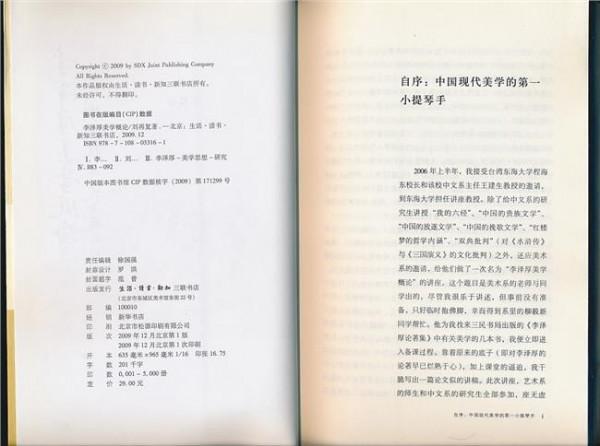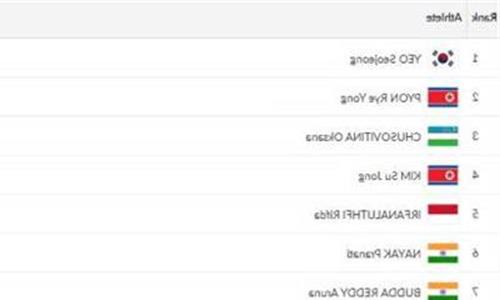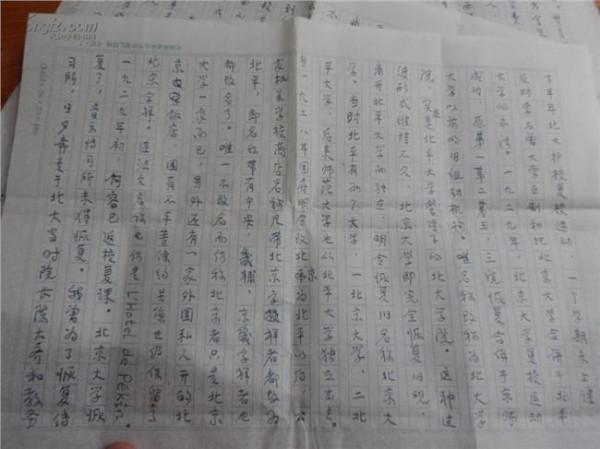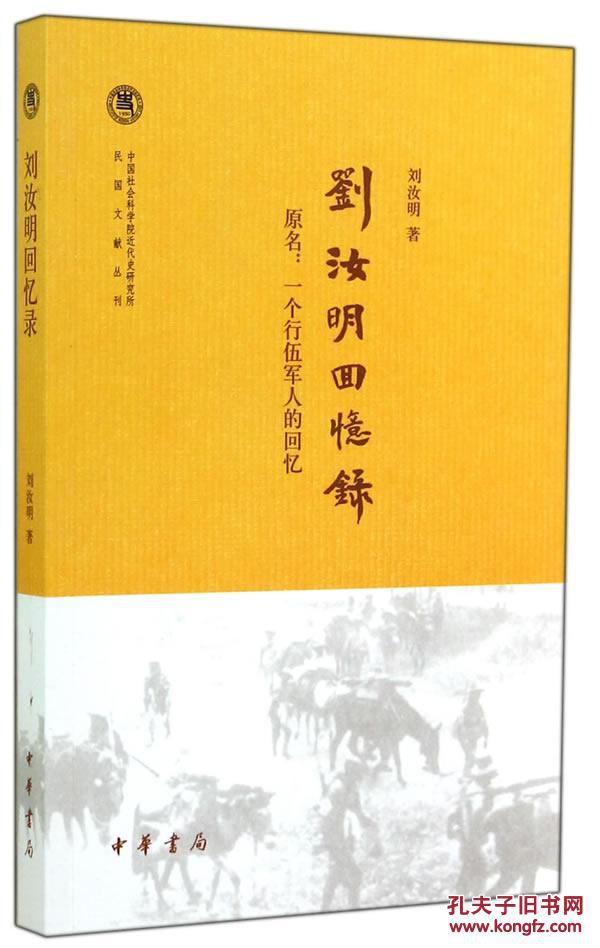刘再复回国 刘再复:李泽厚的中国美学观和刘小枫的挑战
刘再复:李泽厚的中国美学观和刘小枫的挑战 (摘选自:刘再复: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 李泽厚对我国古代美学有一套新颖的阐释,在这方面,他的论著相当丰富。
在八十年代之前就写过〈谈李煜词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载《门外集》长江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以“形”写“神”(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等文章。八十年代之後,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成果。
一九八一年出版了著名的《美的历程》,对中国古代美学历程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描述。这是一部简要的、广义的美学史,也可以看作简明的中国古代艺术思潮史。他在这部书中,把中华民族的美的历程视为以实践理性为特徵的民族审美意识的积淀过程。
在这之後,他又主编了多卷本的《中国美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史,而且是狭义的美学史。该书《绪论》中说:“所谓广义的研究,就是不限於研究已经多少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而是对表现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中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其中包含的美学思想的实质,并对它的演变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
所谓狭义的研究,就是以哲学家、文艺家或文学理论家著作中已经形成的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注意於我国历代对有关美与艺术的种种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思考所取得的成果,亦即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在理论上的表现。
因之,这种狭义的美学史,实际就是我们民族在理论上对於美与艺术的认识的发展史。”(《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四至五页)在写作这两部美学专著之後,他又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访问期间,完成了《华夏美学》(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出版)。
这部书是他对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些更加成熟的思考。 对於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轮廓,李泽厚多次地作了概要性的说明。
一九八O年李泽厚在为宗白华《美学散步》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美学有四大主干,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以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为特色的庄子哲学,以及并不否弃生命的中国佛学,加以屈骚传统,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精神和传统。
”一九八一年他在〈关於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中又说:“如果说儒家学说的‘美’是人道的东西,道家以庄子为代表的美是自然的话,那么屈原的‘美’就是道德的象徵……还有就是中国的惮宗。
”从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起了决定作用,而从文艺领域来说,儒、道共同起了作用,“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都展示这条基本线索。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就是按照这种基本认识,描述了中国美学史在惮宗诞生之前的三大美学思潮,即儒家美学、庄子美学和楚骚美学。第二卷则侧重描述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文论、画论、书论、乐论中所包含的审美意识。
《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的写作方式是以论带史,因此,在这两本书中凝聚着李泽厚对中国美学的一些最重要的见解。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阐释中也显得更加具体。
他在《华夏美学》的结语中说: 甚麽是本体?本体是最後的实在,一切的根源。依据以儒学为主的华夏传统,这本体不是自然,没有人的宇宙生成是没有意义的。
这本体不是神,让人匍伏在上帝面前,不符合“赞化育”、“为天地立心”。所以,这本体只能是人。本书作者在哲学上提出人类学的本体论,即认为,最後的实在是人类总体的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两个“自然的人化”。
外在自然成为人类的,内在自然成为人性的。这个人性也就是心理本体。 李泽厚认为华夏美学、哲学、文学艺术,甚至包括政治伦理,都是建立在这种心理主义上。
这种心理主义,不是某种经验科学的对象,而是以情感为本体的哲学命题。这个本体,不是神灵,不是上帝,不是法律,不是理知,而是情理相融的人性心理。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感性,是一种审美的形而上。
李泽厚在写作中国美学史时,完全打破唯物、唯心斗争史这种庸俗的两项对立的模式。他在〈关於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中曾说明:中国美学史不能用唯物唯心斗争史来贯穿。
而这点,正是过去写作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的根本弊病。大陆有一个叫做侯敏泽的人,他写了一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是把朱东润等老先生的材料偷窃过来,然後给每一个批评家贴上唯物唯心的标签,便成了一部新的文学批评史。
李泽厚非常鄙视这种学风。抛开“唯物唯心斗争史”的庸俗化模式,李泽厚对我国美学史的特点和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很有见地的阐释。他把中国的美学特徵概括为四点:(一)以乐为中心(不是把乐视为一种认识,而是把乐看作与感性相关的一种愉快,“寓教於乐”的命题就是这个意思)。
(二)线的艺术(这是以乐为中心观念的延伸,对事物不是注重模拟,他还提到黑格尔注重色彩,康德更重视线条)。
(三)情理交融(抽象具象之间,表现再现同体)。(四)天人合一。对於最後这一特徵,李泽厚特别强调,他认为,中国的审美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参见《中国美学及其他》)。这一境界,包含有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的常规范式。
李泽厚认为,美感有三个层次: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而“天人合一”处於美感的最高的层次中。 “天人合一”一词出自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义》:“以人类合天,天人合一”,按李泽厚学派的解释,它包含着形体合一,情理合一,规律、目的合一。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美学命题,它强调人对自然的协调和适应。这就是说,美不脱离人和自然的关系,美就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过程。
董仲舒说:“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从自然的一方说,这是“自然向人生成”,从人的一方说,这是自然的人化。孔子曰:“逝者如斯夫”这句话正表明,对时间、人生、生命、存在有着很大的执着和肯定,人的生命价值不在来世或天堂的不朽,这种不朽即在此变易不居的人世中。
它的路标是指向审美的,而不是指向宗教上帝。这是非常珍贵的民族传统,是天人合一的核心和灵魂。
魏晋以後,诸致东来而被同化,便是被这一传统所同化。 如果说儒家美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道家更是如此。李泽厚认为,儒家美学强调“和”,主要是人和,也就是使人与天地同构也落实为人际的谐和。
庄子美学也强调“和”,但这是“天和”。所谓“天和”,也就是“与道冥一”,这就是不必人为地强求益生,而自自然然地会生长得很良好;不必人为地具有喜怒好恶等感情,而自自然然地如四时那样有喜怒暖凄的感情。
“所以,庄子哲学是既肯定自然存在(人的感情身心的自然和外在世界的自然),又要求精神超越的审美哲学。庄子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的感性,他将超越的存在寄存在於自然感性中,所以说是本体的、积淀的感性。
不假人为,不求规范,庄子就这样提出了在儒家阴阳刚柔、应对进退的同构感应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天人合一’,即‘与道冥同’。这种‘天人合一’之所以可能,正由於它以这种积淀了理性超越的感性为前提、为条件。
”(《华夏美学》第七十七页),过去人们重视和强调儒道的差异和冲突,而李泽厚却充份注意到二者在对立中的互补和交融。认为老庄道家乃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庄子美学显得更为重要,儒道互补的现象也更为明显。
他认为,庄子道家“比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别都更好地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基本特徵:形象大於思想;想像重於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纷,乃凝於神。儒家强调的是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审美与情感、官能有关),是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道家强调的是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亦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
”(《美的历程》第六十六页)总之,庄子美学的特点是对生命、个性、感性的注意,因此,庄子的哲学其实是美学,是关於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的美学,是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个体身心绝对自由的美学,於是,李泽厚认为,庄子乃是我国反异化的最早的思想家与美学家。
刘小枫很不赞成李泽厚对道家美学的评价。他不认为道家美学是反异化的美学,而认为它是引向另一种异化的美学。
刘小枫认为,道家美学所鼓吹的“逍遥游” ,“蝴蝶梦”这种“绝对的自由”,其实质不过是生命的自然顺化,即生命的植物化和石头化。这裏没有丝毫价值形态的心的激动和颤慄,没有任何超越意义的情的感受和爱意。
它不是要求生命超越原始状态,而是要求生命回归原始状态,从而成为无情的石头,就是道家审美主义的最终结果。石头性格就是道家的审美人格。这种人格排除了关怀而发展了一种大智,即冷漠、游心、物我同构的智慧,从而使天地人世界丧失了神圣立场的可能,达到自然生命的本然,使自然形态等同於价值形态,这样,就否定了一切价值形态。
刘小枫说: 道家精神的出发点是对事实世界的残酷、虚妄、丑恶的反动,但它引向的并非是一个更高的价值世界,而是植物性、生物性(“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保身、全生、养生、尽年)的世界。
(《拯救与逍遥》第二百四十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小枫还说,我们始终要询问的是,它是否是一个更好的去向,是否是人的真实的留居世界,是否是人的真实意义所在。
肯定道家的路向,就意味着肯定在任何不幸的境遇中,人都有理由返回到另一种非人性状态,排除爱和善的价值意义,使整个世界陷入另一种虚无。
把价值等同於自然就无所谓价值。道家的审美主义还暗含着对审美形态的根本否定。因为,审美仍然是一种价值肯定,而道家是否定一切形态的价值的。
如果人中止了任何种类的意念(包括价值意向),不辨任何种类的是非(包括美丑),审美形态的价值何以能够确立?除非我们首先认定审美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非价值的形态,它不关涉人的价值意义,这样才能确立道家审美主义的正当性。
而事实上这恐怕很难说得通。审美形态不是自然形态,从逻辑上讲,否定任何形态的价值的道家审美主义就是一种伪审美主义、伪美学。 不管赞成不赞成李泽厚或刘小枫的观念,都应当承认,这是很精采的辩论。
无论是李泽厚对庄子的阐释还是刘小枫的挑战,两者都充满着美学的智慧。我本人常常只顾欣赏其智慧而忘却其是非的判断。
和李泽厚争辩的人很多,人们熟知的李泽厚与蔡仪先生的争论就一直延续二、三十年,但是,我们发现,双方辩论的语言互不相通,而且蔡仪先生总是设置一个现实的、充满俗气的“马克思主义”的审判台,唠叨着的总是那么几句话,完全没有刘小枫争论中的那种活泼的思辩和知识的魅力,更没有刘小枫的那种富有魅力的独特文采的学术语言。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也以欣赏的冷静的态度对待刘小枫的挑战。他巧妙地引用刘小枫在另一本书中——《诗化哲学》谈论庄子的一段话来回答刘小枫。
刘小枫曾说: 中国浪漫精神当然要溯源到庄子……超形质而重精神,弃经世致用而倡逍遥抱一,离尘世而取内心,追求玄远的绝对,否弃资生的相对,这些与德国浪漫派在精神气质上都是相通的。
同样企求以无限来设定有限,以此解决无限与有限的对立。只有把有限当作无限的表现,从而忘却有限,才能不为形器(经验事物)所限制,通达超形容的领域。
同样,只有把语言视为出於宇宙本体的东西,才能使语言以意在言外(类似於比喻)的手法去意指绝对的本体。……一个根本的区别在於,中国的浪漫精神不重意志,不重渴念,不讲消灭原则的反讽,而是重人的灵性、灵气:不像德国浪漫精神所讲的综合那样,实际是以主体的一方吃掉客体(对象)一方,而是以主体的虚怀应和客体的虚无。
李泽厚表示,他赞成刘小枫早些时候这种思想,即把庄子的浪漫主义美学视为一种不为形器所限制,通过超越形器而达无限的美学。
而庄子从“逍遥游”、“至乐无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到“庖丁解牛”、 “梓庆为╳”……,所贯穿的基本主题都在於由“人的自然化”而达到自由的快乐和最高的人格。
而所谓人的自然化,并不是要退回到动物性,去被动地适应环境;刚好相反,它指的是超出自身生物族类的局限,主动地与整个自然的功能、结构、规律相呼应、相建构。
而这种呼应和同构也并非当下即得,而是在长久积累之後,已积淀成无意识的倾发。庄子在这方面把“天人同构”远为具体地和深刻地发展了,由於它舍弃了社会与人事,集中注意人的生命与宇宙自然的同构呼应,所以他才注意和突出了全身心与自然规律长期呼应而积累下来可以倾泄而出的无意识现象。
(《华夏美学》第一百页) 对庄子道家的思想的批评,我觉得应当分开现实层面和审美层面。
如果不加区分,我们批评一种美学思想或美学命运,就往往不是批评思想本身或命题本身,而是批评思想和命题在社会中的作用。而把命题(或一种思想)在社会环境中的作用当作命题本身,就是因为批评者站在现实层面的某种现实文化的价值立场上,以某种现实的价值眼光对命题作出判断。
世界的情景充满矛盾而且不断变化,很难用一种绝对性的理论和眼光去解释世界和评判一种命题,这不是相对主义,而是把命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情景和世界情景下加以审视,看其在哪一个范围内才有道理。
庄子的许多思想,就是在具体的审美的情景下才显得精采和有道理,而如果把它放在社会历史的现实层面上,它确实会发生使人植物化、石头化的作用。
我的这一意见不是毫无原则的彼此皆是皆非,而是划定一个界限去讨论问题。人是有限的,人的眼光也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眼光不可能绝对地把握世界,把历史说成是某种必然,就是把人的有限眼光夸大为无限,其实,人的有限眼光只可能把握几年、几十年,不可能把握整个历史进程。
人的智慧所孕育出来的某种学术命题,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和有限的情景语景下才是合理的,超出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就不合理。刘小枫在《诗化美学》中批评庄子时,显得比较公平,因为,他把庄子美学放在艺术精神的范围内审视,而在《拯救与逍遥》中则把庄子推向现实的价值领域,自然就对庄子的反价值性不满。
这种不满和批判在现实层面上有道理的,但在审美层面上,宣布庄子为伪美学,可能要求得太苛了一些。
不过,在思维方式上,李泽厚似乎也是如此,他已经把庄子美学推出美学的范围而进入社会作用的范围,他在谈论“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的现代意义时说:“把美和审美引进科技和生产,生活和工作,不再只是静观的心灵境界,而成为推进历史的物质的现实动力,成为现代社会的自觉韵律和形式。
只有在这样一个现实物质实践的基础上,才可能经过改造而吸收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作为生态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睦相处的亲密关系;在此同时,人自身的自然(作为生命情欲的内在自然)也得到了理性的渗透和积淀。
外在和内在两方面的自然在这意义上都获得了‘人化’,成为对照辉映的两个崭新的感性系统,这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化的自然’和‘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既然把庄子的美学思想置入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之中,无怪乎小枫要批评了。我个人认为,把庄子思想放入历史系统和放入美学系统很不相同。
我只欣赏李泽厚那些放在美学系统的阐释,而推广到现实层面,我则有所质疑,例如“天人合一”,放在审美层面上,它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可是,如果放在现实的层面上,却容易导致人对自身有限性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