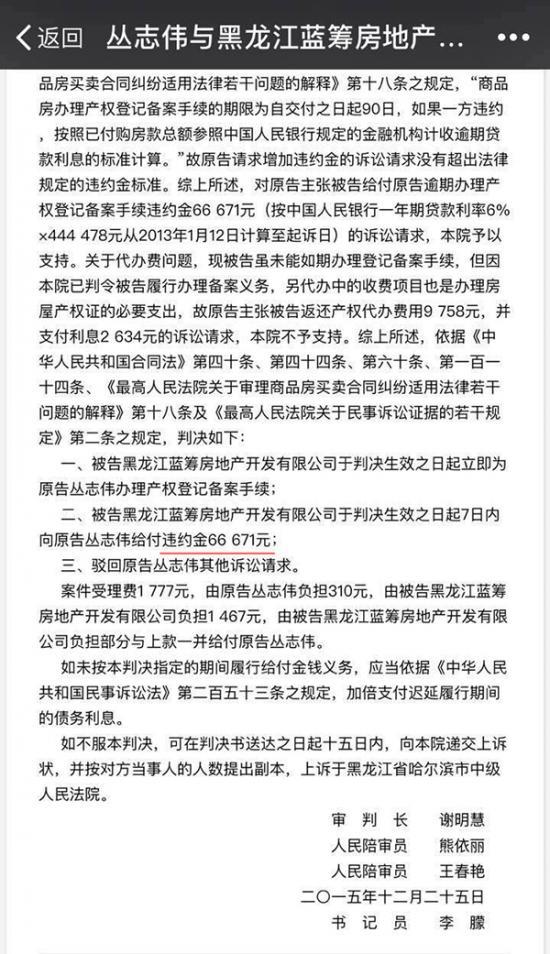刘再复刘剑梅 刘再复什么是文学 刘再复:我对文学不是兴趣 是信仰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著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人文十三步》等40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
“70岁,我觉得我刚刚起步,而悲剧性在于,思想成熟,却在等待死亡。李泽厚说他一直有死亡的假设。比如我现在死了,死了还追求什么?财富权力?我只想让我的心灵提升”。昨天,刘再复坐在晓风书屋里,说话带着闽南乡音。
呷一口大红袍,说这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二三十位仰慕他的读者看着他。 他是作家,他说要“以轻驭重”,用轻来观察人性。相比于前天在厦大做演讲,他说其实更爱这样的小环境,“人真的不用多,多了反而听了不明白,一个人我也讲”。
回答问题,他不需要哪怕一秒的思考,严密,有逻辑,带着诗意的感染力,透着智者的豁达。和记者聊“悟”是“凭空还是阅历”。他说倾向于阅历而悟,不断地读书、经历挫折,或许就能小悟、中悟、彻悟。
记者:当年出国后,是否让你转变为另一种状态? 刘再复:出国后,我赢得了一个读书、写作、研究的沉静状态,也可以说是达摩面壁状态——只不过我面对的是落基山。有这个沉静状态,才可能和历史上伟大的灵魂相遇。
我的书,实际上都是在对话,和荷马、莎士比亚、但丁交谈。 我在中西文化夹缝中,打通两者血脉,打通学问与人生的连接。我自己构造了“象牙之塔”,住在里面。但也要有饭吃,比如到香港当当客座教授,挣点教科费,这是为了谋生。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象牙塔就是达摩之洞,文学状态也是。
记者:您的新书书名是《走向人生深处》。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在“深处”吗? 刘再复:这个书名原来叫《两次人生答问》,编辑改得好。真正的宝贝沉在海底。“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已成为我的座右铭。
原来我的社会关系太沉重,出国后简化了。我变成和几个朋友、几个学生、大自然相处而已。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与大自然的关系重于我与人的关系。这和海明威挺像,我去参观他的故居,他当年站着写作节省时间,恐怕是为了赶紧去捕鱼,那时他最高兴的是把鱼提起来给人看。
我也是,赶紧写完,然后去草地开拖拉机,割草。李泽厚说没想到我这么喜欢体力劳动。我从小学起就当劳动人民,墙上全是“捕鼠英雄”、“学习模范”、“劳动模范”的奖状。
记者:从您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乡情。您对家乡依然牵挂? 刘再复: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的心牵挂祖国,牵挂故乡。一来厦门,老乡很多。佛教要义里讲“放下,放下,放下”。
放下权力欲、功名、孤独感……奇怪的是,我只有乡情老放不下。 我不断定义故乡,就是因为对故乡的眷念太深。这种情很难断。闽南人乡情重得不得了。我到东南亚去,吃惊怎么到处都是家乡人。到新加坡演讲,《联合早报》给我看老乡送的花篮,我真的很感动。
记者:您对文学还在坚持,可是现在的文学状态却很尴尬,被排除到边缘。 刘再复:进入商业社会,俗气覆盖一切。全人类在变质,变成金钱动物。人们崇奉伪宗教——拜金教。我对文学不是兴趣,是信仰。
以前有个年轻人给沈从文写信问,我对文学有兴趣,我该怎么做?沈从文回答:对文学有兴趣不够,要有信仰,什么都可以不要,都可以牺牲,这才够。我要守住对文学的真诚。尽管我后来对人文、文化都兴趣,但文学是我的基点。文学代表广度,历史代表深度,哲学代表高度。我要把文学、历史、哲学打通,也是“三通”嘛。
记者:您对于自己现在的角色如何定义? 刘再复:我的本真角色是作家。世俗角色不要迷恋,虽然它带来世俗利益,比如我当所长就有汽车、秘书,但这些东西一不注意就损害了本真和心灵。我当不了救世主、灵魂工程师、先知,我只是把作品写出来,发出自由的声音。
外在评语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内心自由。而所谓幸福,就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自由状态要自己给,自己觉悟到,才有自由。 文/图 记者 林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