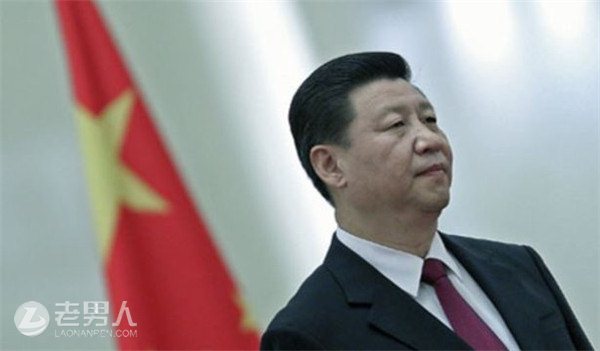任剑涛谈中国传统的国家管理结构 称其是三权割裂

提问: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农耕文明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文明?
任剑涛:农耕文明可以叫做分裂式的经济文明。什么叫分裂式文明?官方有一套控制经济资源的强有力行政措施,国家权力方面是绝对主导力量。但农耕文明实际的财富贡献者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是以家庭和家族为生产单位的,跟国家没有关系,“皇权不下县”。这就是一种经济行为主体的分裂状态。

秦晖教授曾反驳“皇权不下县”,说不下县纳税怎么成功?我认为是皇权下县,是皇权、官权委托绅权征税展现出来的。所以皇权并不直接下县,县官以下不到基层社会活动。这是费孝通、吴晗等学者写《皇权与绅权》时特别强调的,中国就是这么个二元社会。而我特别强调,中国传统的国家管理结构是三权割裂的,而不是三权鼎立、分权制衡的。皇权,在宫廷里制定政策,是否能执行,根本保证不了;执行靠谁?靠官僚。皇权在官权那里,就有一层过滤,而官权只到县级,就是县官一级。官权以下靠的是绅权。皇权、官权、绅权一割裂,跟基层社会的行动逻辑便不搭边,国家管理的实际有效性大打折扣。

我们给国家算财富,说古代中国GDP很高。但这并不是一种政治经济连贯运作的机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明高度发达,却没有催生出有契约精神和法治行为的政治文明。为什么?因为经济跟政治在古代并不是勾连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紧紧勾连是现代世界的特征。因此,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并不自然催生出民主与法治。从现代世界出发,要求中华古代文明能把政治经济勾连在一起,进而克服三权割裂导致社会不能连贯运作的弊端,那是必须的。但对我们的祖宗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苛刻。
英国能够实现现代文明的突破,有其偶然性。但经由偶然催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其他国家没法拒绝。为什么?因为它解决了其他文明形式都没有解决好的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大关联问题:第一,大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势必分享经济成果,不分享,共同体就建立不起来;第二,共同体建构必须解决人类的权力来源和权力分享机制,否则其稳定性堪忧。很多地方没有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没有可靠的契约精神,就是因为不问权力来源,打天下者坐天下。

提问:传统的农耕文明,虽然生产力远不如工业文明,那有没有可能传统农耕文明当中某些东西恰恰是工业文明所欠缺的?在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碰撞过程中,传统农耕文明中有没有我们需要保护和珍视的东西,比如工匠精神?
任剑涛:从结构上来讲,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面前彻底败下阵来,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去为农耕文明唱一曲挽歌。生在一个农耕文明过于深厚的国家,我们常常对农耕文明有一种浪漫的幻想,比如你提到的工匠精神。传统的工匠精益求精,一辈子做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他仅仅是为了做贡品,并没有拿来作为提升社会财富的普遍性生产手段。所以可能是你将之看得太浪漫了。那么,从功能或者要素上来讲,农耕文明有没有某些要素值得我们在工业社会当中缅怀、继承呢?当然有。

第一,就是你表现的那种浪漫情绪,因为工业社会没有给人太多的浪漫余地,高速运转的机器,紧绷的社会精神状态,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可能?但这个“悠然”可以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去想象。当然,农耕文明是不是真个“悠然见南山”?除了陶渊明这样的少数人,绝大多数恐怕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这少数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想象空间。
第二,则是你提到的工匠精神。古代中国那种制作贡品但精益求精的精神,对粗制滥造的低级工业生产、对于纠正当下挣快钱的社会风气会有帮助。换句话说,农耕文明某些局部的工匠追求,对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眼花缭乱、只挣快钱的社会,也可能是一剂良药。
第三,在某种情况下,农耕文明那种家庭的内在协作,能不能扩展为社会的广泛协作?也是有可能的。当然大规模的陌生人协作,是不是可以直接来自熟人的内在协作,还可以讨论。但可以给我们启发,则是一定的。此外,还有农耕文明对于人情的重视,对于传统习俗的看重,由血缘力量外生为一种社会动员方式等等,都有可能提供现实帮助。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先要把自己的农耕文明狠狠地摔在工商文明的铁板上,然后再做冰凉即理性的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