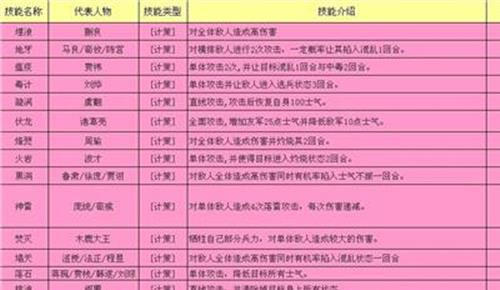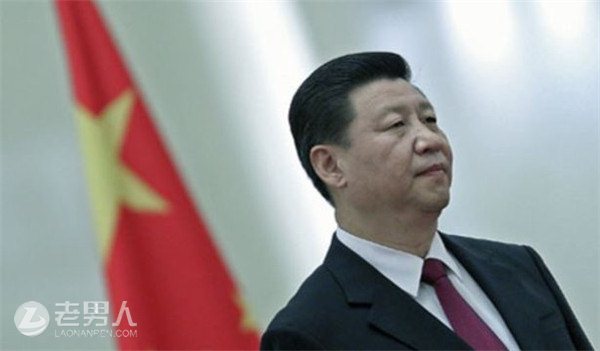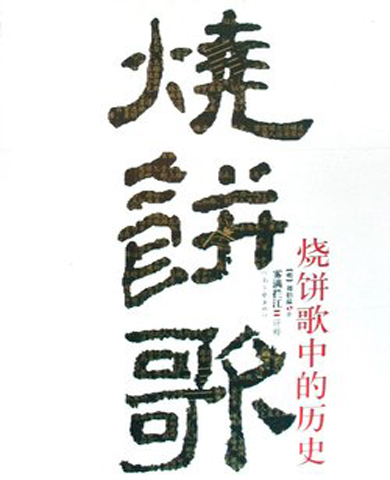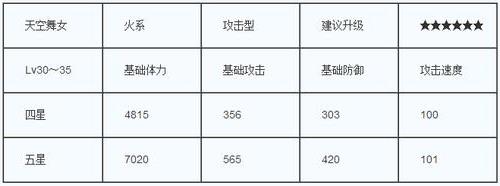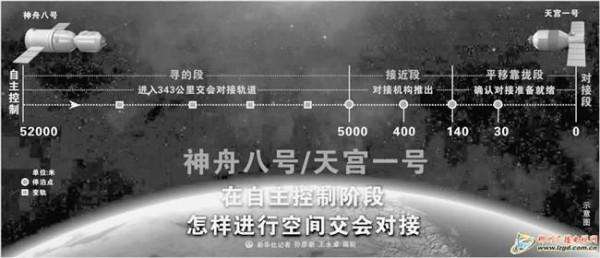任剑涛详解为什么基层官员容易被污名化

凤凰评论《高见》:在中国历史上,周代的封建制度造成地方过于强大,中央越来越弱。但是,周代延续了八百年,比后面的历朝历代都长。周代的政治体制,似乎有点类似于“联邦制”的形式。你怎么看?
任剑涛:如果要回到中国的传统,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西周是有稳定政治秩序的一个阶段,它历时275年,可以傲视后期王朝。到了东周,周代的制度运转已经风雨飘摇。因为东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封建制已经被新兴起来的诸侯采纳的各种制度类型,竞争性地取代。但是周代为什么能够维持到秦,才正式宣告“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制度的终结呢?这里面有几个因素要考虑。

首先,它是刚刚告别初民社会,建立的第一个重要的政治体。我们一般说夏商周三代,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晚期的重要标志,但是直到今天,通过考古还无法完整地勾勒出夏文化。它的物质文化可能看的比较清楚,社会文化也比较清楚,但它的政治建构主要出于传说。殷商通过挖掘,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真正可以全盘复原的是始于周。
对周代来说,它确确实实把初民社会的血缘控制机制,变为政治社会的人为控制机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所谓分封,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大宗套小宗。通过宗族的自然结构,扩张为一个政治社会的结构,我们最熟悉的家国同构就来自于周。这个自然秩序的扩展,是一种血缘控制体系,它运用是自然血缘不可变更的力量,把它改编为一种高度稳定的政治力量。

第二点,周代建国的国父们——文武王和周公,承继了中国原初社会的禅让制度,尧舜禹选贤任能,而不是直接的私相授受。文王本来可以当政,结果他没当政,他开创了以崇高的道德威望和先祖辈分为依据的齿序结构安排。这种政治控制机制使得道德变得非常重要,这属于高度稳定的机制,它意味着当权者必须站在道德高位,以免争权夺位。加之这种制度逐渐形成了一种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周代的政治非常稳定。
第三,周公开辟了叫做“敬德保民”的政治传统,掌权者不会极其恶劣地表现贪欲,起码在表面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行政秩序上把君王放得很轻,民众就不会造反。依靠这些,才延续了八百年。

秦始皇本来建构郡县制,它又想在中央权力上延续封建制,所以他开万世之基业,但二世而亡。原因就在于,他的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是错位的,中央机构就是我一世,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地方是通过选拔,通过郡县制的安排来治理。大多数人看到秦这个制度安排,于是就认为秦创造了很伟大的现代国家,福山就是一个典范,这给我们中国人以巨大的鼓舞。但是,这是个巨大的误会。分析制度结构就会看出来,它其实是错位的:它的中央政权是分封制,地方政权是郡县制,是一个怪胎。

凤凰评论《高见》: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说,它衰败的原因是什么?
任剑涛:周秦之变,经过了四百来年的运行,彼此征战,尸横遍野,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说到底,那就是面对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争权的局面,周的体制已经运行不下去了。今天我们大陆新儒家的朋友们,把周代的制度说的是花朵一样美丽,美轮美奂,感叹周秦之变的糟糕,说周秦之变是第一次败坏了儒家文化。要搞清楚,周秦之变晚期,儒家文化才出现,儒家文化就是要去挽救周秦之变而产生的新型秩序。
凤凰评论《高见》:周的体制运行不下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任剑涛:孔子强调,时也命也,他绝对不是捍卫周的制度,为什么?孔子也看到了,周的制度面临的问题,就是人类统一政治体的政治难题——三大行政矛盾。

第一,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考虑的统治对象,范围,结果,诉求和最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中央权力是通盘的,它把所有臣民当做一个整体。中央政府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而越是基层,越要脚踏实地。民众交了多少税收,地方政府想要更多,保持手头宽裕。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就必然搜刮民众,民众就会骂地方政府官员,中国自古至今就是如此。但是向中央缴了重税,中央给的财税分成又不够,地方政府怎么运转?没办法就只能讹诈,什一税的规定是规定,文明的官员收十之二三,不文明的官员收十之七八,再野蛮的官员收十之八九,最野蛮的官员把明年的税收提前给收了。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它的权力大小范围幅度的划分,使得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
第二就是人民难题。大家可能对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有统一的感受,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处境中,我在山东或者四川,我在江南和在晋城,那反应完全不一样。所以具体的地方民情或中央统一下抽象的人民,是不一样的。对于抽象的人民,中央政府可以站在道德高位,称自己就是坚持民为贵。地方政府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要是民为贵就很困难了,它一定要社稷为贵,代表皇权来维持地方运转。

皇帝尽可以讲民为贵,地方政府要守卫社稷,而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派出的.尤其是科举制正式成熟以后,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是皇帝给授权的。因此,从权力来源上来说,官员第一个要感谢的是皇帝,因而在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运转上,民众变得最微不足道,因为官员的权力来源于谁,它就对谁负责。因此就变成了名义上的君为轻,实际上的君为贵,所以这个行政统治秩序的第二个难题里就出来了。
中央政府的排序,展现的是一种道德姿态,因为地方具体课税,然后上交。中央政府吃的是间接税,在道德上可以很高尚,而地方政府越到基层越要负责实际征税,比如七品芝麻官,是最低级的官员,他必须和乡绅打交道,乡绅好就是良绅,不好就是劣绅,一群恶霸去收税,民众就会很反感,但是地方官员为了皇权不得不这样去统治。所以,第二重难题也就使得皇帝、社稷和民众产生了行政上的排序分离和严重错位。

第三,权力运作所体现的行政伦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也大不一样。行政权力越往基层走,冲突越尖锐。谈民为贵,在地方的实际运转中基本上不可能。他必须对民众征税,于是他的道德高位就在基层权力上彻底丧失,由此导致第三层问题出现。陶渊明挂冠,千古以来被视为文人典范,其实陶渊明作为县太爷想升知府升不了,他就辞职,是被迫的。行政权力必须要从低位到高位,如果不能,那就没有按照行政逻辑来发展,官员就没有动力。而一旦有行政动力,要取得上峰甚至皇帝的欣赏,就一定要通过权力运作的绩效表现出来,而很高的绩效往往意味着权力讹诈,于是权力应用的悖论也就出来了。
周代的崩溃,其实就是分封诸王跟中央王权冲突矛盾的结果,分封诸王想自己的权力大一点,还想有一点话事权。这个逻辑我们今天应该熟悉,比如说广东的顺德是一个县级建制,给它的是地级市的权力。为什么?因为它觉得县权力不足,比如它想搞一个大型投资,要市里批,等批下来菜都凉了。古今都要讲行政效率,地方诸侯想有更多的权力,中央不愿意让权,于是东周的崩溃是必然的。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说到的情况跟美国正好相反,基层官员因为要对上级负责,一直被污名化,一直都不受人待见,但是在美国,地方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的威信更高,越往上走,民众反而没什么感情。
任剑涛:这当然是不同的政治传统所致。美国开国前就有强大的自治传统,地方不需要中央政府干预,它已经通过互助运行得很有序了。在他们看来,干预就要征收联邦税,要加重税收负担,所以美国就形成了对中央权力警惕和怀疑的强大传统。一直到今天,联邦政府可为的事情不多。

美国国父们在设计政体的时候,唯独在外交和对外战争上,留给总统极大的自我决定权,其他权力包括联邦的征税权,都已经限定在国会和最高法院以及总统的三权分立格局里,总统只能对外有紧急权力进行宣战,绑架国会,支付战争拨款。总统对地方事务的干预权力非常小。比如美国哪个州遭遇到飓风,灾情严重,联邦政府说我来救灾,给你派军队,这个州说我不要你派军队,因为你有灾的时候你派军队来,你认为有正当理由,假如州在跟联邦政府冲突的时候,你认为也可以派军队来,那就危险了。所以,在能够自救的情况下,州不需要联邦政府出面。
凤凰评论《高见》:这跟单一制国家很不一样。

任剑涛:我们更仰赖高一级的政府。地方一旦遭了灾,中央政府不管派什么,基层都会欢迎,因为它带好处来了。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中国民众像瑞士联邦那样,公民全民投票拒绝每个月发福利,那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傻瓜。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单一制政体里头,地方会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中国从秦以来就是强干弱枝,中央政府权力大,中央一声令下诸侯闻风而动。然后到了现代,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政令出不出中南海。这不能一味的视作行政效率低,关键得看是什么政令,如果是事关国家全局、国家统一、国家主权的,政令不出来那就是国家危机了。如果中央事无巨细都发指令,地级或市级政府和实际管理的省级政府权力都被抽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话反而是好事。

凤凰评论《高见》:单一制下这种政令的上下级衔接方面,会有什么潜在的隐患?
任剑涛:单一制情况下最大的危机就是地方权力挂空,无法决策。但地方又得在第一线去领导民众,民众会以为权力就是它的,结果它的所有指令要等待中央政府发布,这种挂空会产生一种双重效应。第一,它没有前线决策权,在等决策权的过程当中会延误时机,因为前线的决策权必须是当下、及时的。县级政府请示市委(地委),市委请示省委,省委请示中央,等决策下来菜都凉了。

第二就是资源动员。地方政府的资源被上级和中央收走了,在应应对紧急状况的时候,地方政府手里资源非常稀缺,以至于必须中央权力调配分割。地方官员没有决策权,又没有资源动员能力,在民众面前就容易招骂,也就成了委过的对象,地方官员因此容易被污名化。
但是在联邦体制下,地方有自治传统,首先会强调公民之间通过互助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得来,因为公民对地方政府直接缴税,所以公民首先不是盼望中央政府,如果地方的资源、地方的权力确实已经无法应付这个紧急事件,那中央政府就必须出面,因为公民交了联邦税收。

凤凰评论《高见》:由此可见,纳税人意识的养成很重要。但中国民众在这方面,的确有所欠缺。
任剑涛:我们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基本的消费税都不打入发票和小票,一般人连税收意识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我在几个名牌大学任过教,学生说不要讲纳税人,我们现在还没工作没纳税呢。我说开玩笑,你任何一笔消费都在缴税。在美国,商品本身的售价、税收是多少,标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是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交了税的。于是,真正成熟的纳税人意识才有了。

纳税人意识不只是解决纳税人跟政府的关系,最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能够为社会自治做什么事情的问题。纳税人不知道纳税了,政府的权力很大,又对民众承诺民为贵,民众会觉得政府是全能的,来张口衣来伸手都应该。无所不能的万能政府把权力捆得死死的,因为大家可以对它提出无限的要求。
所以,在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政府的层级越往上,大家对它的要求和期待也就越高,甚至产生一种道德虚幻的自我安慰。但是越到基层,大家的要求越具体,基层政府因权力和资源的匮乏而无法成事,民众会骂得狗血淋头,基层政府就被污名化。这样的污名化,导致低层权力承担道德罪过和实际罪过,高层权力享受虚幻的道德满足感,权力之间产生了事实上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