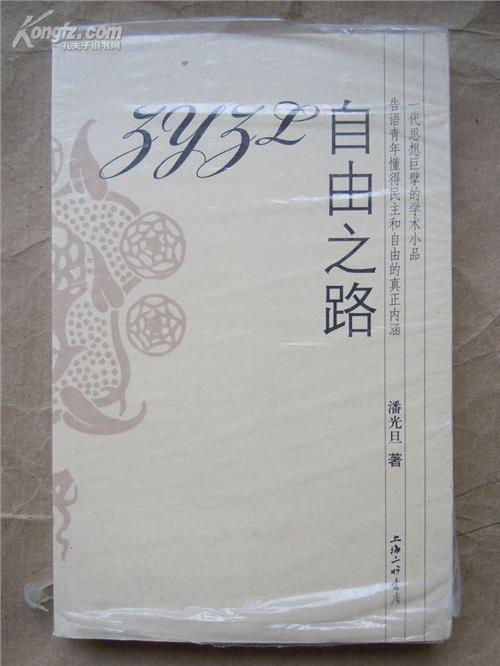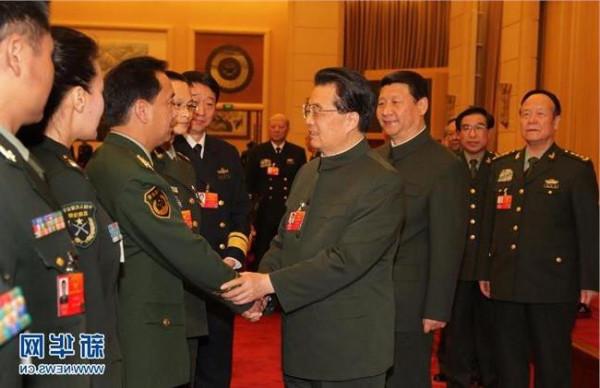潘光旦的人文思想 陈奎德:潘光旦: 新人文思想者
潘光旦(1899——1967),是上世纪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国学者之一,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其涉及学科领域之广,对中西文化造诣之深,可与陈寅恪等学人并列,堪称学界翘楚,屈指可数。
由于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根基,再加上他那过人的天资,他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运用自如。”因此,所提出“人文史观”,“新人文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实际上,早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梁启超赞赏曰:“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推崇至此,罕有他人。
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1926年,潘光旦学成回国。其后一直在大学任教。先后在上海的吴淞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职。
1934年,应梅贻琦校长之聘,回到母校,从此成为清华最重要的核心和骨干之一。曾任教务长、秘书长、社会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还曾两度出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在政治思想上,他一以贯之,倡导民主自由,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
在共产党主政后,由于1952年中国教育系统全面效法苏联,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潘光旦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1967年文革中备受迫害郁郁病逝。潘光旦先生一生涉猎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鉴于留学的师承渊源、鉴于时代的主流思潮,也鉴于中国当时情势等诸种原因,潘光旦的自由主义与他的知识界友人如费孝通、罗隆基和储安平(这些人是他的学生辈)一样,主要受到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费边社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的影响。
但由于潘光旦涉猎广博,所以他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海耶克的思想,在中国知识者中是最早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年出版,而潘光旦1946年出版的政论集《自由之路》就讨论了海耶克这本书,而且不是一般提及,是有详细的评介。
潘光旦说,海耶克这本书是专门就竞争在经济上的价值立论,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作为亲费边社的自由主义者,潘光旦虽然觉得海耶克较为偏激,但还是认为海耶克对集体主义的评论是很健全的。
在潘光旦看来,海耶克过去在奥国时受过苏俄式的集体主义压迫,又吃过德国式的集体主义的亏,所以对任何集体主义,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情感。潘光旦虽然不赞成海耶克关于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的思想,然而他很欣赏海耶克在政治上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批评。
当年中国自由主义主流虽然大多留学英美,但其时“英美自由主义”声音最响亮的不是以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所代表的以及海耶克所复兴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以边沁、密尔、拉斯基、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有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因此,潘光旦的基本想法,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很有代表性。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种在社会思想史研究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社会思想,他的“人文史观”,其核心是说:文化的发轫,要靠知识分子的思考,而文化要继续维持或代有积累,也要靠知识分子的努力。在当年,在民粹主义式的“劳工神圣”等口号响彻云霄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潘光旦这样的“人文史观”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赋有某种“知识分子中心论”的嫌疑。
但潘光旦并没有随波逐流去附和正在膨胀并日益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力量。潘先生择善固执,我行我素。
他的“人文史观”,是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因素的集大成,其中含有“遗传论”因素,对各种哲学决定论和本土思想传统进行广泛论述和筛选。他把知识分子对基本价值的守护,对文明的创新与发展,称之为接受历史的嘱托,承受文化的使命。这一论点,至今看来,仍是经得起历史风雨吹打的。
潘先生平生治学的特色:一头扎根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一头吸收现代生物学的精华,二者之间相互阐释,相互发明。而潘先生平生治学和为人,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自我”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从近代社会思想演变的规律来看,这“推己及人”的观点,带有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个人观念”的特定印记,带着现代性所赋予的“个人解放”的某种追求,但它的核心内容包含着一种以普遍的人类进化来论述民族命运的历史关怀,这种关怀的基本特征是知识的反思性与现实的人类行为之间的高度统一。
它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洞察中,人类的普遍性遭际与文化的特殊性遭际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当潘光旦把“推己及人”运用于民族关系上时,他雄辩地指出,既然我们不愿遭受他民族的支配,也就需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弱势民族,也就是中国内部的其他文化类型——即我们内部的少数民族“他者”。
他在“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一文中,提醒我们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们不欲受其他民族支配,则我们也不能去支配国内的少数民族。这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釜底抽薪式的化解。
作为长期从事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潘光旦对中国自由教育思想也贡献甚大。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讲“ 位育”问题,潘光旦先生最明确地宣明“位育”的意义的思想家,而“位育”虽然来自西方文化进化论的“adaptation”(适应)一词,它在潘先生那里却成为一个能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意义更为广泛的概念。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位育’是潘光旦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潘先生对“中和位育”作了很好的 发挥。潘光旦认为人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以“自我”为对象。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教师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自得于后。
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潘光旦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是“自由教育”的精义,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进入“自我”状态。
潘光旦认为中国近代教育中的德、智、体划分是十分牵强的,不能涵盖“健全的、完整的人”的全部内容,在教授方式上绝对划分也是不可能的。他在考察欧美教育时发现西方社会的教育旨趣有这样六个方面:关于健康的、关于财富的、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关于美的欣赏的、关于智识的探求的、关于政治和人我交际的,潘光旦将其归纳为德、智、体、群、美、富。
基于上述认识,潘光旦对当时的教育部门(1939年)在学校里设立训导处给予了严厉批判:近代教育把所谓训育从教育中间划分出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是失败的一个招认。潘光旦认为教育的对象就是人生,教育就是人生,学习与做学问的目的都是做人,学问不能离开生活而独立,如今把训育从教育里划分出来,使训育与教育成为并立对待的东西,其结果于受教者是有害无益的。
潘光旦还特别看重教师的言传身教,看重教师的表率作用。他提出要慎择师资,选择教师不仅要看他的学识多少,学问深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所谓学识与个人操守之间是否是贯通的,也就是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潘光旦认为教师风度的表率作用远远胜过训导中实行的那些生活戒条和所订的几种奖惩功过的条例。
潘先生属于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学术遗产,是相当丰富的,他的为人为学的自然自由以及中和谦冲的风范,堪称为中国的自由立言立德,足堪为人师表,垂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