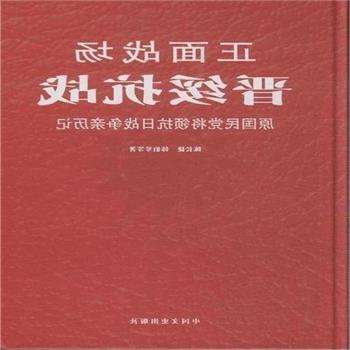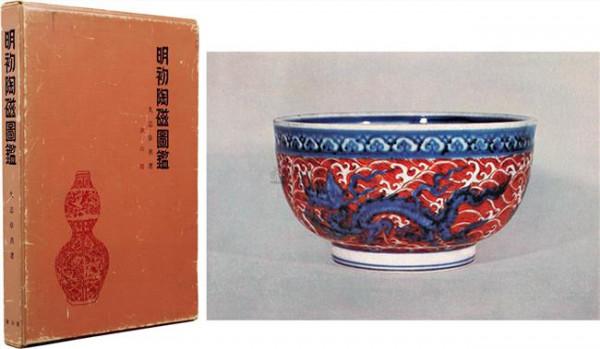杨献珍简历 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亲历记
45年前,发生过一场规模不算很大但影响不算小,涉及全国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的批判运动。这就是所谓“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它也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展开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大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是1964年夏到1965年春,主要论战阵地是以《光明日报》为首的报刊,主要斗争靶子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原校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著名哲学家杨献珍,主要批判会场是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以下简称中央党校) 我当时在中央党校机关党委秘书科工作,直接参与运动情况的汇集和资料的整理工作,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运动,而且经历了一些不太为人知的事情。现在,很多同我一起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当事人已不在了。
有些事档案上不一定有记录,所以感到说一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还是有必要的。 【康生认定“合二而一”是反毛泽东思想】 这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从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与林青山合写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开始的。
两位都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中年教员。 众所周知,“一分为二”是毛泽东给唯物辩证法下的定义。在个人崇拜极端盛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年代里,对“一分为二”的评价十分高。
作为普通的哲学工作者只有赞美和宣传的义务,竟然有人提出和毛泽东不同的解释和说法,岂不是胆大妄为甚至大逆不道吗?因此一看到这篇文章,就不免为他们两位捏了把冷汗。
不出所料,没过几天我所在的机关党委办公室就开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小会。会上办公室主任揭星光传达了校委的指示。校委认为:艾、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注意,目前,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还是当作学术问题看待,但机关党委要密切关注全校教职工的思想动向,随时了解情况,搜集反映,向上汇报。
我当时有点不太理解,提出为什么叫“当作”?揭主任说,你好好领会就是了,不必向外面说。
后来才知道,在艾、林的文章发表前,《光明日报》上报文章清样时,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便认定,“合二而一”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调和论,而且认为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抓出大鱼”杨献珍。 为了“引蛇出洞”,康生授意《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并以学术讨论的形式组织发表一批文章,赞成的、反对的都要有。
所以,“当作学术问题”,正是康生的政治圈套。可惜全国不少不明事底的学者上了圈套。凡是赞成“合二而一”或哪怕是出于礼貌而稍微有一点肯定的人,不管文章是否发表都被转送回原单位,遭到批斗,蒙受了不白之冤,这是后话。
稍后,揭主任交给我一项具体任务:办一份油印的简报,并要我去林枫校长的办公室直接听取指示。
我奉命到达后,林校长指示我:简报的任务是向中央领导直接反映中央党校运动的情况;不定期,每期不超过两千字;重点在反映思想状况,要有名有姓具体细致。简报由党办搜集情况,我一个人执笔写出稿子,然后报贾震或李一非副校长定稿。
校打字室指定一个人专责打印,共印30份,密级为绝密。印好后,校对清样和打字蜡纸都必须收回销毁。这是我第一次当面接受由林校长下达的任务,既感到有点紧张,又感到领导考虑得真是既具体又细致。
林校长还交给我一份他亲手写的简报上送人员名单。我记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有关的中央负责人如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
最初名单上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是后来让我补送的。同是常委的朱德记得没送,不知什么原因。校内主要的校长林枫和五位副校长贾震、李一非、龚逢春、艾思奇、范若愚也都送了。
每期印好后,由我一个人写信封,装封好之后直接交机要科,由内部机要交通送往中南海。那时给我的印象是党中央及最高领导人在直接领导我们战斗,并不像后来有人说,这些批判完全是康生瞒上欺下一手操纵的。
简报大约出了10多期,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期专门摘录了杨献珍1964年4月在中央党校新疆班的一份题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的讲稿。杨献珍认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
“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当强调一个侧面的时候,不可忘记了另一个侧面”,“事物本来就是由矛盾的两个侧面构成的,两条腿走路,而只抓住一个侧面不放,用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片面性”。
(转引自《中国当代哲学40年》,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的讲法显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这里顺便提一下,15年后的1979年,《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问题》一文,杨于文中解释说:“合二而一”是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提出的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简明表达方式,并非他自己的独特发明。
他提出“合二而一”“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然而,客观运动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这种“当作”学术讨论的过程很短,不到50天。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王中、郭佩衡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点名批判一位中央委员,当然非同小可,一下子就挑开了那层薄薄的学术幕布,改变了人们对这一争论的看法。当时就有校外的朋友向我打听,这王中、郭佩衡是何许人也?其实这二人虽然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在当时的中央党校只是一般的中层工作人员。
文章也不是他们两个写的,只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新疆干部班里工作,听过杨献珍的讲课,就被选为适宜的署名人。大概发表时比较急促吧,一个人名被写错了:郭丕衡写成了郭佩衡。
王、郭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中央党校内部就集中展开了对杨献珍及其支持者和关联者的公开批判。全校展开运动,设立了专门的运动办公室(称南院办公室)。我被编入南院办公室简报组,出版铅印的运动简报,那份小范围的油印简报也就停刊了。
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就在这个简报组工作。简报组共5人,由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里的一位老教员任组长,组员有校办秘书科长、组织处一干部和我,另有一位教务处的女同志管文件资料的收发。
为了迅速反映情况,经常是晚饭后汇集全校运动情况,再研究分几个专题整理成简报,然后分头连夜编写,清晨送校印刷厂。第二天上午把印好的简报送给有关领导。这样,开夜车成了家常便饭。我的头发就在连续开夜车的过程中,日见稀疏,开始秃顶。当年我只有32岁。
【被陈伯达辱骂的孙定国投湖自尽了】 从1964年7月到1965年春,校内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批判会开了无数次,其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三次: 一次是以哲学教研室为主,有艾恒武、林青山参加的小会。中心是追查他们的文章同杨献珍的关系。
这两位作者承认是在听了杨老在新疆班讲课后,感到受了启发,认为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更丰富了,才立意给《光明日报》写文章的。林青山表示:现在认识到文章观点有错误,愿意检讨。
艾恒武则对文章是否有错误一直沉默不表态。不管别人怎么批判、劝解、诱导,不管别人说什么,两人都坚决否认写文章是受杨献珍指使,连“授意”、“暗示” 也不承认,强调文责自负,和杨献珍没有任何关系。会议僵持不下,无果而散。
不过,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只要是领导已确定了的大批判对象,无论当事人有何种辩解,都是不起丝毫作用的。 8月下旬,《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报道员”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文章以极其严厉的措词把批判提到一个政治新高度。文章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论战双方的阵线分明,针锋相对。
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论,就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
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篇从政治上给“合二而一”论定性的文章,给人们的思想震动很大,要求必须进一步扭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央党校在大礼堂召开了全校学工人员1000多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会议由校长林枫主持,主讲人是范若愚。范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副主编,也是《红旗》报道员文章的主要执笔人。
范若愚坐在讲台上,一支又一支地吸烟,声色俱厉地历数杨献珍的所谓各种错误观点,上纲上线,主调当然就是上引那篇《红旗》的文章。这位马列学院一期毕业的高材生、杨献珍特意选留中央党校的理论骨干,大概是为形势所迫,批判起自己的恩师毫不留情。
(这里顺便说一下,范若愚后来的遭遇也是不幸的,特别是“文革”中曾入狱多年,令人十分惋惜和同情,这也使我深感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
)这次全校批判会,杨献珍是到会的,不过没有坐在讲台下,更没有低头站在讲台上,而是坐到后台的贵宾室里,通过扩音器听批判。“文革”时期就没有这样的文明待遇了。 第三次印象深刻的批判会,是陈伯达在全校批判大会上的报告。
时间大约是放寒假前。陈伯达的著作看过不少,但直接听这位理论家作报告还是第一次。遗憾的是,陈伯达的福建话实在难懂,两个多小时的讲话没听懂几句。唯一听明白的是他让孙定国(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当时已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因“合二而一”又调回北京参加运动)站起来,并在1000多人的大会上当众骂孙定国。
陈伯达说,他的一幅没写好的墨迹扔在废纸篓里,被孙定国捡回去裱糊起来挂在墙上,真是“死不要脸”。
全场顿时哗然,孙定国十分难堪。事后听亲眼见过这幅陈伯达字的人说,悬挂在孙定国家里的条幅上明明写有“定国同志嘱书”的字样,怎么会是从废纸篓里捡到的呢?孙定国抗战时期就担任过晋察冀边区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员,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学院一期毕业后留校从事理论工作,而且卓有成效,成为知名的哲学家。
难以承受这样当众凌辱的孙定国,此后一天夜里就在党校院内的人工湖投湖自尽,钻进冰窟窿身亡了。
不少人说陈伯达“文人无行”,“文革”往事已让陈伯达的人品有了公论,孙定国也早已获平反——这件小事存此以证“大批判”之荒唐与无理吧。 校内批判运动到放寒假时基本结束了。此后,我们简报组的任务就转为协助各单位起草修改各种处理意见和处分决定。
批判“合二而一”,绝对不限于杨献珍本人和少数写过文章的人,而是株连一大批人。那时搞政治运动的特点是“上挂下联,成串成批”。杨献珍当时往“上挂”尚不好办,到“文革”时就“上挂”到“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了。
“下联”更厉害,杨献珍的所谓亲信、骨干、学生中有多人无辜遭殃。除了前面提到的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外,还有原副校长侯维煜、党委副书记兼组织处处长伍辉文、校办副主任王介山、教务处副处长王莹、党史教研室主任李践为、党建教研室副主任周逸、行政处处长郝沛霖等。
整个中央党校当时的全部教职工不过一千几百人,而在这场运动中受批判和受处分者竟达154人,超过10%。其中有些人“文革”中再受折磨,比如哲学教师黎明被开除党籍,下放河南,“文革”中不堪凌辱,投井而亡。
全国各地被批判斗争者没有统计。听说有的干部仅仅因为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听过杨献珍的课,或者在平时对杨校长稍有赞誉之词,便被打成了杨献珍的“徒子徒孙”,受到各种迫害。
这样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196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文章:《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
文章认为毛泽东提的“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合二而一”不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和革命辩证法根本相反的东西。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对这场论战的理论总结吧。从此之后,报刊上就不再有这个问题的专门文章了。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办公室解散,我又回到机关党委办公室,但半年后又被逐步卷入一场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风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已被调离中央党校,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的杨献珍,又被揪回党校再遭更残酷的批斗。不过,这已经不属于这次“论战”的范围了。
(作者系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