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芙蓉国 柯云路:中国最会“变脸”的作家
“为什么后来我写李向南容易写?不仅是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物,也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带着这样政治性的理想:改变社会”
柯云路的作品似乎总是与这个社会的热点关联在一起。
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出轰动一时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新星》,而后在众人的期待下却转而研究中医、气功乃至人类“神秘现象”,他因与无证行医而致多人死亡的“传奇神医”胡万林纠缠在一起而广遭诟病,他又在育儿、情感、婚恋问题上给众多咨询者以“指导”。
因此,有人称他为“中国最会变脸的作家”,以及“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柯云路无疑是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作家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如此评价,“可惜有时候野心太大,现在的社会一个人只能做好一件事,他做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是耗费了他的黄金年华。”
如今的柯云路已年过六旬,依然每天在家勤奋写作,早晚都练习打太极拳,遇到小病小灾则自行针灸治疗。
“以前总是拒绝记者,现在还想着给自己混点儿人气,呵呵。”9月20日上午,柯云路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戴眼镜,穿夹克衫,语气随和,谈起文学滔滔不绝,而触及人生最受争议的部分则一言带过——“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新星》奇迹
说起来既幸运又悲哀,柯云路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新星》,就使他到达了创作生涯的最高点。
这部长篇小说以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为主角,讲述他在县城大展拳脚进行改革的故事。果断有魄力的李向南在短时间内政绩斐然,被群众誉为“李青天”,他不可避免地遇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抵制……
在那个人人热衷讨论政治问题、改革开放的年代,《新星》引发了后来的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社会影响。
小说最早发表在1984年《当代》增刊上,反响强烈,被全国多家大小报刊转载。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短时间内加印多次,卖出几十万册。
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小说连播形式播出《新星》。
高潮在1986年来临。
该年,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期间的黄金时段播出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12集电视剧《新星》,省级电视台先后播出两遍以上,近乎奇迹。在《射雕英雄传》、《上海滩》、《霍元甲》等香港电视剧大行其道的年代,《新星》凭借其改革题材所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共鸣位列当年的收视率冠军。
一度,人们会把本地的贪官污吏都称为《新星》中的恶官僚“潘苟世”,山西某地甚至还出现了“苟世街”,当地人民以此称呼官员们集中居住的街道。
“社会充满了动荡和对变革的要求,人们都很有故事”
写出了《新星》的柯云路,那时是山西省榆次市锦纶厂的一名戴着眼镜的工人,38岁。
他住在厂内一间半的平房里,没自来水,每天的必要任务就是出门提水。经常,他出去提水回来,就会发现门前停着一两辆自行车,“有拜访的文学爱好者来了。”柯云路对本刊记者回忆起陈年往事,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在山西已经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他的“小有名气”是因为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千万》,1980年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那时,他还没有用“柯云路”这个笔名,署名用的是本名鲍国路,凭这部小说,他在1983年就加入了山西省作协。
此后,他门前的自行车就多起来了。有的怀揣自己的作品“请鲍老师指导”,有的因为生活困难慕名来借钱,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带来“冤假错案”的资料希望他帮忙。
“那时候的中国,作家有特殊的位置,有点像社会代言人。”柯云路记得,那时来的人有榆次市的,有下面农村的,还有附近县市的,“你才知道文学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社会问题又有那么大的普遍性。”
《三千万》之后,柯云路写过几部中短篇小说,自感并不成熟。多年后他不断再版其他作品时,一直恪守一条原则:《新星》以前的作品绝不再版。
在他的心里,《新星》才是自己货真价实的“第一部”。
“《新星》是我实现早期文学梦想的尝试,我希望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样,用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写社会生活、写众生相。”柯云路说,那时他一直希望能写一部长篇来概括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感到“社会充满了动荡和对变革的要求,人们都很有故事”。
“可以说,现在省一级的、地市一级的、县一级的干部,基本都是《新星》出版时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我现在有时去各省市走一走,他们还会跟我聊《新星》,有的还问我李向南的原型是谁,李向南最后到底跟谁好了。”
“年轻时我也有李向南式的抱负”
“熟悉我的人都认为,我能写出《新星》以及后来的作品,一点都不稀奇。”
柯云路生于1946年,出生在上海,成长在北京。他不喜欢透露自己早期的家庭背景,向本刊记者叙述的个人史始于1963年,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读高一的时候。那也是他文学梦想开始的时光。
他回忆,在高一的第一堂作文课上,他奋笔疾书,语文老师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课后老师问他:“你对文学感兴趣吗?”他说:“感兴趣。”于是,少年柯云路成了校刊《圆明园文艺》的副主编,一学期后又成为主编。《圆明园文艺》每两周出一期,从全校36个班级里挑选学生的优秀作品,找写字好的人用钢笔抄在稿纸上贴出来,每期可以贴满三个大玻璃橱窗。
那时的柯云路爱好读书,读中国的四大名著,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但他最爱的却是哲学,“原来愿望是当个哲学家,第二才是文学家。后来发现我只能当文学家,当哲学家困难。那时候并不太适合出哲学书,只要发表一点见解就是‘突破禁区’,研究哲学就很吃亏,很多话不能说。”
中学毕业时,“文革”也开始了。
1966年11月,北京农大附中两名学生化名“伊林、涤西”,在清华、北大等高校贴出大字报《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质疑林彪的一些言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不符”。柯云路读到这张大字报后很兴奋,当即找到这两位作者表示支持他们的观点。后来,那两位中学生被逮捕,搜查人员查获了他们的谈话记录,又抄了柯云路的家,“批判我的大字报从圆明园一直贴到(北京)动物园。”柯云路回忆。
两年后,柯云路和十几个中学同学一起下乡到山西晋南的绛县,开始了挣工分、集体开伙的岁月,一呆就是四年。
“开始的两年我还有点志向,老想着帮农民脱贫,一年四季拼命干活。”柯云路说自己帮助村里创建了全村第一个集体豆腐坊、第一个集体养猪场,发展多样经济。假期时他还领着村里一些知青回北京协和医院学习针灸,在北京买了常用药,回到绛县农村给村民义务治病。
“我对中医的兴趣和研究就是那时开始的,到现在我的针灸也很准,因为都是在自己身上练出来的。”柯云路回忆。
在山西农村的后两年,柯云路突然意识到自己再怎么干农村也脱不了贫,还是有很多农民吃不饱饭,于是跑了很多山区、农村进行调查,最后他发现“农村贫困的原因是生产体制问题”。在这个调查过程中,他接触了社会各层面的人和机构:农民、干部、乡里的、县里的、粮食收购站、加油站、棉花收购站……
“那时我老是在研究社会怎么发展变化,带着李向南式的抱负。为什么后来我写李向南容易写?不仅是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物,也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带着这样政治性的理想:改变社会。”
“他是属于80年代的”
《新星》之后,柯云路借势推出了其续篇《夜与昼》、《衰与荣》,反响依旧轰动。
此后近10年时间,柯云路几乎放弃了文学领域的写作。直到1997年,他才接连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主题已然变成商界沉浮和情爱纠葛。
在今天的柯云路看来,“80年代那种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的文学突破和先锋尝试过去了,作家的社会代言人地位也变化了,商业气氛开始蔓延,这对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他那三部描写商人世界和情感嬗变的作品并没有获得成功。
2000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芙蓉国》,从乡村到京城各个阶层描述“文革”的全过程。小说作者署名“辛克”,后被证实就是柯云路。他解释是“文革”题材过于敏感,因此匿名出版。此后,他以“超过阅读速度的出版速度”(司马南语)又出版了四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2000年的《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2001年的《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但都反响平平。
2002年,《当代》刊载柯云路的长篇小说《龙年档案》,这部小说回归了《新星》的道路,以当时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为原型,讲述了新的历史时期下市级政府改革者的经历,并具体翔实地描写了政府机构的运作和中国社会生活的演变。
小说出来之后似乎又像当年的《新星》那样受到了关注,几十家电视台争相购买电视剧改编权。但它显然无法再复制《新星》的轰动。
时代变了。用陈晓明的话来说,90年代以后改革就不是文学的话题了,那是实干家的事情,“柯云路是属于80年代的”。
柯云路目前最新一部小说是《父亲嫌疑人》,被他定义为“概括了现在两代文化人的关系”。
联想到当今80后作家如日中天的态势和众多“老牌作家”的日渐式微,柯云路下面这句话让人感慨:“80后反叛长辈,既是对长辈的超越,又是对长辈的‘屠杀’。”
“我知道……但我就是做了”
“我的创作领域有三大块:文学、社会学、生命科学。”柯云路不止一次这样解释自己的“变脸”,“只不过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写了小说,大家就以为我是作家,但我在作家之外,还可以做一个研究者。”
1988年,柯云路转向东方神秘主义主题研究,陆续发表多部关于气功与特异功能的著作,包括小说《大气功师》、论著《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中国气功大趋势》、《中国气功九大技术》、《生命特异现象考察》等等。
柯云路关于“生命科学”的书又一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据称当时《大气功师》一年内就加印五次。不过,他以作家的身份介入生命科学的研究,这种似乎“捞过界”的做法引起了很多文坛和科学界人士的争议,以及猛烈的批判。
“我做了一些非文学领域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但我不后悔,其实我现在也还在研究(生命科学),只是不出书了。”柯云路对本刊记者说。
在气功研究之后,柯云路又纠缠进一个人生中再也绕不开的事件:胡万林案。
有关此事的争论一直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柯云路与胡万林勾结,骗人赚钱;有人认为柯云路也被胡万林欺骗了;但柯云路自有看法,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及此事,他缓缓说了一句:“这是个冤案”。
“那几年我经历了人性的至善与至恶。这事给我带来的影响特别大,我为之付出很大代价,但我不后悔。”柯云路说,“人不能太功利,历史就是这样的。”
无论外界如何争论,柯云路一直坚持写他的书,保持一年三四本的速度。每天写作,写童话、写马俊仁、写子女教育、写情感问题、写婚恋指导……
“他对文学贡献最大的还是《新星》,在当时的形势下实现了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起到了开头的作用,可惜之后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作品了。”文学评论家解玺章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柯云路去做“生命科学研究”,解玺章认为至少是“走了弯路”。
外界的评价和惋惜柯云路似乎都知道,“我知道我的那些作品跟我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我就是做了,”停了停,他又对本刊记者说,“过两年就不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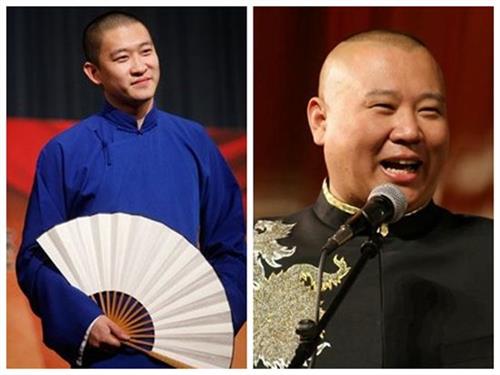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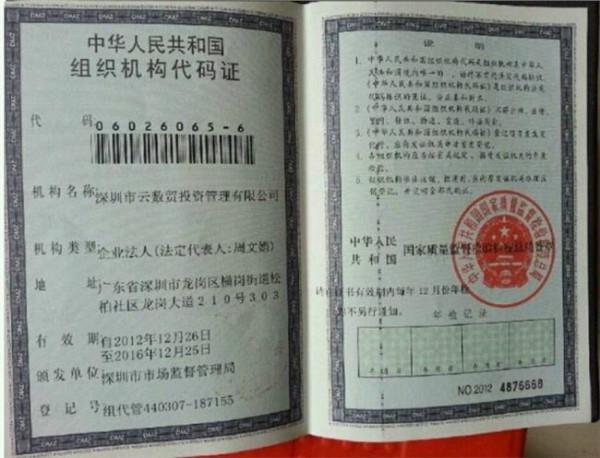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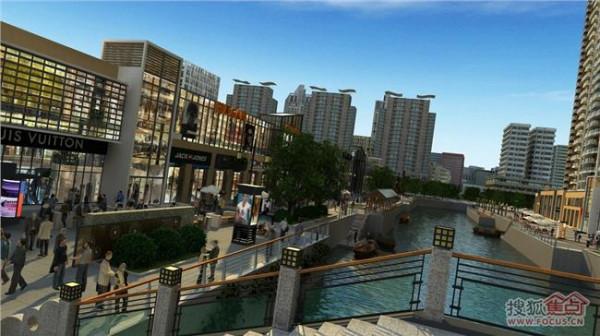





![>柯云路灵异 柯云路掀起工作革命:心灵太极[TXT] BY: 柯云路](https://pic.bilezu.com/upload/3/7c/37c5ddaa4641286bc3129054b28174f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