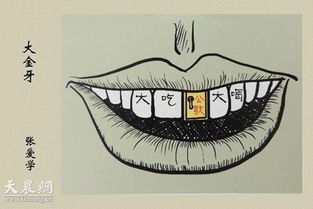张兆和沈从文其二 沈从文曾苦追张兆和引反感 校长胡适劝其放手
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善意地笑了,宽容了他的惊惶。
他便是沈从文。
他的学生里有一位18岁的少女,极其清秀美丽,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三小姐,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她便是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牗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在合肥老家,张家有万顷良田,光是收租就能收10万担。张冀牗担心久居合肥会让子女沾染世家子弟奢华的积习,遂举家搬迁到上海,而后,又迁居到了苏州,从此在这婉约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来,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他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三三),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
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沈从文那时出版了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人也生得清秀斯文。
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公学讨论得沸沸扬扬,给张兆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里。于是,她带着沈从文的一沓子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
没想到,胡适并不站在她这方,反而大力夸奖沈从文的天才,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地写着信。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也许是那海滨城市比上海宁和,他的信也变得端然静好起来。
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寻死觅活,于是,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回到苏州,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
那天,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情书的沈从文。允和邀他进门坐坐,他却执意走了。
也许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动了允和,张兆和回来的时候,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允和对兆和说:“你去了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于是,张兆和去了,站在旅馆门外,老老实实地将姐姐的话一字不落地背出来,于是两人一起回了张家。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4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迸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中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中国公学被叫做“黑凤”。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了。往来书信后来汇集出版了,就是《湘行书简》。
1938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去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她也依旧回着,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建国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呈现,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