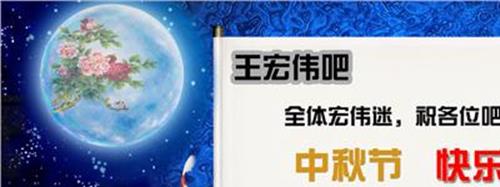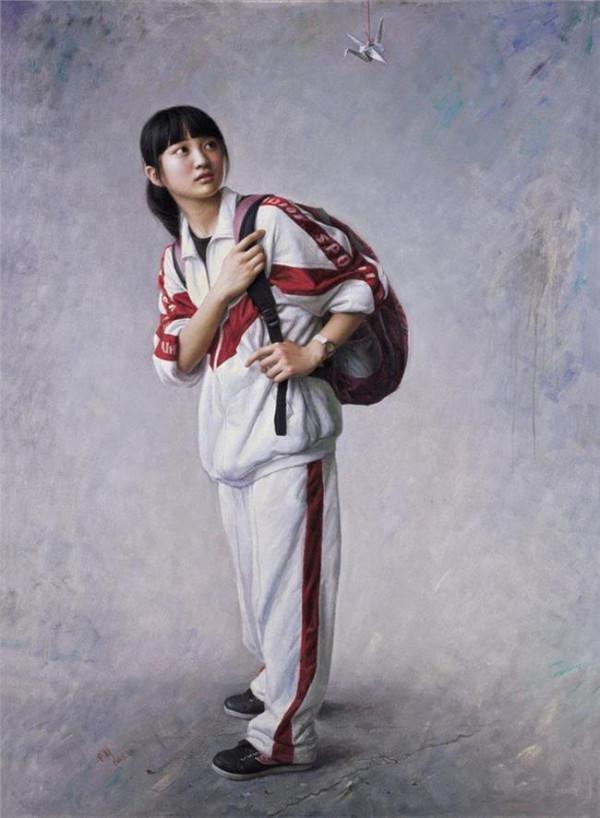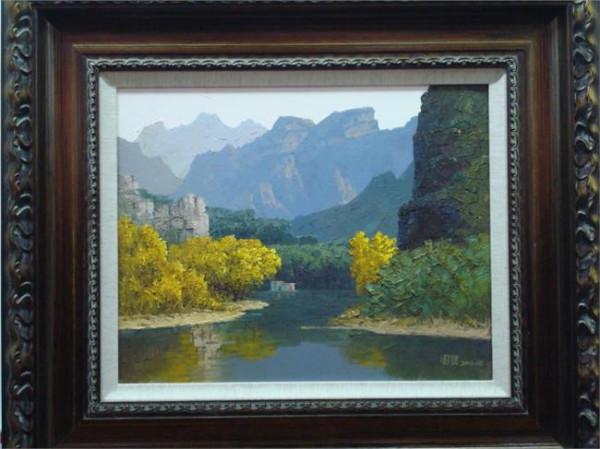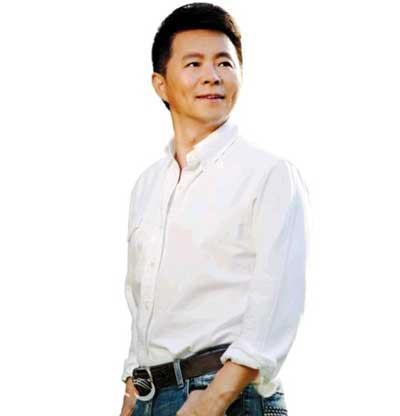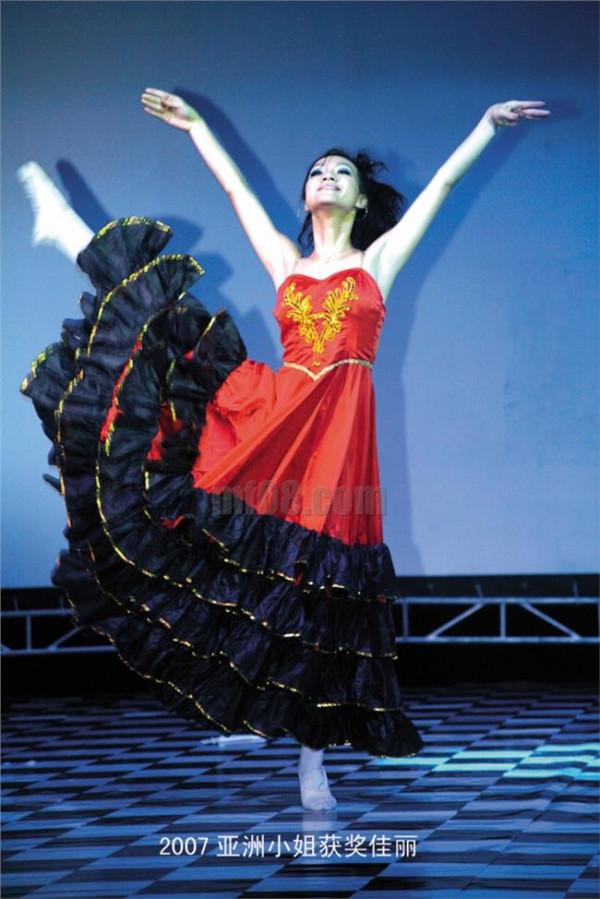王宏伟油画 王宏伟: 大众为什么疏离美术?
王宏伟,1984年生人。先后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美术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现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工作之余绘画,习书法。

大众为什么疏离美术
文/王宏伟
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作为社会文化艺术子系统重要门类的美术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官方及民营美术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新的艺术媒体与报刊不断涌现;十几年来各大院校普遍开设美术专业,接受美术教育的人数相较以往极具膨胀,看起来美术事业繁荣兴盛,艺术盛世似乎就在时下。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走进美术馆的基本是专业美术工作者或与此相关的人员及美术专业的学生,一般观众,如公务员、知识分子、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体力劳动者等等如果对美术没有爱好是不会走进美术馆观看展览的;美术媒介(美术书刊、杂志等)的观者和读者更是此一群体中的部分人员,普通公众往往绝不会关注和阅读美术的消息和动态(有此爱好者例外)。

所以,实际的状况确实是,大众并不关心美术,大众无所谓自己与美术的关系。以致有的学者追问:“……美术馆和画廊里的艺术,前卫和后卫的艺术,至今还在狭窄的专业圈子里打转,也就只能成为阳春白雪和空中楼阁。美术,真的就是那样脱离日用、晦涩难懂、不能与大众共舞吗?”
“大众”是谁?
既然我们说大众在疏离美术,那就有必要弄清楚是谁在疏离美术?这里的“大众”究竟意指何人?“大众”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意指“民众、群众”,言下之意,大众说的是一个特定地域里生活的人群。“大众”这个词所包含的人群应当是非常广泛的,以美术为分界点,“大众”可以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美术工作(含与美术相关的工作)的人群,另一类是完全不从事美术工作的人群。
一个肯定的答案是,从事美术工作的“大众”是不会疏离美术的,美术家、设计师要创作,理论评论家要研究,美术教师要教学,美术专业的学生要学习,美术事业的管理者要经营,这些“大众”以此为业,赖以生存,每日都在走近“美术”,断不可能与美术疏离。
那么,疏离美术的究竟是哪部分“大众”? 如果笼统一点计算,自然是不从事美术工作的那部分人群了。
其实,我们都明白,所谓的在疏离美术的“大众”是指那些不以美术或与美术相关的产业为业的以及没有美术爱好,对美术不关心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如公务员、知识分子、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体力劳动者等等从事各种行业,各个阶层的民众。
“美术”何指?
《美术观察》杂志曾作出调查并得出结论,美术的影响力在近几十年来逐渐式微。那么我们追问一个问题,“美术”具体何指?是什么样的“美术”的影响力在日渐式微?在此有必要简要梳理“美术”这个词的内涵。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语汇中,“美术”一词是近代舶来品,它最早在十七世纪被欧洲采用,是从西方经过日本以汉字意译后融入现代中国语汇的,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
”鲁迅在文中对“美术”进行了说明,“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问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
这里鲁迅按照柏拉图的解释将“美术”一次等同于现在的“艺术”,就是说,“美术”一词最初与“艺术”的内涵是相同的。与此同时,加上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推动(如蔡元培发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号召) “美术”一词在社会和中国语汇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后来,“美术”一词的内涵有所变化,成为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相并列的“艺术”的一个子系统,其既包含绘画、雕塑这样的非实用美术,也包含工艺美术、环境设计等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实用美术。
实际上,在今天“美术”一词的内涵包罗万象,并且仍然在不断变化。杨晓阳先生曾提出“大美术”的概念,认为“大到一个国家、城市、地区的面貌,小到居室、餐具、食品、钥匙链等任何能够‘看’到的小物件。‘美术’就是创造‘美’的视觉形式的‘术’……它可以包括创造纯粹供“审美”的、非实用的形式,也可以包括创造实用的使用的物品,还包括将现有的东西按照美的法则来排列、置放。
在此基础上理解‘美术’的范畴,就可以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美术、环境美术、设计美术、装置美术、服装美术,以及一切民间美术和随着新生活需要而诞生的全部新的物类美术……”这也并没有背离一般意义上对“美术”的理解,即在用途和目的上,美术大体有上文所提到的两个种类,一是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作品,二是以实用为目的实用美术,绘画、雕塑是美术,建筑、广告、书籍装帧、电影场景、日常服饰、环境设计也是美术。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在疏离美术的命题是难以立得住脚的,因为无论何人,在实际生活中总要进行穿衣、居住、读书、看电影等一系列的活动,这其中,“美术”又与我们的生活的难以分离,息息相关的,大众似乎也不能疏离由这些活动而带来的与“美术”的关系。
所以,我们所认为的大众所疏离的“美术”,是指那些由艺术家通过具体的材料和手段,以艺术欣赏和收藏为目的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即邓福星先生在《美术概论》中所指的“纯美术”是也(下文如无特别说明,所提“美术”皆指此意)。
大众为何疏离“美术”?
历史的影响
其实,在明清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还是有着相当的关联的。在清代直至民国时期,家境殷实的中国家庭一般都会在客堂或其他居所挂上字画以供欣赏,谚语云“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这是基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艺术生活传统而形成的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艺术接受和审美方式。
但这种情况在上世纪、特别是上世纪中期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把中国的传统艺术分为劳动人民的优秀遗产和统治阶级的封建糟粕,对为中国人原来所普遍接受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展开激烈的批判,很多优秀的画家被迫进行思想改造,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价值被抛弃。
特别是经历了前无古人的“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的摧残后,中国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欣赏和识别能力几乎丧失殆尽,“民族虚无主义”蔓延,传统的绘画和艺术生活方式等在大众的生活中消失了。
本来,以阶级分析理论对于传统的艺术的批判性继承是为了使其大众服务,但这一方式在具体的执行者手里被推向了极端,不但传统的文人画被全盘否定,甚至中国画本身也被宣称“必将淘汰”。当然,这其中也有在中西文化交融下,社会文化转型的客观原因。
几乎以此同时,西方传来的油画虽然在“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指导下进行了“油画民族化”的实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油画在20世界下半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进入大众的生活。
在油画取得极大发展的几十年中,其是以一种反应大众生活面貌的宣传品式的艺术创作出现在大众面前,其看似与大众相关,但实际上与大众的生活并没有产生内在的血肉关联。“文革”结束后,清醒过来的人们突然发现,一些标榜“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作品,竟是那么千篇一律、空洞和苍白,难以为大众所真正接受。
虽然在今天,无论是在尊重和恢复传统艺术,还是在对外来艺术的吸纳和中国化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笔者还是想补上一句,公众对美术的陌生和漠视显然来自于其自身的物质生活不足和文化修养的断层与缺失,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鱼翅燕窝远不如羊肉土豆来的实惠。
国人的实用主义观念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这是有道理的。作家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说:“……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
实用主义的观念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从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到今天略显繁杂多元的现实,尽管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主题精神价值,但我们要承认的是,在我们的观念中,不论是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一个恒古不变的核心精神就是所学、所做、所求都要对自己有实际的用处,否则何必牺牲时间精力于此?事实上,在当代国人的生活中,读书求学有着实用目的,研究写作也有着实用目的,乃至很多人日常交友也以有用与否为目的。
不客气的说,实用主义才是今天中国人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哲学。而美术,尤其是直接关旨精神生活而没有实用价值“纯美术”,在很多国人的观念里,往往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从中也得不到实际的益处,故而在国人是生活中完全是可有可无。
面对包括美术在内的许多艺术形式,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的,而并不是、也不可能发自内心的去走进艺术。换言之,艺术对自己有利,便去认识它、学习它,反之,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艺术无论占据了何等位置,普通的大众是不大情愿去走进和关心它的。
艺术教育的问题
艺术欣赏、艺术接受需要学习,需要艺术的欣赏者和接受者受到相对完善的艺术教育。然而回顾我们受教育的历程,不难发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所接受的艺术教育基本是支离破碎,甚至是完全空白的。由此导致艺术知识和艺术修养的严重匮乏,不足以支持艺术欣赏活动。
在长期的以升学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中,艺术教育的地位显得尴尬而难以自处,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和提升,直到学生进入高校学习,也往往难以描述基本的美术史知识。普通大众遑论品评美术作品的优劣,就连基本的画种也难以辨认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没有接受过艺术教育的大众走近艺术、熟悉艺术,岂非痴人说梦?
另一个问题来自专业美术教育。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特别注重在教学中对技法的传授,这样的教育模式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探讨,著名艺术史家陈传席在20年前就认为:“当代美术教育,以技术培训为主,无论从培养画家,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而言,皆不可取……所以美术系的学生除了绘画技巧外,要特别注意文史哲、数理化方面的学习,而且必须对其中一种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甚至有所研究。
否则,进行较大的创新(而不是大同小异的自然变化),只能是一种空想。
”以后又有论者不断地对这种艺术教育方式进行了反思。这种教育方式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接受美术教育的学生的文化修养严重下滑和缺失(这也是当代中国美术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让大众对艺术教育的目的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将其当做一种谋生的技术学习,一度将其蔑称为“小三门儿”之一。
“美术”本身的原因
上文已述,大众疏离的是那些以艺术欣赏和收藏为目的而创作的“纯美术”。这种“纯美术”往往是艺术家遵从个人内心情感而创作的作品,一般论者都认为这样的艺术具有精英性,与传播相对广泛的“民间美术”不同,所谓精英艺术是也。
精英艺术除了相对较高的技术难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创作的动机往往是个人情感和才能的抒发与展现,而不会遵循普通观众的意愿,倪瓒就曾说“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这就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得艺术创作先天具有小众性,决定了其难以向工业产品那样,目的就是为适应大众的需求而生产。
事实上,在美术史的长河中,尽管可以列举出数量巨大的人物名字和作品,但绝不能否认的是,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无论是西方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赞助,还是中国上层社会的种种艺术活动,这种具有精英性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及收藏都是少数人的事情。
故而王洪义指出,“精英绘画(笔者认为也可理解为精英艺术)的物质形态,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创作,另一部分指收藏。这两部分内容都与社会等级有关,没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专业技术的非精英大众,通常不会与精英绘画有什么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除却作品外,在大量的艺术家的论述和访谈中,往往将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思潮等宏大,但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抽象概念述诸笔端,以体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理想,这对以当下中国的普通观众而言,显然是难以像一般的综艺娱乐那样容易亲近的。
再者是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盛行以来,各种观念盛行,新的艺术样式不断出现。这种令人乱花缭乱的不断翻新促使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以文化精英的身份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份子从事艺术创作,而往往无视其与公众的关系。百余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但大众对艺术的理解和接受似乎更模糊和不屑了。
“美术”功能的削减与艺术市场中艺术品审美价值的缺失
在历史中,“美术”在不同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有着具体的功能,但总的来说不外乎画(塑)像存形、宣传说教、艺术收藏、装饰宅邸、欣赏研究、图示文字等几种。在摄影术发明之前,“美术”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多实际的用处,其既是社会管理者用于宣传和维护秩序的工具,也是用于纪念人物、画(塑)像存形的唯一手段;既是象征社会地位的财富收藏和宅邸装饰的理想选择,也是仕人们用于寄托性情、相互交往的最佳媒介,可以说在当时很多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美术”的具体参与。
摄影术发明并逐步推广、以及由之带来的电影等艺术形式出现后,“美术”的很多功能被其他艺术形式所逐渐取代,社会原本赋予“美术”的重要意义被大大地削弱了,致使“美术”不得不凸显其与大众生活相对较远的人文价值,以艺术欣赏和艺术收藏的方式而流传于世(其实“视觉艺术”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无奈和不得已的意味)。“美术”的社会功能的削弱直接影响了大众与其的关系。
然则雪上加霜的是,当下“美术”的人文和艺术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艺术市场的挑战。以绘画为例,在今天的中国,很多绘画作品往往流传于作者、经销者、收藏家等人只手,而与大众的关系微乎其微。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当下数量相当的展览和美术活动都是策划人、画家、经销者、收藏家围绕着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而谋划的,并没有考虑艺术与社会及大众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艺术作品流通于市场之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它的商业价值而非艺术价值,就是说,越是流入市场中、价格越高的艺术品,其审美的艺术价值就越被无视和剥离,没有人会以单纯的审美心态将一件花高价购买的艺术品随意地挂在墙上供人欣赏。
艺术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投资和交易的载体,而很少有人再关注艺术品所承载的那些文化和艺术上的价值。这种情况下,即使大众想要接近“美术”,“美术”也被人为地建立起了其与大众的一堵墙。
文化生活的多元与多样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当代社会生活方式不断丰富,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不但对物质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对于精神生活也同样有着越来越多的需求。由此带来两个精神生活(或者说审美)上的倾向,一是对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审美上的需求,大到城市建设、环境设计,小到生活用品、服装首饰等尽量讲究求新求美;二是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精神文化供人们进行选择,尤其是诸如电影、电视、各种出版物、流行音乐等等大众文化产品更受到人们的青睐,无论怎样比较,“纯美术”对于大众的吸引力都不能和影视和娱乐文化相提并论。
这两个倾向在相当的程度上使生活本身变成了审美的对象,一些学者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泛审美”或“生活美学”,因为“艺术已渗透到几乎一切对象之中,使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美学符号’”。
既然生活为大众提高了诸多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方式,大众又何必拘泥于“纯美术”的欣赏呢?再说,当下美术馆和博物馆中的艺术品看起来总是显得那么“深奥”,让人难以接近,那么又何必花费时间和心思于此呢?
美术高峰的出现非主观和外力可以左右
按照一般的逻辑,在以上对大众疏离“美术”的原因作了分析后,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出某种对策和建议,但在这里,还需思考并回答一些问题才能更为合理的理解大众与“美术”的关系。
如果站在理论的高度来看,那么完全可以认为,本文所探讨的“纯美术”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文化的造型载体的重要角色,一个时代的美术创作凝结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和人类的审美意识,传达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其对传承和创造人类优秀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按理说,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纯美术”应当为大众所普遍熟悉和接受才对,但事实总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从古至今,无论中西,高雅的绘画、雕塑相对而言总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而不是普通大众人人参与或多数人关心的对象。
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前,生产力远不能和我们身处的时代相比,民众的生活水平偏低,满足基本的生存已属不易,哪来的的闲心关心绘画和雕塑这回事?所以,那时的美术创作无论是用于说教宣传的佛寺壁画,还是辗转不同人之手用于收藏欣赏的文人丹青,都是上层社会和文化精英们的事情,与一般的大众几乎没有什么瓜葛。
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大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相应地在精神生活上也有了不同程度的需求。然则,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产品的丰富并不限于“美术”一门,电影、电视、图像(摄影)、流行音乐、话剧、各种书刊杂志等等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涌现,而且,它们的势头明显盖过了门厅冷落的“美术”。
尽管当下也有一些优秀画家和作品横空出世,但在整体上“美术”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明显地自惭形愧了。
那么,“美术”有没有必要得到大众的关注?如何看待这种大众与“美术”之间的疏离?
其实,我们之所以看重“美术”与大众的关系,无非是出于对大众文化生活品质的关注和“美术”本身发展的关心。如果我们认同“大美术”的概念并认可当下种类繁多的文化艺术形式完全可以丰富和提升大众的文化生活品质,就大可不必担心大众因为疏离“美术”而得不到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当下中国美术本身问题不少,美术创作良莠不齐,甚至完全脱离大众的审美,即使大众对“美术”抱有兴趣给予关注,也往往是一头雾水,不见得有益于其文化生活的提升。那么,被大众疏离的“美术”自身又当如何?与有的论者不同,笔者宁愿相信“美术”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与社会和大众对其疏离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在此,有必要谈及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即“美术”的兴衰有着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实非外力可以左右。
其一,社会和一定人群的关注固然可以催生一些可观的艺术家和作品,然则,“美术”高峰的出现却与社会和人们的关注并不相一致。艺术史可以证明,往往社会环境相对混乱、思想冲突激烈的年代更容易出现伟大的艺术家和不朽的画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几乎无暇自觉顾及艺术的发展,而中国艺术就是在此时自觉起来的,并出现了前所有未的画论;唐末五代宋初,社会再次因战争陷入混乱,然则此时山水画却高度成熟并从此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由宋入元,战乱刚过,社会文化环境大变,仕人在生活境遇和思想意识上受到猛烈冲击,而此时,却出现了中国绘画史上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元四家”和元代绘画彪炳史册;明清之际,山河巨变,中国又一次面临大变革和大冲突,就在此间,石涛、八大、陈老莲等明代遗臣再次将中国艺术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上半页,中国社会积贫积弱,民族的生存和延续甚至受到了威胁,而在中国美术史上,又出现了齐白石、黄宾虹等后人难以超越的大师,和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潘天寿等对现代中国美术影响深远的大家。
凡此种种不一一而举。在这些时代,遑论大众,就是权贵阶层也不见得对美术有多少关注,而中国美术史的几个关节点均出现于以上几个时代。
其二,大众的关注、资助及社会的物质基础并不一定会产生更为优秀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能证明这一点的还是艺术史。历史上,相对而言穷困潦倒但艺术成就煌煌于史的人物并不在少数,而当时受人追捧、事后遭到质疑的人物和作品也不在少数。
伦勃朗、梵高身处困境也能完成不朽之作,董其昌、王时敏富贵一生,追随者甚众,艺术成就却不能和石涛八大想提并论。其实,当下一些受人追捧,画价离谱的“大师”、“大家”放在更为博大的历史语境中,可能连立得住脚都难以在做到,由此可见,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艺术的质量甚至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美术创作并不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没有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出现,与公众的关注、疏离和艺术家能获得多少资助往往并没有直接关系。一国之大众疏离美术与否与能否出现伟大的艺术家与作品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品的产生却直接代表了一国在文化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
基于这样的思考,或许担心公众与“美术”的疏离就显得有些多余。诚然,我们不否认,一个地域的民众是否愿意接近“美术”体现着该地域民众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审美程度,也就是说,大众与“美术”的关系对于特定地域的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一定要和“美术”发生某种直接的联系,尤其是当下显得繁复而纷杂的中国“美术”。何况,今天的“美术”已然成为一种“大美术”状态,大众的生活并不缺乏审美的媒介和途径而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而“美术”由于其自身的某种规律和特质也决定了其不会因为大众的疏离就难以自处,尽管卓越的艺术家和杰出的作品是一个时代文化艺术高度的代表,呼唤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品也是我们身处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