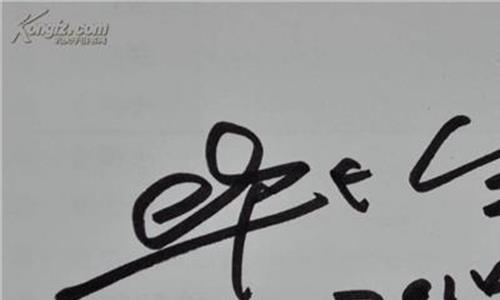毕飞宇玉米赏析 江苏作家毕飞宇:贴着大地飞翔与时代紧密互动
1964年生于兴化,1991年凭中篇小说《孤岛》叩开文坛之门,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和中篇《玉米》相继摘得第一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填补了江苏文学史上这一奖项的空白……多年来,作家毕飞宇透过深邃灵动的文字,凝视大地、思考生活,取得杰出的文学成就,更代表了江苏40年改革开放在文学领域结出的硕果。

“改革开放40年,每一天我都完整地经历过。我们这一代作家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毕飞宇说。
变革,成就一代作家的精神成长
1979年,毕飞宇15岁,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进他的家乡兴化县城。那时候,县城里文艺青年的时髦“标配”,是胳肢窝里夹一本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你只要一出门,至少能碰到三个人在读这本书,《悲惨世界》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震撼绝对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主人公冉阿让和警察沙威,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善恶截然对立的人性观轰然倒塌了,《悲惨世界》启示我们,应重新审视人性的浩瀚与宽广。”毕飞宇说。

春风吹过,文学欣欣向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经历了沉寂与爆发的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拥抱时代和回望历史的巨大渴望。有了父亲为他办理的县图书馆借阅证,毕飞宇没事就泡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和西方经典名著。

通过广泛阅读,他的世界观渐趋成熟。毕飞宇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世界观的人,和在之前世界观已经成型的人,是不一样的,“而世界观的差异,将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通向何方”。
对人的赞美、对生命的珍视,在精神上寻求并建构起对话关系,是包括毕飞宇在内的一代作家从这场时代变革中获得的充实体验。毕飞宇至今记得,当年喇叭裤流行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灵冲击:“精心剪裁的喇叭裤让身体展现出优美的线条,这几乎第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人可以这么美!

”这种认识投射到文学中,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成为“人学”的开端。另一方面,对外开放重塑一代人对于“我”和世界关系的思考。“海洋不再是‘围墙’,它变成通向世界的道路——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在精神上主动地和他们对话,并不会使‘我’失去‘我’;相反地,全世界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我们也在服务并影响着世界。
吸收、互鉴、对话,使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毕飞宇说。
“在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光辉使命
改革开放也重塑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在场”成为文学的一种使命。作家们怀抱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关怀人的境遇,关注社会的发展,使当代文学真正和国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短暂地跟随过一阵“先锋文学”的潮流后,毕飞宇迅速回到写实主义的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先后创作了一批重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那个男孩是我》《哺乳期的女人》《白夜》《男人还剩下什么》《地球上的王家庄》《彩虹》《家事》等,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叙事》《青衣》《玉米》《玉秀》《玉秧》等,以及长篇小说《上海往事》《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平原》和《推拿》。
如果说毕飞宇前期的写作侧重以回望和反思的姿态,书写现代中国发生的命运之歌,那么从《青衣》开始,他对当下社会的关注明显加强。
200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推拿》,成就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高峰,其“贴着大地飞翔”的深刻与悲悯,以及后来引发的社会关注,成为作家与时代紧密互动的最好印证。
《推拿》是一部深刻反映盲人生存现状的作品,它的独特魅力在于,用鲜活的个体刻画取代“盲人”的抽象概念。《推拿》提出的社会问题同样发人深省: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盲人并没能和社会建立起真正的关系”。谈起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毕飞宇回忆,促使他下定决心写作《推拿》的动力,正是身边盲人朋友希望他为他们“言说”的渴望,“哪怕我可能写得不好,但我必须提出这个话题——关于盲人推拿师的社会保障问题,关于我们对他们的忽视”。
2011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导演娄烨将其搬上银幕,并于当年夺得第50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溢出文学,引发全社会对盲人的关切。“那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光。我看到关于盲人的话题在不停地发酵,许多媒体也开始走进盲人推拿所,探寻这个群体的生活境况。我没想到《推拿》有这样的影响力,但它最终落在这里,我确实很愉快。”毕飞宇说。
之前一些重要文学奖项的评选比较偏好宏大叙事,而《推拿》这部作品展示出,小切口的故事一样可以抵达厚重:这厚重,来自作家倾注笔端的深刻悲悯情怀,对民族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介入社会、反哺时代的自觉意识。而这,也是伟大时代与文学互动的最好写照。
学习,让追赶者的步伐更有力
2001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开始实施,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文化。2003年,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法国翻译出版。随后,《青衣》走进了更加广阔的西方世界。
在2004年法国巴黎书展上,毕飞宇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国际奖项——“最受法国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2009年,凭借长篇小说《平原》,毕飞宇摘得著名文学奖“世界报奖”,这标志着他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法国文坛的认可。
2012年,小说《玉米》又为他赢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来自英语世界的国际文学奖项。2017年,凭借为中法两国之间文化艺术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毕飞宇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这是否说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已经具备赢得自信的实力?毕飞宇认为,就当代文学艺术而言,谈“自信”或“不自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即使对自己的作品再有信心,作品好不好,只能读者说了算。我们还是要在与读者、与世界的对话中,让作品接受检验。”
这些话,透露出毕飞宇对作家使命的独到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面对这一切,他认为,作家仍然不能放弃批评与反思。“对作家来说,不管他心里多么爱,有时他必须要像医生一样,先施行手术给病人一刀子,只有先经历了痛,才能使他变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也是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力量。”毕飞宇说。
回首40年,展望改革开放“再出发”,毕飞宇深情寄语:“不论我们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我们依然要保持谦逊。罗马决非一日建成,我们这一代人获得较好的成长,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赋予我们的珍贵品质,那就是学习,向世界各个国家学习,向一切值得学习的地方学习。比起领跑者,追赶者往往更有力——让我们更谦逊一点,学习的姿态更强烈一点。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永远不能停止的实践。”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