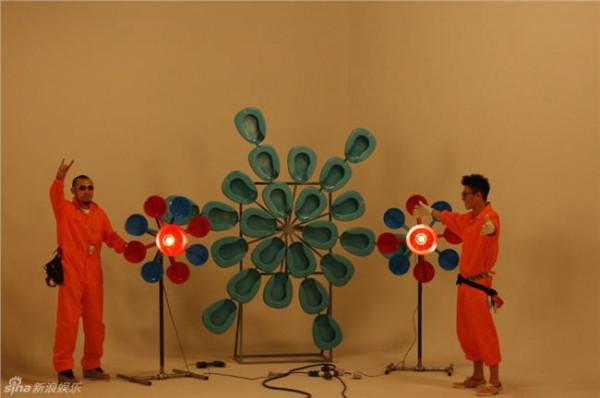熊十力痛骂徐复观 徐复观日记里的余英时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一生极少写日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1980年10月26日,徐复观在笔记本上写道:“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在悔也无益。十月十一日由台返港,病体似有进步,我想把零细的感想纪录下来,又因循了十多天。从今天起,写了试试。”

徐复观的日记,前后跨度约两年多,从1980年至1983年,史料价值不可谓不高,其中涉及到许多港台以及国外的各界贤达,比如董桥、余英时、胡秋原、郑学稼、余纪忠等。其中涉及到余英时部分虽然不多,却“事关重大”。

因戴震而起争论
徐复观和余英时曾有一场著名的争论。时在1977年,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刚出版不久,在这一年由杜维明主持的“中国十八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余英时与徐复观相遇,当时徐复观74岁,余英时48岁。

据徐复观在杂文集《忆往事》中追忆,参加那次会议的学者,最为年长的是台湾学者陈荣捷,和徐复观一样,都是74岁。其他较为年长的分别是生于1908年的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生于1919年的美国学者狄百瑞,“其余多是四十余岁上下”。徐复观还记得,“会中对唐君毅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比港台两地更高”。这次会议过后不久,唐君毅病逝。
徐复观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清代汉学衡论》,自称对所谓“乾嘉学派”做了总的批评。在徐复观宣读论文前,已宣读了六篇论文,其中有三篇是专谈戴震,在其他的论文中,也多关涉到戴震,徐复观因此觉得“这次讨论会无形中是以戴震思想为中心”,同时认为“大家对他有过高的评价”,戴震之所以在北美学界有如此地位,和梁启超、胡适等人的鼓吹有关,即徐复观所谓“主要是通过梁胡两公的著作议论而来”。
正因为有感于此,徐复观便“撇开论文的主要内容”,集中到对戴震的批评中,因此引起一连串的讨论。
徐复观批评的面很广,其中专门批评了余英时:“余英时说他对戴震和章学诚的研究法,重心理分析,这是治思想史的最后达点,但一个人的心理是与其人格关联在一起。”徐复观进而提出三点批评戴震人品有问题,其一,戴震三十三岁到北京,尚对他的老师江慎修推崇备至,因为江氏兼治汉宋之学,与当时专门标榜汉学反宋学的风气不合,所以当他四十岁写《江氏行状》时,便芥提彼此间的师生关系,以后则只称之为“老儒”;其二,戴震集中有《与王光禄(王鸣盛)书》,称《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应作“充”字解。
但王鸣盛在《蛾术篇》则称戴震并未写这样一封信给他,此书乃戴氏伪托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另外据徐复观的考查,戴震对“光”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其三,戴震的《水经校注》,与赵一清的完全相同,赵一清的著作,在戴震进四库馆的前一年已经进呈到四库馆,所以当时只认为戴震抄袭赵一清的著作,而没有人怀疑赵抄袭戴的著作。
听完徐复观的发言,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立即站起来,表达对徐复观的支持。
徐复观在这次讨论中虽然批评了余英时,但余似乎并不介意。徐复观晚年回忆此事,对余英时颇为感激:“我非常感谢余英时先生,因为他的饱学及俊俏的口才与笔调,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我的话虽完全不是针对他的论文而发,但我与他的意见是显然不同。
他不仅未曾稍为介意,并且他在讨论会结束时向我说,徐先生的态度,我早已知道,也看过你的文章,但此次听徐先生的讲话,和看文章时的感受不同。许多美国朋友,受到徐先生的话感动。”徐复观因此称赞余英时的“识量之宏”。
因方以智而结缘
此次会议之后时隔三年,徐复观在1980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记:“汪宗衍先生来信,内附汪世清先生补充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补论的材料,即转余教授。”这则日记涉及到余英时的另外一本著作,即出版于1972年的《方以智晚节考》。日记中提到的的汪宗衍,后来在余英时的文章《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中曾经出现,余英时当时特别提及了他和陈垣的关系。而汪世清则是著名的徽州文化研究者,在学界颇负盛名。
余英时开始对明遗民方以智产生兴趣,是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后期,并且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完成这一人物的初步研究。此书看似和余英时之前的研究没有关系,其实暗中所接续的乃是余英时在1958年所写的《陈寅恪先生书后》,对此余英时曾经多次加以申说。
1986年,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中曾言“《方以智晚节考》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皆为考据之书,然其旨则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证以外者,盖亦欲观微知著,借‘个人良知’以察‘集体良知’也。考证、笺释虽皆属传统文史研究之体制,若善尽其变,则亦未尝不能与时俱新,以供今之研治文化史与思想史者之驱遣。”
余英时后来在2003年为《方以智晚节考》在大陆三联书店重版的序言中也说:“我是希望通过他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试图揭开当时遗民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一角,因为明、清的交替恰好是中国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悲剧时代。
这一精神世界今天已在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获得惊心动魄的展开,但一九七一年我写《晚节考》时,《别传》的原稿尚在尘封之中。后来我果然在《别传》中读到方以智与钱谦益曾共谋复明,可惜语焉不详。在这个意义上,《晚节考》也许可以算作《别传》的一条附注。”
余英时撰写此书的因缘,还是钱穆在序言中的概括最为准确。钱穆指出:“英时此文之贡献,所谓发潜德之幽光,其对于密之之生平志节之表扬,以证晚明遗老遭际沉痛深衰之一般,以及满清异族政权所加于中国传统士气之摧残压迫,不啻是钩画一轮廓,描绘一形态,使后之读者更益有以想见其时之情况,而不禁然以思,惕然以悚,而油然生其对当时诸老无穷之同情,而悼古怜今亦必有不胜之感慨发乎其间者,则莫大如此文最后之《死节考》一章。”
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的增订版自序中也曾提到,1980年代大陆有许多对方以智晚年事迹的讨论,“皆以此书为争议之对象”,“而尤集矢于《死节考》一节”。比如冒怀辛在1981年发表的《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一文,便对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提出商榷:“唯其论证方之死事为出于自裁,则予不能无疑而尚有说焉。
”而在冒怀辛之外,余英时写作此书之后之所以一再增订,还有李学勤的功劳,而且李学勤曾经以“仪真”的笔名在1962年和冒怀辛一起发表过《方以智死难事迹考》,1978年余英时访问大陆时和李学勤谈起方以智研究,李学勤随后以旧文相赠。
而后余英时又读了容肇祖的《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和张永堂的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等文献,撰写成《方以智晚节考新证》一文。
徐复观在日记中记载的转赠资料一事,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一书增订版中特意点明,汪世清辗转托人转给余英时的资料,内容为根据方中通《陪集》以及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订正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余英时当时大喜过望,撰写《方以智死节新考》,随后又过六年,1985年余英时又读到了任道斌所撰写的《方以智年谱》,在此书的基础上又撰写了《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
谢国桢在为《方以智年谱》的序言中,还特意提到了余英时的三篇文章———《晚节考》、《新考》、《新证》。时隔13年,余英时才结束了自己对于方以智的研究,而徐复观与余英时的这一段学缘,也在余英时的著作和徐复观的日记中得以记录。
◎周言,青年学者,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等。






![[原创]熊十力痛骂徐复观](https://pic.bilezu.com/upload/1/55/155ed7bcd3b9e252d36d2c9e1c8922cd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