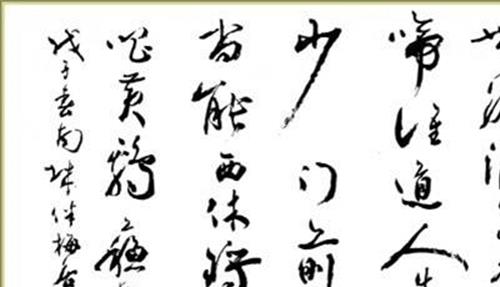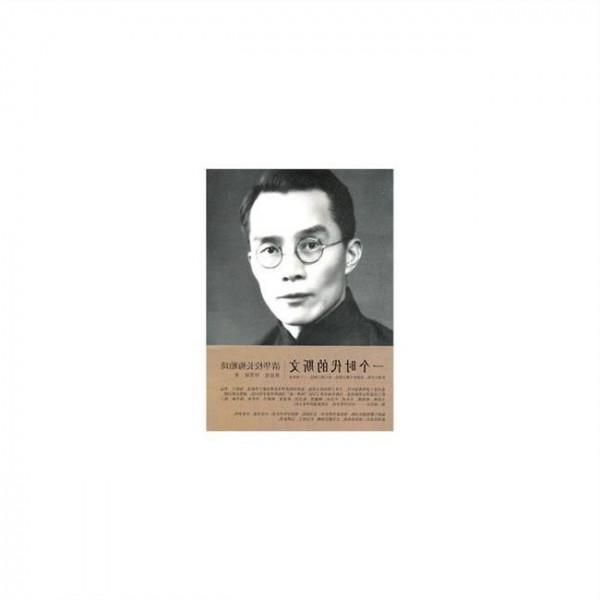梅贻琦怎么读 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了?傅斯年、梅贻琦如何阅读
剥夺了学生养成“自发”能力的可能,又谈何“领袖人才”的培养?
据传傅斯年有一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个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台湾大学在傅斯年去世后铸钟纪念,“傅钟”只敲二十一声,提醒台大学子应该把每一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二十一小时内,剩下三小时,用于沉思。

这最能警醒当下大学的本科教育。在我熟悉的几所大学中,本科毕业要求修学分140有加,平均一课程1.5或2学分,以4年7学期算,则每学期平均需要修10门功课以上。事实上,一般低年级学生每学期修15门功课确是常态。加上团委、班级、社团的活动,其结果,则学生天天疲于应付,时间七零八落,不仅没有沉思的时间,甚至已到了无暇读书的地步。

就理想言,大学生每修一课程大概均需阅读数部或十数部书,但因多数时间已用于课堂,修课而不读书渐成常态。到期末时,甚至出现多数学生需要在二三星期内完成近10篇“论文”的困局,除了“抄”之外恐怕真没有其他办法。

因此,不少学生在选课时考虑的不再是通过这一课堂是否能提升自己,甚至也不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课程好不好“混”,是否容易得高分。教师也深知学生情况,往往网开一面,故不读书也均能通过课程考核,甚至高分——或不读书也能撰写论文!

师生双方对待课程都渐流于“走过场”。这更进一步造成了大学中读书氛围的淡薄,甚至有某历史系学生到大三时仅曾读三五部书,且均非一般认为的历史研究著作。在近年历史系研究生面试中,当询问“读过什么书”时,得到的多数回答都仅限于三五通史,甚至有部分除大学教材、考研参考书外从不读书者!
造成这一境况的原因自有很多,与浮躁不重读书的世风不无关系,不能仅仅归罪于课程设计。就世风言,“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这并不表示身与大学教育者便一无可为,只能听之任之。课程的调整正是我们最能、也最应从事的改变之一。
较为可行的方案便是提高每一门课的学分数(因总学分不能减少),减少课程数量,尽量保证大二以上学生每学期可以不超过五门功课,有认真对待多数课、跟着课程读书、不用靠抄袭就能完成期末“论文”的精力,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有更多自由阅读“课外书”的闲暇时光。
梁启超曾提醒大学生需要“做课外学问”,最主要内容便是“读课外书”。如果学生“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这样的人便无“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他又曾警示学生,如果整天“无一刻暇适”,很容易沦为“躯壳之奴隶”。然而,大学主事者的课程安排,已使学生不得不忙忙碌碌于上课,不好学者有借口不读书,向学者无时间读书,逼迫着学生“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这不正是剥夺了学生养成“自发”能力的可能,又谈何“领袖人才”的培养?
“闲暇”地读书,在中国历史上,实有传统。宋儒朱熹曾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教门人。在闲暇中才能“敛其心”,收束身心,头脑清明、志气如神;也只有在闲暇中才能“纵其心”,展开想象的翅膀,“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不然,“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读得书”?(朱熹语)当今的大学,恰已渐成这样的“闹场”。
梅贻琦就曾这样批评过当时的大学,“学程太多,上课太忙”,致使学生无闲暇。他认为大学最重要是养成学生“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自修功夫”,课程不过是“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更多需要学生在闲暇中“咀嚼融化”,这便“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不然,“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入室矣”。
大学,本是一个让学生变成读书人的地方,最成功的教育也不外乎养成学生自动的阅读习惯,使其在毕业后仍能保持这一习惯,让读书成为他们此后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所以,办学者不妨静下心来,放慢节奏,还学子一些闲暇,为他们提供一个场所、一段时光,让他们悠游读书,养成“自修功夫”,在“咀嚼融化”中识学问之门径,甚或升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