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陈东 宋朝有一个太学生 叫陈东|文史宴
中国古代学潮学运史,有个人是无法绕开的,他就是陈东。
我们上中学那会儿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他的名字,当时觉得很奇怪,一个普通的学生,居然能青史留名。多年后,有了更多的知识,就更感觉不可思议,因为比起大学的历史教材或专业历史书,要能在中学的历史教材上留个名,那简直类同登天,不信的话,你去翻翻这些历史教科书,数数看,在上面留下名号的到底有几个?

但是陈东做到了。
我不想拿意识形态来解释这件事,我只是在更后来知道了,陈东这个人的事迹被载在《宋史·忠义传》里,也就是说,他在历史上是有定评的。
其实翻遍可靠的历史记载,他的事迹实在也是有限的很,唯一详细一点的也就在他离世前的最后两三年。(突然想起前些年流行的《***的最后***年》这类书,如果写陈东的话,只能用最后三年了。)

北宋繁荣的太学
他是身份是太学生,也就是国家在京城设立的学校里(如果用现在通俗的类比,太学应该算是一所部属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
当时的太学实行“三舍法”,所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类,陈东属于哪舍,我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按照他当时的年纪,四十多岁的人了,如果达不到上舍生的水准,那起码也是内舍生,至于外舍生,感情上我们似乎不太好接受。

两宋重视教育文化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太学生,国家免去他们的差役之外,还每月发津贴,如果学行优异,在科举道路上还可以越次擢拔,比如直接授官,或者不需要经过省试而直接进入殿试,诸如此类。

当然,国家的优待也不是白给的,当时太学生的学习也是鸭梨山大,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为上舍生,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而且升等的比率又不高,压力我猜想绝不低于现在的高考。
到陈东生活的宋徽宗年间,虽然不用原来的每个月频繁考试了,但每季度还是要考试一次,每次考试的结果要和品行方面的测评一起记录到学生档案,并且每季度按照积分排名,年终给予校定,以上叫“私试”;另外,所有太学生每年还要参加一次“公试”,公试要分等第的。
最后,公试和私试还要一起结合考评,决定这帮学生的前途,优秀的升迁,良好的就地升舍。可恶可怖的是,对学业品行不达标的,太学实行积分排名淘汰制,予以退送和除名,退送就是退回原来举荐的路府州。
你想想,本来这些地方推举上来的都是本地优秀的学子,而一旦被退回,无论对地方还是个人,荣誉和面子方面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以频繁的考试来培养所谓人才,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和宋代似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今天的你可以傲娇的说,我们考的门数比宋代的多,综合素质比宋代的学生强,对此,我只有呵呵了。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享受着国家生活、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优待,学业又那么繁重,考试压力又那么大,他们最大的本事应该就是安安静静的读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回报国家,你说是不?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徽宗朝以前的太学,太学生们除了有可能在自家学校院子里高谈阔论外,余下的时间,也就是埋头读书,应付考试,争取科举上的功名。
我们的陈东在成名之前似乎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因为有资料记载,他也是一个被地方推荐上来的贡生,受着优待的同时,同样面临着升学考试的压力。
北宋末年的学潮
我有时候想,一个人人生轨迹的突然改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情和势是最大的两个。情是本性,也可以叫气质,势是外部环境。
陈东的突变和这两者都有关联。
他本是个慷慨磊落的汉子,敢于指陈时事,敢于针砭时弊。蔡京、梁思成等人和宋徽宗混在一起,成天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表面上鲜花着锦的时代,却到处潜伏着危机,更要命的也最终要了北宋命的是,北方正又悄悄地崛起了一个强悍的少数族——女真!
处于这样的环境下,任何有良心的士人都会有所警惕、有所担忧,也会或多或少有所行动,但是可怜的是,那些已经借科举上位的士大夫官僚们只会巴结着上司、围绕着皇帝,那时候对皇权相权很有制衡力量的一支——台谏,也是尸位素餐,除了用君子小人、新党旧党的老招数胡乱攻击人之外,其他并无作为。
怎么办?
处于士人最底层的普通的一名太学生——陈东挺身而出!
必须要说的是,对徽宗年代朝政的批判,太学生中,陈东也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有李彪、陈朝老等人。但论影响,陈东恐怕不仅是在北南宋之交、即在整个古代学运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士人敢于发声敢于批判时政,虽是性之所至,但关键是也要有可以发声、允许发声的环境,如果一个时代不允许你开口议政、只允许你做良民,你能怎么办?幸运的是,陈东生活在这样一个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允许自由发言的美丽新时代。
“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这是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的话。思想自由的基础是言论自由,而赵宋,的确是这样一个朝代。两宋的舆论场中,士大夫固然可以发声,太学生也可发言,即使是布衣,也允许和上述对象一样上书谏议,对朝政表达自己的意见。
前些年网上有个调查,问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很多人选择了宋朝。当然各人喜欢的原因不一,除了对这个吃喝玩乐花样百出的时代的诸般艳羡外,很多人喜欢宋朝,似乎都是奔着它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上述宽松的政治环境来的。
但是很不幸,本文的主人公,却恰恰死在了这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时代。
祖训与皇权的较劲
宋人的言论自由是有来源的,追根溯源,据说和当年宋太祖留下的誓约有关系,有人还有鼻子有眼的说见过那块刻有这誓约的誓碑,其中有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誓约上的所谓祖宗家法是否真有,我们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但是不得不承认,两宋确实不曾轻杀滥杀过士人。
但是我们的陈东死了,就死在了这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时代!说好的自由呢?——你和谁说去!
话到这里,我不得不要残忍地揭开一个华美的疮疤了。虽然,虽然大家都知道宋代的执政牛逼、台谏牛逼、文人士大夫牛逼,甚至普通老百姓也牛逼,而皇权似乎受到多方面的节制,但我想要说的是,没有皇权的让渡,没有皇权的允许,这一切的所谓言论自由都是虚幻,犹如海市蜃楼。
因为两宋的皇帝绝不是近代立宪制意义上的虚君,所以皇权的实质仍然是专制,谁敢于揭开这个疤痕谁就注定了要吞下自己酿造的苦酒。
很多人歌颂那个时代的文人自觉、士人担当,仿佛他们取得了与皇权一样平起平坐的权利,能够抬鼻子上脸了。他们看不到,美丽面纱的下面其实暗藏着一张狮子的脸,而皇权,就是那只狮子。
它只是暂时睡着了或半睡半醒,而一旦你撩着了它的痛处,等待你的必定是难堪或悲催的下场,我们的陈东就正死在这个美丽的虚幻图景之下。
再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太学。如大家都熟知的,宋徽宗时代的教育事业比起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那会儿,表面上更加兴盛,尤其是太学,在蔡京的主持下,无论规模、考试制度还是学生的待遇,都较前有了新的提高提升,颇能够体现传统社会君主追求的文治升平。
但是与之伴行的是,对太学生的明里暗里的思想言论控制也更加严格,比如宋徽宗就曾经亲自颁布诏书,把很多书籍列为禁书。再如对太学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有和当局不同意见的,就采用连坐惩罚的法子处置,当时人有记载:
这个时候的太学生的言论自由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只准唱赞歌、不准唱反调成为了一条潜规则,当时“学规以‘谤讪朝政’为第一等罚之首”,不懂这条潜规则或者考试的时候不小心触犯了所谓的时忌,那你就等着进自讼斋(反省院)反躬自省吧。
不得不承认,在专制专权的操弄下,宋徽宗和蔡京颇为成功,一时间居然出现了“士无异论,太学之盛”的场面。懂事的太学生们纷纷写文章搞肉麻,大唱赞美诗,以至于徽宗“幸学,多献颂者”,你看,上倡下和,一幅多么令人舒心和谐美好的景象。
而我们的陈东的形象和价值也正在这样一幅图景中凸显得越发的高大而清晰,没有这样的一幅背景衬托,你看到的陈东也许只是一个平面、一个剪影、一个单调的人物而已。
陈东之死与赵构之惧
关于我们的主人公,我不会写他的七次或八次伏阙上书,也不会写他的举动引发了多大规模的连锁反应,这个甚至连《宋史》的编者都搞不清,一个地方说数万,另一个地方又说数十万,也不会写他犯宋高宗赵构的忌讳,赴狱前写的关于身后事处理的书信。
这些史书笔记里都有,我都不会写,因为这些都不是我写他死因的初衷。
我想要写的是,当一个个体被错置在一个时代一个无知之幕里,当思想的头颅被专制的利刃割下,当一腔热血被上下勾结的权力放空,当以生命为代价的努力最终换来的依然是蝇营狗苟,我们致力追求的是否还有什么价值?我们是否还要向陈东同学学习?向他学什么?
陈东死后三年,刽子手赵构良心突然发现,下了一道类似罪己诏的文书,这份文书写得温情款款却又进退狼跋,似乎自己是被别人绑架上了道德祭台,令他一想起杀陈东这事就左右为难,尴尬羞惭不已。赵构的真实内心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一道冤魂从此也注定了伴随他一生。
陈东死后,太学依然还在。那帮太学生呢?与闻时政、参与朝政的热情不减,似乎也更加闹腾。当然,一遇君王和权臣联手弹压,依然是一色的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这和陈东生前没有多大区别。对权臣的依违和望风承旨的品性,比例上我猜度也不会和陈东生前有多大差别。
陈东之死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有多大,不敢妄测,倒是最近翻览的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里的两则,很耐琢磨。一条讲高宗幸太学(似乎也是成规,例行视察,以表领导高度重视),本来只想看一看养正斋的(斋就是现在的学生宿舍),哪知道被隔壁宿舍持志斋的热情高涨的同学力邀参观。
没办法,高宗只好也临幸了一回,但是打住,从此之后,再没有这样的例子了。之后来考察太学、临幸宿舍的时候,都预先指定宿舍名,而且挑选也是极其谨慎,只看预先挑好的,其他的一概免谈。
高宗这一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他怕什么呢?怕再被力邀?恐怕还不是正因。我猜测还是怕被太学生热情过度,一不小心万一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陈东形成的阴影一直还在呐。
还有一条的对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南宋名臣胡铨上书请斩秦桧时,史载:
看来,陈东在南宋初政治至少在高宗一朝的影响还是始终存在的。但我这里却也不得不说,像陈东这样刚性的汉子,本身的号召力以及对时政的影响力,却再也没有在高宗以后的南宋各朝再次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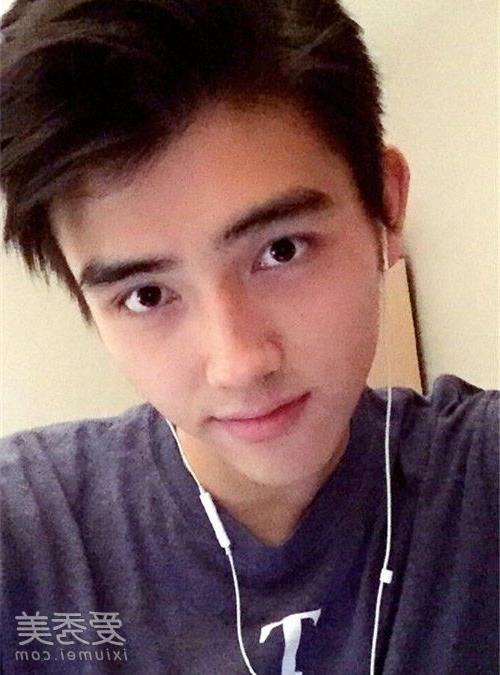

![>陈小旺文章 [图文]陈小旺丹田内转教学//陈小旺83式太极拳教学](https://pic.bilezu.com/upload/9/c5/9c5189d823ad903113fd69edf93165ae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