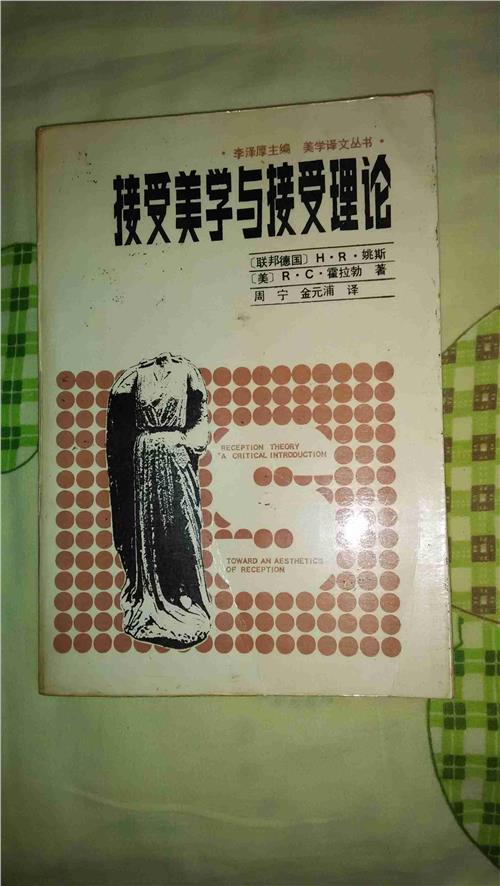霸王别姬小豆子 《霸王别姬》和接受美学运用
“接受美学”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学派创始人之一姚斯(HansRobertJauss)在1967年提出的。姚斯对接受美学的研究是为了解决文学史研究是方法论危机。在姚斯那里,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显示为紧密相关的双重历史,即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相关性历史和作品存在与一般社会历史的相关性。结合一般历史意识和特殊美学意识才是接受美学的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作品与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这里就需要引入“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这一概念,这种读者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存在。姚斯对文学接受的研究是从“期待视域”入手的,即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

当一部作品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符合一致时,它立即将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使理解迅速完成;当一部作品与读者既有的期待视域不一致甚至冲突时,它只有打破这种视域,是新的阅读经验提高到意识层面产生新的期待视域,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对象。

姚斯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尺度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会反驳”。由此我们可以回顾电影《霸王别姬》中小豆子对《思凡》“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演绎。小豆子小时候在念这段唱词的时候总是念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很明显小豆子的期待视域是一个被师傅削去头发的男子,他从心底里反驳“女娇娥”,可是在一次演绎中,师傅逼迫师兄用极其残忍粗暴的方式强迫自己接受“不是男儿郎”,自此小豆子的一生开始走向悲剧,他改名程蝶衣。

而后来,程蝶衣因《霸王别姬》而成名,缘是他“人戏不分”“不疯魔不成活”,称他是虞姬转世。此时的蝶衣已经打破了原先的视域,新的阅读经验构成新的期待视域。两三个龙套穿梭便是千军万马,舞台上的分花拂柳、翻山越岭、攻城略地,佳人与帝王的悲欢离合已经深深印入蝶衣心中。
自己演绎的虞姬与师兄演绎的楚霸王的爱情,他渴望延续到戏外,于是就有了那句“说好了一辈子,少一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两人分离22年的舞台上,虞姬唱罢最后一句,用他送给霸王的那把注满蝶衣感情和幻想的宝剑自刎了,蝶衣亲手结束了这出灿烂的悲剧。
在接受美学的审美经验论中,姚斯对“净化”的概念史作了一番情理,认为它在指称审美经验的交流经验方面具有代表性。
其后姚斯还借助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确立的五大英雄类型来设想五大交流模式,这些模式是经由接受者对作品主人公的识别来进行的,分别有联想模式、敬仰模式、同情模式、净化模式和反讽模式。显然蝶衣对京剧《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是一种联想模式和同情模式的识别。
蝶衣在表演中借助联想把自己置身于所有其他参与者的角色中,共享欢乐,后来他自己的命运与虞姬的命运愈来愈平行,他同情虞姬,并将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与之共同受难。
从寻求文学史写作的方法论基础,提出接受美学的问题,到转向审美经验的全面研究进而反思接受美学的经验基础,这便是姚斯的主要思想轨迹。相比之下,姚斯早期对接受美学的方法论意义的探讨更有价值和影响,尤其是在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的结合方面,他作了有效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