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是昆明人吗 费孝通抗战时期在昆明“跑警报”(图)
1930年在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时的费孝通
在西南联大时,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 》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概说来,10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我们住在昆明的文化巷,是出城门必经之路,一有预行警报,街上行人的声音就嘈杂起来,我们一听就知道。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开拔。

这一路上的人,大多是联大和云大的熟人,跑警报也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有时我还带书在身上,可是心里总觉得有点异样,念书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别样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在昆明跑警报,对跑得起的人即便不说是一种享受,也决不能说是受罪,比不得重庆。我在重庆又热又闷的山洞里坐过几天之后,更觉得昆明的跑警报是另一回事了。昆明虽则常有警报,真正轰炸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又不常以市区作目标。除了有一次投燃烧弹外,破坏的程度很小。要不是疏散,郊外虽有它的吸引力,我想绝不会有这样多的人,一听到警报就这样起劲地向城外跑。

现在想来,这种躲避轰炸的方法,实在是相当危险的。你想,成千上万的人暴露在山头山脚,至多不过在深不及三四尺的土沟里蒙着个头,不正是一个最好的扫射目标吗?有一次我在飞机里偷偷撩开窗帏,望着昆明附近的景致时,我才明白地面上的人物是这样清楚。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那时不向我们开个玩笑,低飞扫射一下。
昆明的这种跑警报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我是不相信有什么效用的。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感觉得到,所以当时有很多传说,敌人来轰炸昆明是练习性质,航空员到昆明来飞了一圈跑回去就可以拿文凭,是毕业仪式的一部分,所以谁也不认真;又说东京广播里会提到为什么不扫射暴露在山顶上群众的原因,“你们这些在郊外野餐的青年男女们连一点遮蔽也没有,破坏你们的豪兴,似乎太不幽默”。
这些传说显然是昆明人自己编出来的,但也足够说明当时跑警报时的气氛了。
1940年9月,我们就这样过去了,到10月初还是这样。行动上的习惯化和心理上的有准备,把警报的惊人作用大大的减少了。
13日那天,我们又照例在山脚下闲谈,可是那天有传说是要炸大学区了。我们的家就在两大学之间,所以我太太有一点担心。1点多钟,27架银灰色的日机从东方出现了,向着我们飞来。我太太忙着要我把头用手蒙起来,可是我却被好奇心所支配,反而把头仰了起来。
恐惧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有的是兴奋,像是在看电影。“下蛋了!”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在那群机翼下,丢了一阵怪好看的小东西。响声相当沉重,比以往听过的好像实在得多,而且地都有一点震动,响过了,很多人就向山头爬,我也在里面想看看,究竟炸着了什么地方。
城外的联大新校舍还是好好的,城里升起了一大堆尘烟,没有火光,在山头上望去好像还远,在城中心似的。我跑回来,一口咬定我们的家一定没有事。这时周围的人争着打赌,没有人懊丧或是惊慌。
解除警报那天放得特别迟。但是大多数人早就拥在城墙缺口等着了,而且因为城墙上着了几个弹,从缺口望进去也看得到云大校舍有几栋房子倒了,所以消息便很快传到后方来:大学区这次可真着了。这消息使我太太很焦急,于是同行的人中就派出了先遣队回去招呼。炸着了之后怎么办,那是出于我们经验以外的事。
当我们进城时一看,情形确实不妙,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我们踏着砖堆找到了我们的房子,前后的房屋都倒了。推门进去,我感觉到有一点异样:4个钟头前还是整整齐齐的一个院子,现在却成了一座破庙。没有了颜色,全屋都压在有一寸多厚的灰尘下。
院子里堆满了飞来的断梁折椽,还有很多碎烂的书报。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木框连了窗槛一起离了柱子,突出在院子里,可是房里的一切除了那一层灰尘外,什么都没有变动。我拂去桌上的灰,一叠稿纸还是好好的,一张不缺,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这是难以相信的,一切都是这样唐突。
“着了,着了。”我好像是个旁观者,一件似乎已等待很久的事居然等着了,心情反而轻松了一些,但是所等着又是这样一个不太好看的形景。我太太哭了,也不知为什么哭。我自己笑了,也不知有什么可笑的。
和我们同住的表哥,到厨房里端出了一锅饭菜来,还有一锅红烧肉。饭上也有一层灰,但是把灰夹走了,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麻烦的是这一层罩住了一切的灰尘,要坐、要睡先得除去这一层。这一层被炸弹所加上去的,似乎一拿走就是原有的本色一般。
可是这是幻觉,整个房屋已经动摇,每一个接缝都已经脱节,每一个人也多了一层取不去的经验:一个常态的生活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被破坏,被毁灭,这就是战争,歌颂战争就是在歌颂一件丑恶的事。
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在哭。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
天黑了,没有电灯,点着一支洋蜡,月亮特别好,穿过了屋里的窟窿,射进来。我见了身上发冷,赶紧上床,可是老是不容易入睡,穿过屋顶看月亮。这房子住不得了。房东来看过,说没有钱修理,实际上也不容易修理。虽说跑警报并不怎样讨人厌,但是对于我们也并不太喜欢,而且我太太又快要生孩子了,天天在郊外跑也得有个限度,我觉得非搬家到乡下去不可了。
疏散到四乡去是一种长期逃避轰炸的办法。昆明的四乡从来没有被轰炸过。经了9月和10月初的疲劳轰炸,已有不少人这样下了乡。我们的房子既然被炸着,必须搬家,倒不如一劳永逸,搬下乡了。
14号一早把太太送到了呈贡的朋友家,趁便就在呈贡城附近的村子里找房子,呈贡那时也已成了疏散的地域。李保长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里,这是一个普通农村里的小康人家,房子倒还新,新得还没有盖完全。农村里的房子大多是慢慢地一部分一部分盖起来的,这家房子一直到我们住了5年离开之后方盖全的。
正屋四开间楼房,已经有一半租给同济大学的周先生等3家人。我们去商量了半天,只能租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他们的猪圈。
楼板的材料并不算太坏,乡下人的东西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有法子拼得太紧密,所以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的气味也可以升到厢房里来。厢房靠院子的一半板缝还没有补,只用草帘挡着风。我们希望两件事:把猪圈搬开,把板壁起好。
这两件事交涉了半天,只做到了半件:用竹编的篱笆糊上纸做板壁,我们更加上一层布幕,不但光线好,而且又很雅致。至于猪圈一事,那是无可商量的,他很不客气地说:“猪的收入比全部房租大上好几倍。
”李保长为人顶爽气,在租金上从没有让人难堪过,因为他开头就说得很明白,出租房子是为了交情,而且带一些救济我们这些逃难难民的性质,并不等钱用。这是实情,尽管在这新的房屋里,历史开了倒车,我们的生活逐渐下降,但是我怎能不感激房东主人的好意?他给我这炸弹所不会到的房间,至少减轻了不少生命的威胁。
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在我们的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除了房东住了5家房客,连本来堆柴的小房间都腾了出来住人,我们这间在猪圈上的厢房还算是二等包厢。
费孝通(摘自《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文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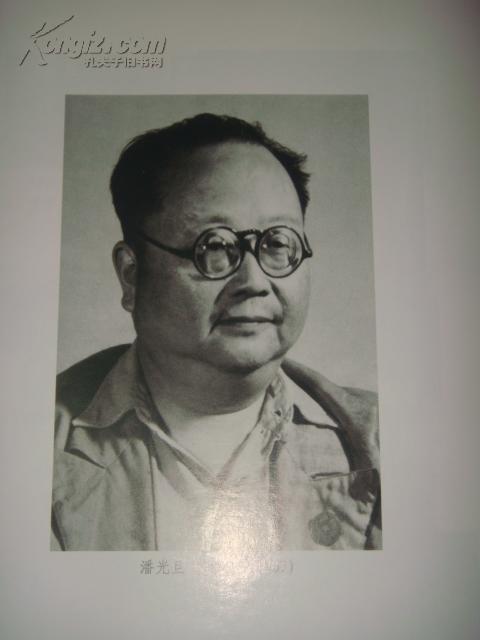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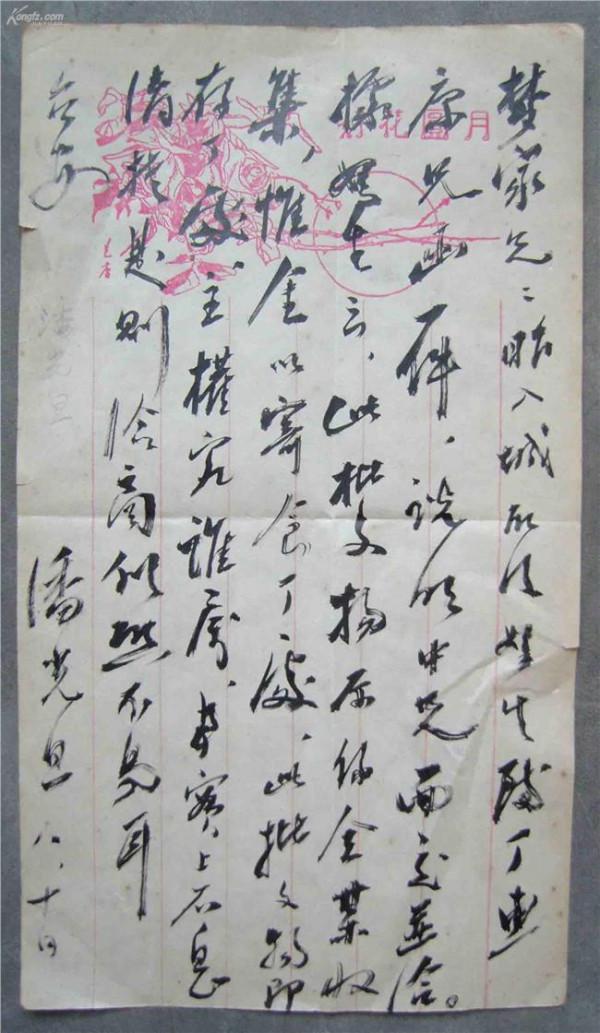
![>程斌抗联 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时期东北抗日武装]](https://pic.bilezu.com/upload/1/fd/1fd4ec5d764dfbaba24a67f14e00fca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