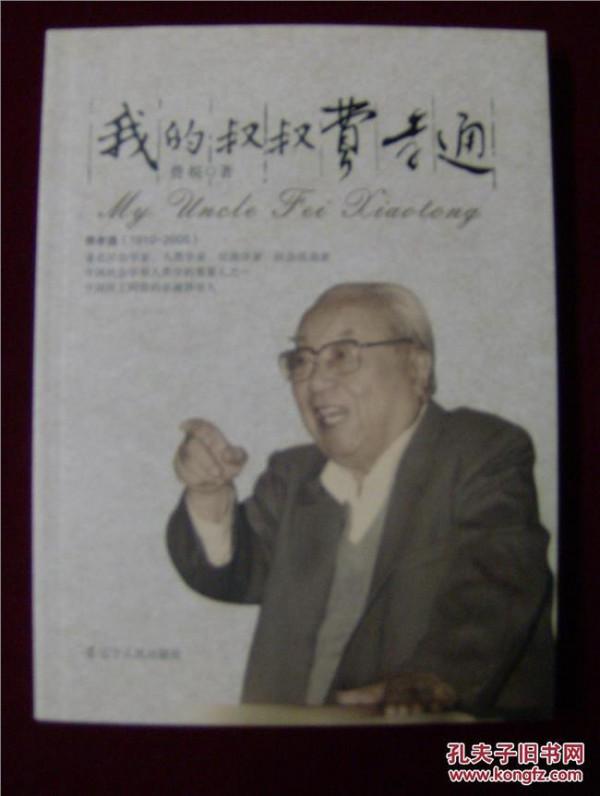费孝通文集 费孝通:1949这一年
今天是费孝通先生的生日,按照中国传统雅称,今天是他的茶寿(一百〇八岁)。
费孝通先生的生命历程,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尽管他去世已经多年,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一生中,探寻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无数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我们再读费孝通,就不能仅仅把他当做一个社会学家,而更要当做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一位中国士绅乃至一位身逢巨变的中国人来解读。可以说,对作为一种“文化典型”的费孝通的书写,或许才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张冠生,民盟中央原宣传部长、参政议政部部长,曾长期担任费孝通先生助手,出版费孝通传记和口述实录多种。本文选自他的著作《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感谢作者授权群学书院发表本文,谨此作为对费孝通先生的怀念。

《我这一年》
文
张冠生
来源
探寻一个好社会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起伏动荡,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其早年心志一以贯之,直达生命终点;其文风却在中年时期发生明显变化,标志性著述是《我这一年》。

费孝通:《我这一年》
三联书店1950年版
《我这一年》一书之前,读者是从《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初访美国》等著述熟悉费先生文风的。其中有的书初版后,因文字深入浅出,脍炙人口,短期里一再加印,读者喜闻乐见之状,不难想象。

若其中文风能绵延始终,不知煌煌十几卷《费孝通文集》会是怎样亲切可人又深邃广远的风景。事实上,1940年代末的社会剧烈变动,导致费先生文风陡转,进入另一状态。
《我这一年》一书首篇,是《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写于1949年8月31日。说是“各界”,货真价实,费先生在会场里见到五行八作的代表。仅服装,就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望而知不同的一众人物,聚在同一个会场里,一同讨论公众事务,费先生还是头一次经历,印象深刻,不由动容。
1949年,费青(左)、费振东(中)、费孝通重聚北京
此前,费先生另有一次经历,印象似更深刻,乃至动心。
1948年年初。他随张东荪、雷洁琼等前辈人物去河北西柏坡,如此记录沿途观感: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的粮队,车上插了一面旗,没有枪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
——这印象打动了我,什么印象呢?简单地说: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丛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
费先生说,西柏坡之行,给他一记“当头棒喝”。革命的力量,已经赶走了装备精良的敌国敌军,接下来,“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触景动心,甘愿低头。这是费先生文风变化的心理基础。他把这种真实心情写进《我这一年》一文。
为读者明白“低头”的意思,费先生特意说起“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自大的心理”。从自大到低头,心理变化带来语言变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无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肯低头”、“传统知识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辩证的”、“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里才真的说得上改造”……这类费先生称为“挂红”的表述,如此密集出现于其文,前所未有。
1956年,费孝通再访江村
《我这一年》一文中,“知识分子”一词先后出现十四次,其中十二次属于贬意或否定性表述,两次勉强属于中性概念。费先生自知属于这个群体。1949新政之后,对这个群体要做强力改造。对改造,费先生表示认同,“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
费先生这一年里发生的变化,在当年知识分子里并不少见。
梁漱溟是他亦师亦友的前辈,曾在1950年10月1日的《进步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该文若改题为《我这一年》,也相当切题。
梁先生开篇就说:“去年今日开国盛典,我还在四川北碚;今年我却在北京了。”接着,他讲了自己在这一年里的思想变化。
开国大典,梁先生本有机会躬逢其盛,他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声明不去。这是他“从1946年秋到1949年冬……一直闭户不出”的延续。其闭户原因,是一次高层政治协商中的冲突,导致他断然辞去民盟总部秘书长职务,退出民盟,离开党派政治,关门写作,即便开国大典的邀请,亦谢绝不至。
固执如此,一年之间,梁先生对新政权的看法大为改观,变化来自其将近半年的国内游历。1950年4月初到9月中旬,他先后行经平原、河南、山东、察哈尔、热河、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九省,观感非凡,以白纸黑字为证。
梁先生说:
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人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可怕的莫过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
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
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
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这段文字,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54—855页。
1938年,梁漱溟与毛主席促膝长谈
梁先生大心大愿,当年创建民盟,是为国;退出民盟,也是为国。既然国家能被一个政党治理得政通人和、清风拂面,当然该说其好话,彰其功德。
费先生内心、文风之变,与梁先生同理。作为一介书生,他抱定以所学知识为民众福祉服务的志向,清楚地表达于著述,体现于实践。如有政党能切实带来民众福祉的增进,当然该赞同其主张,配合其步调,哪怕自己会不习惯。
1949年秋季,清华大学开始开设政治课,俗称“大课”。全校学生、部分教师和职员工友一起听课。费先生时任该校副教务长,负责“大课”的组织领导工作,一边张罗邀请合适的教员,一边要消除一些知识分子对“大课”的反感。
针对“大课是思想统制”的说法,费先生写文章《我们的大课》说:“习惯和思想的改造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所用的方法也必须是民主的……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发表意见,……谁都不应当给人扣帽子……马列主义不需要用权力来压制人家,只有非真理的教条才不能不用强制。改造思想和镇压反动派是完全不同的。改造是为了团结,在民主方式下改造自己,和思想统制本身刚刚相反。”
费孝通:《大学的改造》
商务印书馆2017年
这段话很有意思。费先生内心有变化,文章题材有变化,文风有变化,可以说,变化很多,很大,同时也有不变的东西,原则的、基本的东西,比如对民主的信仰和追求。知识分子即便改造,也应是民主的改造,而非强制改造。
费先生说:“我们知道民主这个名词已经三十多年,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经有六年多,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他在警惕“似是而非”。他知道自己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诚的,故愿意说出真实的想法——
解放以来,我对于共产党钦佩的地方的苦干、负责、谦虚、有办法、不怕麻烦。我爱它,因为许许多多我熟悉的,我爱好的青年朋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个个都拼命地工作,中国有希望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已在我眼睛面前完全证实了。
当然,会上,他见证了。会后,他相信了。《我这一年》一书可作证。
![费孝通名言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https://pic.bilezu.com/upload/3/ec/3ec522368476e234c3ea3796c797095c_thumb.jpg)





![费孝通简介 [费孝通简介]费孝通简介](https://pic.bilezu.com/upload/f/97/f972363481e226bdb39b1c74c9051678_thumb.jpg)



![>杨利民大庆 [黑龙江] 大庆郑新英杨利民谈大庆文化自信与自觉](https://pic.bilezu.com/upload/f/c1/fc111665ca2efdb997ca925ec738049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