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法西斯 乔治·桑德斯在新书《十二月十日》中再展辛辣讽刺
我还清楚地记得是从哪一刻开始,我对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的看法有了改变:从认为他是一位善写好玩故事的有才华的作家,转变成认为他有可能是美国小说界中真正具有斯威夫特风格的讽刺作家——他能够如此巧妙地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可笑,以至于可以真正地切中要害。
在他那篇绝妙的中篇小说《赏金》(Bounty,写于1995年)中,有一段文字描写的是一位奴隶主向他新买来的活资产们解释他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本质——故事的背景设在堕落回蛮荒时代的未来美国,用的是一位刚刚参加完人事部门的三天渡假会议回来、油滑但心中有数的CEO的腔调——他遗憾地告诉他们,他不能给他们以自由,但他会很乐意出钱给他们搞一次年底烧烤大餐,以及为他们所住的奴隶宿舍提供室内装修津贴,甚至出钱赞助一些“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用得着的、有关励志方面的内心调理课和小型研讨会“。
他说,他希望他的奴隶们能感觉到“充满干劲”、表现得“目标明确”。
之所以说桑德斯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极其重要的文学人物,答案就在这个地方。那短短的一段中所涉及的各种元素,如今已经进化成了一种独特而难以模仿的风格,非常切合我们这个由能说会道的财阀们与47%的吃救济人口相对立的时代。
初接触桑德斯的人,会注意到故事的那种反乌托邦背景——它暗示着美国由于某种环境上的或经济上的灾难而衰落,使得历史上某些不可爱的阴暗面再度沉渣泛起。另外他还凸显了权力的不平衡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被广为接受。
桑德斯笔下那些倒霉不已的主人公们就算没有真的被奴役,往往也是被雇佣来从事那些浑浑噩噩、朝不保夕的工作。他特别喜欢把他们设想为某些荒诞的主题公园或活人复古表演里那些低工资的表演者或古装人物,以出卖自身的尊严为富人们献上不咸不淡的娱乐。
在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担任创意写作教授和成为屡获殊荣的小说家之前,桑德斯曾在诸如柯达公司和弧度公司(Radian,环境工程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里工作过。从这两段经验中,他显然意识到了回荡于美国公司会议室里的种种干巴而可笑的套话已经在我们的日常言语当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正如在奥威尔的作品里那样,在桑德斯的作品里,有权势者往往通过对语言的篡改和操纵来分化人民、掩饰没有人性的一面。在奥威尔的笔下这显得令人恐怖,而在桑德斯笔下这却莫名其妙地显得非常搞笑。
但这也令人悲伤。在他这本令人叫绝的最新小说集《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里,所有的故事或多或少说的都是关于分离的悲剧。而它与他前三本同样精彩的小说集【《摇摇欲坠的内战公园》(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天堂主题公园》(Pastoralia),《讲理之国》(In Persuasion Nation)】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增添了少许似甜非甜的救赎色彩,而这种成分是大多数其他讽刺作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因为他们担心那会破坏他们原本辛辣的配方。
《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The Semplica Girl Diaries)是这部新小说集里最长、也最古怪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顾家好男人为了让女儿在生日那天开心,不惜花大钱去买来市郊中产家庭最新的流行装饰品:被绳索穿起来挂在前院里、精心安排作为活生生会呼吸的草坪装饰物的白袍女郎——她们都来自第三世界的贫苦家庭。
就算你把《奥伯林文科目录》(Oberlin liberal arts catalogue)中的所有课程都加到一起,也比不上桑德斯通过这篇小说而展现出来的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后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与白人中产阶级焦虑情结之间那种联系的理解力。
(而且你肯定也不会象在读这篇小说时那样放声大笑。)
作为那些串成一串的桑蓓莉卡女郎的拥有者,小说里的主人公对他那位半信半疑的女儿解释说,她不必为她们感到难过,她们在合同期满后会拿到报酬。而且当她们返回到自己那贫穷而饱受战争蹂躏的故乡后,那笔钱“会有助于她们照顾在家里等待着她们的亲人”。
这位主人公的道德思路似乎与小说集中另一篇故事《逃出蜘蛛头》(Escape From Spiderhead)中的那些技术专家不谋而合:那些人负责给囚犯注射可以改变情绪的化学药剂,目的是要找出能够完全控制人类喜怒哀乐等情绪的终极配方。
(用他们当中一位的话来说,这样的发明将成为他们的一个“绝活儿”,一个“划时代的产品“——这话听起来就象是一位硅谷神童为自己的新创公司寻找风险投资时的口气。
)那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试验对象。当他了解到对方打着科学的旗号——打着制药公司利润的旗号——最终在逼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他感到的是绝对的毛骨悚然。他以最后的反抗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而社会和那些关押他的人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种救赎有可能会出现。
这两个故事都是典型的桑德斯风格:它们的超现实提供了一个刚好足够的荒诞面具,使其似乎隐约有了警世意味。桑德斯在施展开讽刺手法时,更倾向于把批判的对象置于我们正在走向的、堕落了的未来世界,而不是我们目前所身处的这个刚刚初现败象的世界。
不过可以感受到,最近桑德斯开始有点脱离超现实主义而转向冰冷的、重工业区风格的自然主义——类似于我们从查尔斯·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的小说、或与桑德斯一样来自纽约州北部地区的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的小说中能体会到的那种风格。
在《十二月十日》里,这种风格反映在诸如《小狗》(Puppy)和《家》(Home)这样的故事中。前者写的是两个女人的视野被阶层的棱镜扭曲到了彼此完全没有可能”感同身受“的地步;后者写的则是一位情绪极不稳定的退伍军人如何与他的家人重新沟通的故事。
然而,书中最具这种风格的是与书名同题的那篇小说:它写的是一个想要自杀的男人在北方某个湖边遇到一位木讷男孩的故事。
上面这几篇小说里的每一篇,都跟你所预期的桑德斯小说一样风趣幽默、出乎意料而又极其巧妙,但它们除此之外还有一样别的:不加掩饰的柔情。桑德斯经常被人拿来跟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相比——他也自认为很受冯内古特的影响。
这二人的联系在很多方面显而易见。但是即使最热爱冯内古特的读者,也会承认冯氏的愤世嫉俗:作为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目击者,他从未完全原谅人类的这一罪行以及20世纪里的很多其他罪行。
而相比之下,桑德斯至少目前还没有对我们全体彻底放弃希望。正如他笔下一位极其沮丧的人物所说,继续活下去、与亲人保持联系的价值在于“生活中依然可能有很多——很多点点滴滴的善良。”就讽刺家而言,这番话就象是宣战书——它碰巧出现在整部小说集里最后一篇小说的最后几页。人们不免急切地想知道,他的下一篇小说将会怎样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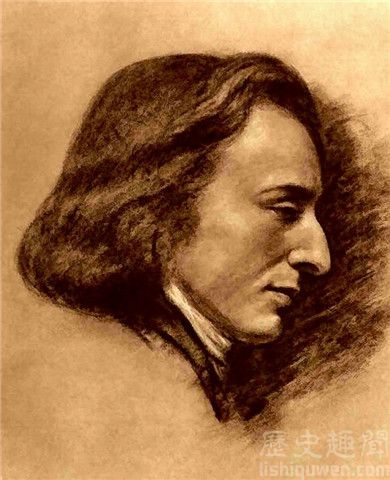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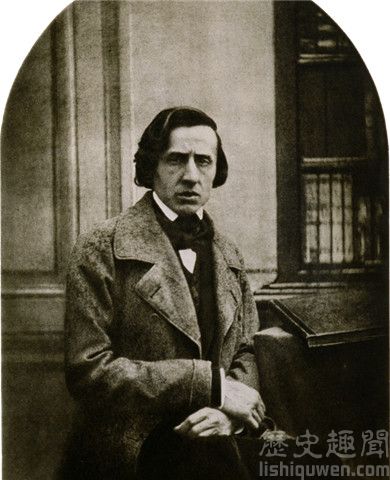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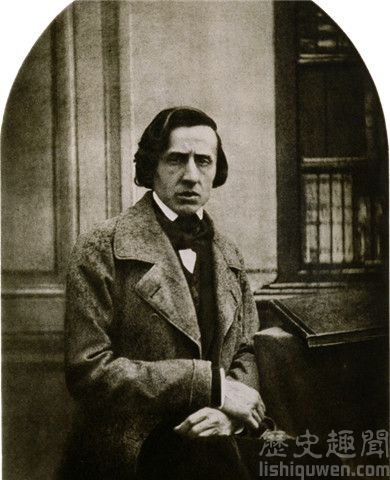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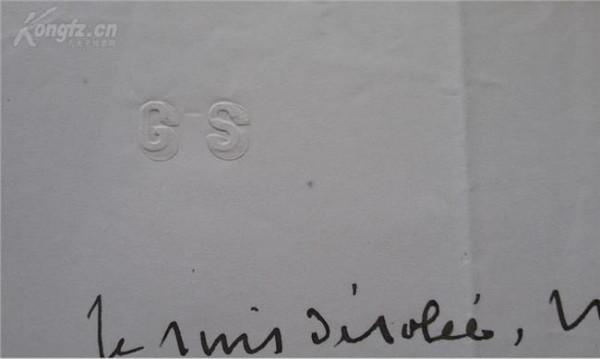
![>乔治桑作品 [精品资料]外国文学评介丛书——乔治桑](https://pic.bilezu.com/upload/9/29/9294b754846347e8f0d0c6f1f7245eff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