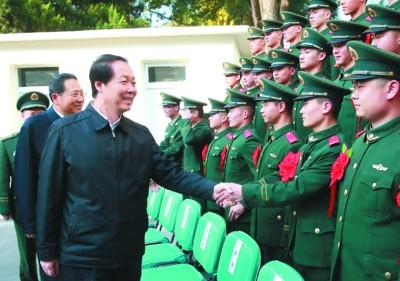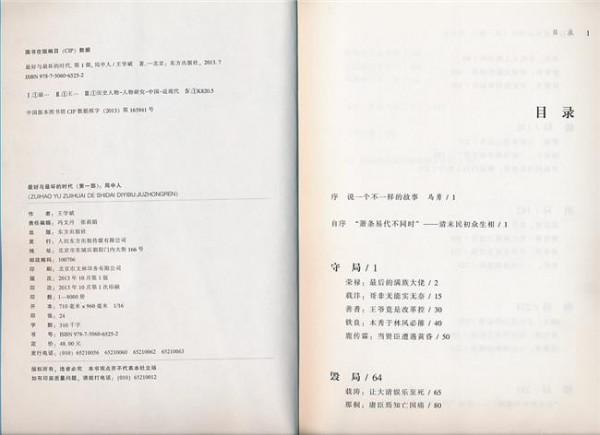荣禄与晚清政局 王学斌:道出未尽的历史本相——读《荣禄与晚清政局》
清末显宦陈夔龙在其自传《梦蕉亭杂记》中,曾如此概括满族重臣荣禄病殁之影响:“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

”陈于清季政坛得以发迹,荣禄其间多有庇佑回护,故此番评论,不免有溢美之嫌。然揆诸晚清政局,荣氏一人在军政两界之份量与作为,确也堪称“枢纽”,无怪乎《清史稿》称其“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只是百余年来,学界对此一流政治人物的研究,却始终处于“运动战”状态,缺乏令人信服的“攻坚”之作。荣禄之形象也常给人一种“有地位,没面目”的模糊印象。

如此尴尬情形,绝非学人有意为之,更多怕是客观因素所致。仔细想来,荣禄作为晚清重臣,身历咸、同、光三朝变迁,宦海沉浮四十余载,涉世愈深,故愈谨慎,所留存文字愈稀;与高层隐秘行事风格迥异,伴随清末官方舆论管控松弛及报刊等新式媒体的兴起,荣氏尚在世时,各种秘辛传闻已是铺天盖地,身后则更呈泛滥之势。

要之,当事人的有意隐讳与旁观者的捕风捉影,便造成历史本相的逐渐遮蔽而坊间八卦的郢书燕说。于是,一百多个春秋更替后,当下研究者所面临的,至少有四重困难:一手史料受限、掌故传闻混淆、人脉关系复杂及关键政绩不清。

去岁从马忠文先生处获赐其新著《荣禄与晚清政局》,正是集矢于此四个问题,抽丝剥笋,一一化解,通读数遍,渐觉荣禄之面目清晰起来,颇有拨开迷雾之感。
毫无疑问,治史首重资料,这恰是研究荣禄时所面临的最大难关。诚如作者所言,看似与荣禄相关的史料范围比较广泛,但“直接有关荣禄本人的资料较少,且十分散乱”。况且庚子之后讹言盛行,很多私人记录彼此矛盾,故使用起来更须注意。
所以搜集荣禄的资料必定繁重且谨慎。于是遍览、比核、鉴别各种资料,实乃绕不过去的工作。作者在此项上用力极深,且很有章法,具体而言有三。其一,紧扣关键文献。正因本人遗存资料稀少,故一旦发现一纸片言,自当深入研读与利用。
作者通过搜集,发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6册《荣禄函稿底本》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10件荣禄传记资料,实为了解其思想动态与生平事迹的可靠依据。也正是凭借这些关键文献,作者在剖析某些重大事件时往往能切中要害。
如在判断戊戌之际天津阅兵是否为政变铺垫时,作者引用了稿本中荣禄的一份《致醇邸函》,从侧面证明此次阅兵“与后来发生的政变没有必然的关联”。其二,立足文书档案。研究清史尤其政治史,官方文书与档案是基本史料,且存量堪称巨大。
作者爬梳了一档馆朱批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以及数十年陆续出版的各类档案文书汇编,可谓穷其所能见,基本上盘点出较为完整的关于荣禄的奏疏、上谕等材料,从中发现了不少线索,其功底可见一斑。
其三,侧重重要人物资料。荣禄一生接触要人无数,不过彼此往来有亲有疏,共事有长有短,交际有多有少,恩怨有深有浅,故侧重与之平生关系密切人物的资料研析,自然是了解荣氏事迹与思想的事半功倍之法。
作者全书抓住盛宣怀、翁同龢、王文韶、李鸿藻、刘坤一、张之洞、樊增祥及刚毅诸人的文集、书信、日记、电函等材料,厘清他们与荣的关系,从而借他者的文字展示出复杂多元的晚清重臣形象。如通过樊增祥的诗文,可大概窥知荣禄在庚子事变中的立场及其后新政肇始时的作为。
搜集史料的过程,亦是破除诸多野史掌故误导的过程。掌故之学,由来甚久,《四库全书总目》将此类图籍列入杂史、杂家和小说家之中,认为其乃“一时之见闻,不得为正史”,可见该体裁往往流于琐碎与随意。孰料降至清季民国,掌故笔记写作很是兴盛,几十年间相关作品层出不穷,洋洋大观。
中华书局曾策划出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陆续推出晚清以来的史料笔记数十种,其中著名者,如徐一士《一士类稿》、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等,均为掌故之属的经典名著。
然大凡一事一物异常流行,亦不免鱼龙混杂,彼时的掌故写作即这般景象。虽有徐一士、黄濬、瞿兑之、张伯驹此等学养与人品俱佳的掌故大家,亦有诸如许指严、陈灨一之流靠杜撰兜售名人逸闻来谋生的文人。
因此对于近代掌故的使用,学界历来主张慎重,如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曾言“笔记资料的来源多是作者的亲闻亲见,作者所目睹或亲见参与的事情,所记本应属实,但亦因种种情形发生误记……至于传闻,不实更多,社会上流传的东西,往往每经一次传播,就有一次加工,传的愈频繁,走样就愈甚”。
另外“作者的学识同记录的真实性关系甚巨,作者才疏学浅,容易相信讹传,考证的事情也易失真”。所以倘若写手学识有限,且只顾道听途说,不加细致考辨即匆匆下笔,那么其掌故作品之水准可想而知,恐仅能当作市井坊间口耳相传的段子而已。
因而作为清季民国掌故笔记中的“热点话题人物”,对荣禄众多传闻的辨析亦是作者的一项既辛苦又有趣的差事。譬如历来掌故笔记大多将荣禄与肃顺间的矛盾视为个人恩怨。
陈夔龙更以肃顺二度向荣禄索要西洋金花鼻烟壶及良驹的事例以求坐实此传闻。此描述看似颇合情理,实则忽视了当时的官场大环境。根据作者的考证,“肃顺对荣禄的排挤,毋宁说是他与另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之间的一次较量。
当日堂官之间才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政治对峙。文祥是辛酉政变后获准留任的唯一一位军机大臣,说明他在抵制肃顺专权问题上早有作为,并得到慈禧、奕訢等人的一致认可。
由此认为,荣禄在户部因傍依文祥而遭到肃顺倾轧,大约没有疑问。荣禄与肃顺的矛盾绝非个人私怨,而是朝中派系斗争的反映”。此论可谓对晚清政坛有深刻洞察。又如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颁旨忽然开掉荣禄内务府大臣和工部尚书职务,晚近私家笔记都将此事缘由归结于荣禄与沈桂芬之间的矛盾激化,后世学人大多接受此观点。
然而作者比勘官方正史与私家野史众多记述,指出“荣、沈公案”恐怕绝非个人宿怨抑或南北之争这般简单。
在理顺当时枢桓之内满汉关系的基础上,作者清晰地揭示出此风波不仅波及荣禄、沈桂芬、李鸿藻、翁同龢等满汉大臣,另宝廷、醇亲王奕譞、慈禧等皇亲宗室亦参与其间,因而“荣、沈恩怨只是问题的一面,主要原因还要复杂。
虽然缺乏佐证,牵涉内务府大臣等满洲贵族之间斗争的可能性极大”。同时“荣禄先前得到的恩遇太厚,难免招忌,宝廷、沈桂芬等人策划的撤差计划,肯定迎合了不少满州官员的心理”。如此解读,似更能贴近晚清政治博弈之实情,亦再度证明流传甚广的掌故笔记往往流于皮相。
关注政治人物,其数十年积累编织而成的人脉关系网络自是聚焦重点。在《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中,马忠文先生对荣禄人脉网络的把握,不仅遵循以往学人所开拓的“明线”,并且还另辟蹊径,清理出几条鲜为人知的“暗线”,明暗结合,使得荣氏人脉网越发立体化。
所谓“明线”,就是荣禄研究方面经常提到几对人事线索,如与李鸿藻、奕譞、沈桂芬、翁同龢、刘坤一等人的交往。仅仅关注这类人事的离合分疏,则往往陷于党同伐异的解释框架中。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台湾学者林文仁的《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一书,他认为自辛酉政变至甲申易枢,透过这二十多年朝堂间决策争论与斗法角力,枢臣常言及“南党北党”等词,因此“同光之际所谓‘南北之争’,绝非后人归纳史事所迳造之新词,而是一种真实的政治现象。
尤其,此时所谓南党、北党云云,已非过往历朝一种较抽象之概念,易言之,不只是一种文化或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历史成见而已,更是政治行为中最直接的权力争夺”。应当说,此角度不乏新意。
然只将庙堂对抗背后隐含的南北之争、恭醇之争揭示出来,似仍不能切近政治脉络的深层肌理。林氏将复杂的政治运作与人事纠葛梳理得如此清晰简约,这恐与史实难符,毕竟矛盾重重甚或混沌不堪方是政局常态。
此外,林氏某些论断的依据,往往取自野史掌故,考证不足,不免偏颇。故陈寅恪高足石泉先生早在民国时就曾论及晚清政局之线索有三:“其一,则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其二,则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其三,则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是也。
三者更相错综,遂使局面益趋复杂”。正因错综复杂,更须于明线之外发现新的暗线。马先生高明之处即在于梳理出数条很是重要的暗线,不妨择其中荣禄与刚毅之争为例。荣、刚关系是戊戌政变后左右政局的关键因素,而二人交往恶化则是起于甲午年间。
根据马先生的考察,刚毅幕后靠山为翁同龢无疑,翁氏长期与荣保持貌合神离的状态。在甲午年入值军机的问题上,荣、刚二人有过暗斗。慈禧起初属意恭王选一位满族官员入枢,在权衡荣禄、刚毅二人时,翁同龢建言刚“木讷可任”,遂刚入荣退。
自此双方的隔阂便愈发深化,“甲午后荣、刚的关系一直不融洽,甚至不断恶化,根源之一当起自甲午入枢之争”。这确是以往学界忽视之处。
依此暗线一直向前推进,便不难知晓戊戌后朝局走向的因果。荣、刚二人愈演愈烈的斗争,是既往研究易被忽略的主线索。“在军机处,刚毅虽然班秩在后,却因入枢在前,在处理军政大事时,‘横出主意’,与荣禄时常发生争执。
由于刚毅援引端王载漪和大学士徐桐为后盾,荣禄虽大权在握,处理朝政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多方周旋。明了这种状态,有助于理解庚子年出现政局动荡的深层次原因”。自甲午到庚子,这条暗线逐渐由微到著,政局的反复变幻基本围绕此线索上下波动。
此线索的挖掘,为我们审视己亥、庚子政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角度。另外,作者还在书中提到“某种程度上,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荣禄在西安将军任上与鹿传霖熟稔,可折射出“从文祥、李鸿藻、荣禄到鹿传霖这些先后执掌枢机者的人脉渊源”。此两条论断,对于理解同光两朝的该派系人事更迭颇有启示。
过往之研究,时常视荣禄为政治官僚,这虽无可厚非,但毕竟冲淡了其军事将领的身份。实际上荣禄的关键作为,却多在军事方面,同时这亦成为他日后地位煊赫的重要资本。马先生在第六章专就荣禄在督办军务处上的作为详加论述,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对于督办军务处的研究,一般都考察机构设置与功能作用层面,而从该机构与荣禄个人权势扩张角度探析的,该书恐是首度。就名义上看,督办军务处本是个战时统筹军务的临时机构,战争结束当随之裁撤。
不过直到甲午后,督办处一直存在,且实际上分割了原属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统筹新政的角色。若视野仅仅停驻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则不易留意此问题。马忠文先生通过研究荣禄的权力增长,发现借助督办军务处这一平台,其权势不仅迅速扩张,并借助荣禄的练兵活动,“湘军、淮军兴起后汉族地方督抚执掌军权的局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清廷中央重新获得统掌军权的主动权”。
这种人物与机构互动探讨的方法,值得借鉴。
实事求是地讲,笔者对于《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无论读前,抑或读罢,自始至终都是抱着学习之心态,故确无具体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倘若说提点建议,不妨妄言一条。全书就荣禄人脉网络的考察,多侧重于甲午之前,之后更多是围绕明暗线索探讨朝局变迁与斗争。
简言之,以甲午为界,之前在剖析所种之因,之后则述论所结之果。此策略确实明晰,但势必难以兼顾甲午后所建构的人事关系。比如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荣、奕二人结识甚早。当奕劻尚为贝勒时,已对荣禄这位满族青年英才很是钦佩,与之订交,以“仲华二哥”相称,但交情只能说是泛泛。
甲午后,二人同朝为官,皆为慈禧宠臣,且无利益纠葛,故愈走愈近,结成盟友。庚子年,奕劻留京善后,其子载振逃往西安。
奕爱子心切,专程写信给荣,言“现时小儿载振,随扈行在当差,年幼无知,务恳推情关垂,随时指教,有所遵循,俾免愆尤,是所切祷。”将儿子托付于荣禄,可知二人交情之深厚绝非常人可比。也正基于此层厚谊,荣禄常将心腹推荐给奕劻,供其驱使。
戊戌政变时,奕劻奉旨领衔审讯六君子。领命不久,奕即派人赶在天亮前督促陈夔龙赴庆王府商议案件。按常理,涉及如此机密,唯有奕劻心腹才有资格参预此事。陈乃荣禄门人,一向谨小慎微,之前尚曾婉拒张荫桓之笼络。
故若非荣禄推荐或默许,奕劻万不会邀陈入府议事。可知陈夔龙是荣、奕皆资信赖的手下,甚或在荣禄授意下,担当沟通与奕劻关系之角色。由此亦可理解缘何庚子年奕劻单单留下陈夔龙这么一个汉族大臣作为助手处理善后事宜。
可知诸如荣禄与奕劻这样的交谊,多是在甲午后形成,本书对该现象未能详加观照。由此再进一步讲,身为重臣与首脑,荣禄自然有不少心腹僚属,如陈夔龙、袁世凯、铁良等人,并隐然形成相应的派系。那么荣禄是如何将诸人纳入麾下的?这些共尊荣禄为泰山北斗的官员所形成的人事网络在清末又有怎样的影响?遍观全书,这两个问题并未有明确解释,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治史向无定法,具体到政治史研究,最能体现学人水准的仍是史料功底与阅历见识。作为后辈与外行,本不该就马忠文先生的著作多加评论,之所以忍不住下笔,大概是因为我从该书中,看到了一位平凡满员于晚清政坛逐渐走向位极人臣的鲜活历程,以往学界未曾道尽的历史本相亦由之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