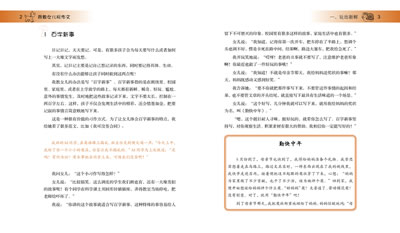肖复兴散步 肖复兴| 草厂胡同漫步(06.3.16)
在北京众多的胡同里,很少能够见到这样大面积的有规律的对称走向。为什么芦草园和北桥湾成为了它们的中心,让一西一东的长巷和草厂那么多条胡同,都能够如江河归海一般在这里碰头?
同长巷一样,草厂也是三里河的旧河道,《京师坊巷志稿》里说:“正阳门东偏,有古三里河一道……”也就是说草厂九条是旧河身,草厂其它的几条胡同都是以它原来流向而修建成的。
北桥湾恰恰是古三里河从前门一路流来到这里拐了弯儿,与金口河旧渠相通,通过南桥湾,流向金鱼池到红桥到左安门,进护城河。如此,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是长巷和草厂诸多胡同以北桥湾为中心呈现出对称的姿态了。如果说北桥湾像是一只鸟的嘴巴,芦草园就是鸟的脖颈,而长巷和草厂就是鸟左右伸展出的一对翅膀了。
九条的17号、19号
在十条草厂的胡同里,草厂九条是其轴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即使现在来看,那种河身的感觉依然明显,尤其是胡同北口路东一侧好几家大门前高高的台阶和院墙,是很扎眼的。
其中最为醒目的是17号、19号两院,门前都有高台阶,都有抱鼓石门墩,都有带瓦当的房檐,都有一溜儿长长的院墙,墙体一水儿的磨砖对缝(17号墙体下端被水泥沙石灰抹了),19号保持得更为完好,墙体下端的方形镂花的通风孔都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号院门上的门雕,图案清晰,笔笔精致,浑然一体。走遍,是这十条胡同中保存最完整最漂亮最气派的门雕了。
正好从19号院门里走出来一位男子,见我仰望他们的门雕,指着门雕下方墙上的一台空调说:“你没有看见吗?我们安空调都不敢碰着它。”
17号的院门前也站着一位男子,隔着老远冲我说道:“你来看看这里,这房檐的瓦当上还有‘吉祥’两个字呢。”
仔细打量17号和19号,这两个院子的房檐是连在一起的,院墙一般高一般齐,它们左右的院子的房檐和院墙明显要矮一截,而且往里缩进一截。它们的气派颇有些趾高气扬的样子。我问这儿的两位街坊:“这两个院子的主人原来是做什么的?”“肯定是有钱的主儿了!”19号的男子说,“这两个院子是一个主人,听说以前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的私宅。”
我问他:“知道这位大人物是谁吗?”
17号的男子插嘴道:“说是袁世凯的一个侄子!最早先这里是山西人开的银号,原来这两个院子是通着的。两个院子的格局一样,19号那边的房子更好一些,进大门过门道后,还有一个月亮门。”
我走进这两个院子,典型的南北走向胡同里四合院的格局,坐东朝西的三间房为正房,坐西朝东的三间倒座房,然后是南北对称的厢房,厢房的西侧各有一间耳房,靠南的耳房的北边是通向大门的过道。
果然19号的房子更齐整,好像也稍微宽敞一些,院落和廊檐都能够看出当年的样子。廊檐下红漆的圆柱和台阶,虽已呈老态,但依然可以感觉到当年的风韵。19号院子中种着一棵椿树,17号院中种着一株核桃树,但年头都不够老,是后种的了。
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一直跟着我,从19号院跑到17号院,指着南边的耳房房檐对我说:“这上面原来还有画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宽宽房檐垂花木板上的红色还没有褪色。”小孩子又指着对面的耳房说:“你看,这边房子的窗格子还是以前的。”是那种老式的云格窗棂,以前是糊窗户纸或钉窗纱的,现在已经凋零得如同姿色全无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老妇人。
当年的银号
走出17号院,那位男子还站在大门口的高台阶上,“两个院子一个主人,为什么开两个门?”他告诉我:“你没看出来吗,两个院子是有区别的,一家主人,就像有两房姨太太,能出一个门吗?”
我不知道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说罢,他就和19号的男人要出胡同北口洗澡去了。他们所说这里是袁世凯的宅第,是不是确切,我不大清楚,但说这里以前的山西人开的银号,是对的,有稽可查。
一是山西作家成一写的长篇小说《白银谷》中专门写到山西银号老号蔚丰厚京号,确实就在草厂九条。二是山西平遥著名商人雷履泰当年开设的西峪成颜料庄的分号,也在草厂九条,后来颜料庄的分号改成了银号。我只是不清楚,17号、19号的银号到底归哪一家,或者后来成为了一家?
我追上那两个要去洗澡的男子,希望从他们那里知道更多一点东西。但是,他们也不清楚了。正好走过路东的前门派出所,他们对我说:“这院子保存得最好。”我趴到门缝上一看,果然,坐北朝南的一排房子,虽然看不出到底是多少间,但在朦胧的暮色中依然看得见房子如同小媳妇梳的头发帘一样整齐。
便折回一点儿,走进派出所的大门,希望能够被允许进去看一下,年轻的警察客气而有礼貌地拒绝了我的要求,但是耐心地向我介绍清楚了派出所的格局,派出所占据的是两座院子,我趴在门缝中看到是后院,没有南房子,和前院子相通。
我猜出了,那后院的大门原来应该是开在朝南的位置上,这在这样的胡同里是有先例的。
我谢了这位小警察,告辞时问他知道以前是什么人住在这里吗?他说这我就不清楚了。后来,我看诗人侯马写的诗中说他1993年在这里当警察,说这里是一个著名花旦的小妾的私宅。
走出派出所,夜色降临了,一条胡同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斑驳的树影和房子黑黢黢的剪影交错着,九条掩映在水墨渲染之中。
不知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九条南口原来有一个小学,叫草厂九条小学,我小时候住的粤东会馆里有一个人,这个人贪玩,酷爱养鸽子,最后大学没有考上,到那里当老师。
学校的校长是个长着兔子三瓣嘴的豁嘴子,不仅长着这样可怕的嘴,嘴上还留着两撇黑黑的小胡子,更加增添了他的厉害劲头,那样子总让我想起黑社会的老大,我们小孩子给他起了外号叫“小胡子”。但是,他人不错,我们院的这个老师的对象就是他帮助介绍的。
那个对象在长巷四条小学当体育老师,个子高,跑得快,我们小孩子当年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二级风”。因为有了这样两个老师一个校长经常在我们大院里出现,那时候上小学,我们都特别害怕被分配到长巷四条小学和草厂九条小学,总觉得他们三个都很厉害,在他们手下当学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现在,这两位老师一位校长大概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浮云一别后,流水几十年。草厂九条还是老样子,和我童年时候见到的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就像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家,即使吃的和住的憋屈、窄巴一些,但出门打扮的得是有模有样,有款有型。有委屈,咽进肚子里;有故事,藏在胡同的深处。
两个小学同学
草厂这十条胡同里,我最熟悉头条、三条。那里住着我最难忘的两个小学同学。
三条住着黄德智,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我从插队回北京最初的日子里。他家以前应该是一户殷实的买卖人家,资本家出身的包袱一直压着他。我插队走的时候,他被分配到肉联厂炸丸子,我从北大荒回来后,他还在那里炸丸子。
他写一笔好书法,是他从小练就的童子功,足可以和那些书法家媲美。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照样只能炸他的丸子。我到他的车间找过他,那一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锅,在热油中沸腾翻滚的丸子,样子金黄,模样不错,我笑他:“你天天能吃炸丸子,多美呀!”他说:“美?天天闻着这味道,让人直想吐。”
那时,我们一样怀才不遇。我正在一所郊区的学校里教书,业余时间悄悄地写一部叫做《希望》的长篇小说。每写完一段,晚上就到他家去念,他坐在那里听,一直听到30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完,他从来都是认真地听着,从春雨霏霏一直到大雪茫茫,听了足足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每次听完之后,他都是要对我说:“不错,你要写下去!”然后拿出他写的字和字帖,向我讲述他的书法,轮到我只有听的份了。我们既是上场的运动员,又是场外鼓掌的观众,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着,虽然到最后我写的那部长篇小说《希望》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希望。
到现在我还总想起那些个难忘的夜晚,有时候我们就这样一个朗读着,一个倾听着,一直到夜深时分,他那秀气而和善的母亲推门进来好心地询问着:“你们俩今儿的工作还没完呢?明天不上班去了吗?”告别的时候,黄德智会送我走出他的小院,一直送到寂静得没有一人的三条胡同的北口,我穿过翔凤胡同,一拐弯儿,就到家了。那条短短的路,总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头条靠近北口原来有个广州会馆,印象中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宽敞的院子里,别的记不清了,一株枣树却总在记忆里疏枝横斜。那里住着我小学的一个女同学,姓麦。她首先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这个姓,说明她的家是来自广东,广东姓麦的人多,而老北京人很少听说有姓麦的。
麦长得非常白净,小巧玲珑,在我的眼里,挺漂亮的,而且还是我们班的班干部。她家住在头条的广州会馆里,之所以这一点印象很深,是因为我家住在打磨厂的粤东会馆,都属于广东的会馆,便自己先把这两个地方亲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但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她家住的广州会馆里,她也从来都不邀请同学到她家去玩或写作业。我希望能够有一次机会走进她住的广州会馆。
我终于得到这样一次机会,有一天她没有来上学,老师下午放学之前说她病了,让一个同学到她家把今天发的作业本给她送去,问谁离她家近?最后老师把作业本给了我,下了课。我像是得喜帖子似的,抱着作业本向头条的广州会馆走去。那两扇黑门并没有关,只是虚掩着,我一推就进去了,院子里和我想象的几乎一样,但我没有想到会有一棵老枣树,我住的粤东会馆里也有这样的老枣树,心里莫名其妙地高兴。
童年的事情,再怎么可笑,总是在心里温馨地记忆着。《京师坊巷志稿》里记载:“草厂头条胡同有归德、广州、兴国、麻城,金箔诸会馆。”但我只记住了广州会馆一个。
前些日子,我曾经两次去草厂头条,广州会馆早就拆了盖了楼。广州会馆在北京有北馆和南馆两座,北馆就是在韩家潭李渔的芥子园。现在,南北两馆都彻底地没有了。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专门到草厂三条黄德智家找过他,可惜主人已经换了,新的女主人知道黄德智,却不知道他确切搬到哪里去了。草厂的老胡同还在,还保留着当年的老样子。
如同一位老友,即使阔别多年,依然故我,站在那里,就像那无数个难忘的夜晚黄德智送我到胡同口,站在那里向我挥手的样子一样。晚雾迷蒙,凄迷昏黄的路灯下,一种小院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的感觉袭上心头。(作者: 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