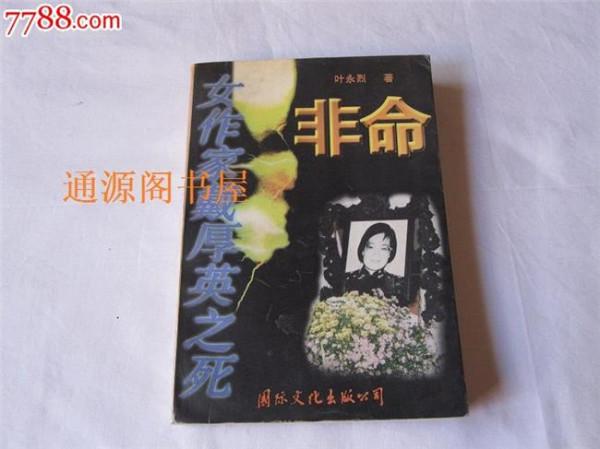戴墨哪年的 戴墨:小凡的黑豆 | 悦读
小凡是我表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她了。表妹在我心里是个特别真诚的人。小时候我们常在一块儿捉迷藏,轮到表妹,她总是逮不着一个人。焦急的表妹就会求助于我:老姐,人藏哪儿去了?我看一眼表妹,故作沉思状说,该不会藏在鞋窠里吧?表妹就会跑去翻看我爸的那双老水靴,往深里瞅了又瞅说,不在这里。我说抽屉呢?她又立即跑去拉开我家唯一的一张三屉桌,再摇摇头说,不在这里。

我笑到肚子痛,不得不弓起腰。表妹也跟着笑,笑了一会儿问我,老姐,你笑啥?
小我一岁的表妹心里没有敌人。她不知道别人捉弄了她。
那年放暑假,表妹把她的新衣服落在栅栏上了。我喜欢表妹的粉花外套,就动了小念头。表妹丢了外套,挨了姑姑骂。我心里扑通扑通欢跳着,盼表妹快点回家。

表妹走了,我把粉花外套套在身上,在外面疯玩了一下午,回家怕我妈看见,掖在了柴堆里。我妈还是发现了,厉声地喊我让我给表妹去送衣服。
毕竟做贼心虚,我跑得像兔子一样快。
表妹比我低一个年级。她念到初中毕业就不念了。表妹学习很认真,常常一个晚上也算不完一道题。表妹是班上唯一可以不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每到期末考试的日子,老师说,朱小凡,明天不用来了。最初,表妹还会问老师,为什么不来了?经历多了,表妹就不问了,她会认真地点点头,然后收拾自己的书包。表妹的假期总是比别人来得早。如果有亲戚问,小凡,期末考了多少名啊?表妹就会空洞地张张嘴,莫名地笑一笑说,老师还没排到我呢。

我读高中的时候,表妹已经参加工作了。她去了姑父所在的一家齿轮厂。进到车间的表妹,像一枚不合时宜的齿轮被传来传去,好像卡在哪里都不是地方。后来,表妹成了厂里一名清洁工,清扫澡堂。表妹对自己的工作是满意的,这是唯一不需要拜师傅的工种。表妹不怕苦,也不怕脏,就担心被师傅骂是猪。

表妹在厂里从没评过先进,但表妹经常受表扬。比如别人都下班了,表妹还在收拾卫生,瓷砖、镜子、手盆、便池,还有高高的玻璃窗,都被表妹擦拭得明晃晃的。夏天,墙角的野花开了,表妹还会掐下一朵插在塑料瓶里,或红或粉的那一枝野花就使得氤氲的澡堂子瞬间多了几分妖娆。
一年四季,表妹从未迟到过,唯一给自己请过一次假,是怀孕九个月的一天,她觉得肚里的孩子像是一分钟也不愿等了。表妹的判断是准确的,果真没走到产房,孩子就伸出了一只脚。姑姑气得直吧嗒嘴,都是先出头,哪有先出脚的,这孩子以后指不定怎么难缠,一个傻妈再养个难缠的孩子,唉,将来这日子可有的过了。
表妹从不跟谁说长道短,也没有人会找表妹说长道短。在齿轮厂表妹没有朋友,表妹似乎也不需要朋友,她总有干不完的活儿。表妹做事跟她做人一样,是实在的。多年后,国营企业大改革,很多人都在换岗,有的人连工龄也给买断了。只有表妹像进了世外桃源,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跟她攀比。
再见表妹是在一次葬礼上,我们共同的表亲去世了。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我分辨着孩提时的记忆。表妹变化很多,有了白头发,以前那一口四环素牙,色泽好像更加的深了。但表妹留给我的真诚却没怎么变。
表妹悄悄告诉我,她学会抽烟了。表妹还用她的一根手指划动了一下被烟熏得暗淡的门齿,仿佛她的手指是一根桨,能破开心间隐藏的一条暗流。继而,表妹问我,老姐你抽烟不?我说不抽。她便眉开眼笑地说,不抽最好。呛得睡不着觉。
我说,那就别抽了。
她说,不抽更睡不着。
在这之前,我已听说了表妹琐碎的人生故事。和常人一样,表妹结婚生子,日子平平淡淡。和表妹结婚的那人算得上一个酒徒,不喝酒时是一个挺好的男人。酒灌下去就不知道是谁家的男人了。表妹先是闹别扭,然后是离婚,一个人磕磕绊绊带大了孩子。孩子养大了,就离家出走了。
表妹说,早知道她要离家出走,让孩子慢点长就好了。表妹说完这话,自己还捂嘴笑了一下。
也许,女人的一生大都是相似的,几句话就说到头了。表妹的人生也就更简单些。不同的倒是烟火气息的背后那吞咽的苦或空,表妹比常人似乎要耐磨些。因为逆来顺受的性格,表妹更习惯于接受,她不知道生活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她只意识到生活到最后,好像没有什么能让她一把攥住。既然都攥不住,就松开手吧。就像当年,老师不让她参加期末考试,表妹便不再考试。
那天我和表妹站在一棵老榆树的伞盖下,难得说了一会儿话。我们对话的过程像解一道数学方程式,慢慢淡化了表亲逝去的悲伤,也淡化了生活本身和女人本身所带来的那些小忧伤。
表妹说,老姐,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
九月的风掀动了表妹额前稀疏的刘海儿,还有表妹浓密的睫毛。睫毛上方的眉毛还像小时候粗粗黑黑的,一直连结到眉心。睫毛下方的眼睛也还是小时候豌豆似的憨憨的样子。变化的只是脸上的毛孔比从前粗糙了。岁月到底是催人老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老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清早的天还阴着,一阵阵的哀乐从不同的角度飘进耳朵,抬眼就能看见年轻的表亲化成青烟的高大烟囱。我的心情还卡在那一缕青烟的寂寞与锥痛之中,自然回答不了表妹的问话。
望着岁月在表妹脸上刻下的条条细纹,我脑海中浮现的仍然是小时候的表妹。她单纯地面对我的捉弄,也还是那么淡然与温和,我从没看过表妹愠怒或发脾气的样子。我知道我依然爱那个平静的甚至有点好玩的表妹。那时的我们,前面总有那么长的路可以肆意奔跑。
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我们渴了饿了或困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怀抱。倏忽间,日子过到了下午,然后就是慢慢到来的黄昏。那曾经大山一样的遮挡,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一座接一座地塌下去了。
一瞬间,这个世界变得那么松脆而孤独,让人一眼就看穿了它最终的把戏,而我们也仍然鼓着足够的勇气,向着一个方向潮涌。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朝着那个方向去,我们并不比表妹幸运多少,倒是表妹比我们少去很多心机。
表妹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表哥和表姐,他们都生活在国外。表哥和表姐偶尔会给表妹寄些外汇,嘱咐她把日子过好一点。但那也仅仅是嘱咐。表妹说,她不缺钱。表妹沉吟着,我想听到沉吟之后的话,但表妹叹息了一声,便岔到别处去了。
表妹的孩子是个女孩。出走的时候还不到十七岁。
表妹说那孩子一次都没有联系过她,真够狠心。表妹说这话时,眼睛望着别处,睫毛还是那么浓而密。外面的伤悲好像也不能挤进去。同样,它内里的损耗也并不能透出来。除了打扫澡堂时,表妹会盯住那些瓷砖或污渍,不让它们漏掉,余下的光阴,表妹的目光总是在别处游荡。也许只有别处的光阴,能削弱她的茫然和思虑。
这样的凝视实在太过沉重。我便重起了话题,问表妹,平时有啥爱好。表妹说有的。她们那儿的社区新建了大食堂,还有了教唱班、舞蹈班什么的,想学的都是免费教。她三顿吃食堂不用自己再糊弄自己。唱歌跳舞什么的她从小就学不来。但她喜欢那个空旷的读报中心。一个什么人还曾拿了一本书给她,她现在天天都在认认真真地念书。
表妹说,送书人还送了她两只陶罐。陶罐一黑一白。告诉她黑的代表悲伤,白的代表快乐。那只悲伤的陶罐,被表妹搁在左手边,快乐的那只在表妹的右手边。
我听得入了神。陶罐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都不难想象,我暗自思忖的是那本书,那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会让表妹有了念书的兴致?
表妹说,老姐,你知道我上学时学习就跟不上趟。我不是念书的料。
表妹说,她上读报中心,就是想看看报上有什么奇闻,说不准会找着孩子的线索。有一天,表妹翻到晚报的夹缝,看到一具没人认领的尸首,就跑去了,走近一看是个男的。那天,表妹在停尸房的外面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表妹说,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男人,真可怜!
表妹说,她真想帮他把脸擦擦,那脸都是尘土,太脏了,看不出人的样子了。但表妹还是没有擦,她想起擦镜子的毛巾,还在澡堂外面的挂钩上挂着。
表妹说,她自己的孩子今年也该二十了。可她想的还是孩子小时候的事儿。喂奶,拍嗝,洗尿布,抱着她去打预防针,风里雨里的竟都过来了。后来就抱不动了,比她还高。再后来,就会跟她吵架和顶嘴。
表妹说,孩子出走的前一天,不知为着什么事扔过来一句话,孩子那话比一把剪刀都扎心。孩子吼着说,傻妈,你整个一傻妈!
表妹说,她长这么大从没打过人,更别说打孩子。但那天她给了孩子一个嘴巴……
表妹说,老姐,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打孩子?
看着表妹灰暗又漏风的牙齿,我突然红了眼圈。想到小时候欺负表妹的情景,心里一阵难受,我说对不起,小凡。
表妹见我滚出了泪水,突然笑一笑说,老姐你咋哭了!我都不哭了。记得我爸没时,我天天哭。我妈没时,我也天天哭,但没像哭我爸那么伤心。和我爱人吵架,我也天天哭。等孩子走了,我就不哭了。
表妹说,老姐,你帮我分析分析我到底错在哪儿了,为什么最亲的人也都嫌弃我?比如说我哥和我姐吧。我姐总骂我是猪脑子,但我姐骂我是心疼我总被我爱人骗,挣点钱都被他骗去喝了。我哥骂我和我姐的骂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但我不能对旁人说。说了怕我哥难堪。我哥巴不得我快点消失(表妹说到“消失”,竟捂着嘴笑了那么一下),从我进厂子那天,我哥就盼着我消失。但我上哪儿去呀,后来我哥就离开厂子了。
表妹又说,老姐你相信我,我从没干过一件让我哥和我姐丢脸的事。我都敢拍良心说。你信不老姐?
我说,我信,小凡。我伸手握了握表妹的手,表妹的一只手像这个深秋的早晨,有一点微凉。
表妹说,老姐你不知道,我整宿整宿不睡的时候,我也嫌弃过我自己。我“啪啪”打自己的脸,说离家出走的人咋就不是你呢?我天天念叨,孩子,你回家吧,让我替你走……后来,我就不敢恨自己了。打开始念书,我就不恨自己了。书上说,心里有恨会长肿瘤。我不想长肿瘤,我不想让我姐再惦记我,我姐说她生活的那地方离我太远了。
老姐,刚开始念书说啥都念不下去,心乱,可一看到人家好心送我的陶罐,我就逼着自己念。那俩陶罐那么好看,那人还说,看看哪个陶罐先装满豆子。后来,慢慢念熟了就念进去了。好像心和字儿贴到一块了。老姐,现在才明白你们为啥都那么爱念书。念书真能使人忘记忧愁。
表妹的话,把我逗得笑起来。
表妹说,老姐,你是不是笑话我了。
我说不是,是你对念书的认识让我惊奇。
表妹说,念书念高兴了,就往白色陶罐里放一粒白豆。忧愁的时候,就往黑陶罐里扔一粒黑豆。开始,扔黑豆的时候多。黑豆一多了,我就让自己从头念。念的时候心里想着白豆,白豆,就真把高兴给念来了。
我问表妹,看的是啥书?
表妹张了半天嘴,还往天上地上左边右边撒眸了一圈,也没撒眸出个什么来。说,老姐,看我这臭记性,那书叫啥名了?
我说,书名记不记得住都没啥关系,只要读着开心就好。
表妹说,嗯哪。
表妹说,老姐,才知道念书能让人着魔。见我愣住的样子,表妹说,有时念着念着就能把我想的人给念来。有一回,我妈给我托梦,跟我好顿哭,说都是因为怀我的时候她和我爸打架打的,让我脑子缺了一根弦儿,现在后悔也晚了。
老姐,你说我妈多有意思,咋让我做这梦。后来,我就想孩子骂我的话,可能孩子说的没错,我真是一个傻妈。有一次,孩子肚子疼,我就让她吃去痛片,都不知道孩子是来例假了。老姐,你说我这妈当得多不够格,孩子跟我不亲,我不能怨孩子。以前,我和我前夫天天当着孩子吵吵,估计孩子早都烦透这个家了。以前,一想起这些我就得哭一会儿,哭着哭着就哭抽过去了,觉得对不起孩子。
表妹说,每次念哭的时候,她就一手拿黑豆,一手拿白豆,瞅瞅左手又瞅瞅右手,不知道该放白豆还是该扔黑豆。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她就重新起头。啥时念的不想哭了,心宽敞了,她就往陶罐里轻轻放进一颗白豆……
表妹突然呵呵笑起来,像手里又攥住了一颗白豆。
表妹说,老姐,你信不信,有一天我把你也给念来了。
我惊得眼珠子都要爆了。
表妹说,有一天,念着念着她就想起小时候藏猫猫的事儿了。我告诉她艳玲可能藏在鞋窠里,她就信以为真去扒拉大舅的一双雨靴。现在才知道自己傻,人咋能待在雨靴里呢……
表妹的话,让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觉得我多年的隐忧突然应验,表妹到底还是记着呢。
欺负人是有罪的。尤其是欺负表妹这样的人。
我紧张地盯着表妹,就像等待表妹一次迟来的宣判。等了一会儿,表妹突然说,老姐,要是咱们还那么大该多好。
我仰起脸,一只鸟正飞过枝头。表亲火化的青烟,淡得已经看不清了。天空似又镀上了一层金色。才发觉太阳早都升得老高了。轻轻拍了一下眼神重又活泼起来的表妹,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那天,我弯腰给表妹鞠了一躬。我说,谢谢你小凡,谢谢你给老姐扔的不是黑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