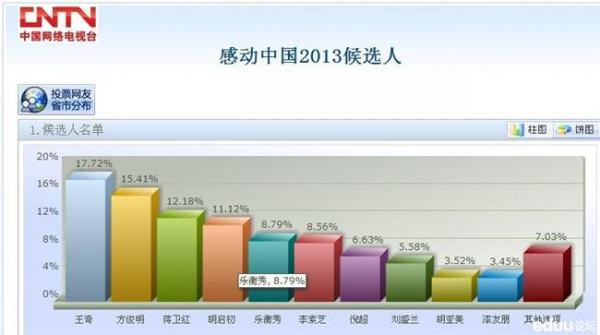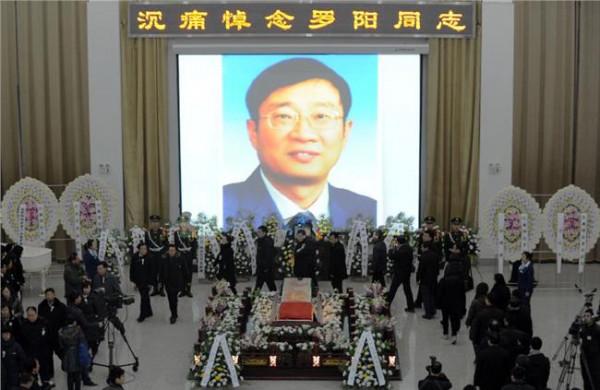感动中国2005王顺友 [面对面]王顺友:马班邮递员
同期声:路太远,山太高,走一趟马班邮路下来要老一两岁
遭遇过生死的瞬间 承受着难言的寂寞
一个人 独自走过26万公里
同期声:在山上睡,路上睡的时候,睡一个晚上和过了一年一模一样
背负对家人的歉疚 留下一身的伤痛

他对这份工作有着怎样的执著
同期声:马班邮路是必须要有的,山里的老乡需要我们。
《面对面》王志,专访马班古道上的邮递员王顺友
王顺友,苗族,1965年生
小学文化,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乡邮员。
送信20年,步行26万公里,相当于走过21回长征。每年在路上送信的时间至少330天,20年来没延误一个班期,没丢失一封邮件,投递准确率100%。

2005年被授予全国邮政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解说:对于王顺友来说,2005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在马班邮路上孤独行走了20年后,今年,他被授予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他的名字也在今年开始被社会和公众所熟知。

记者:你今年好像正好是40岁?
王:今年是没有满41,40岁是满满的40岁。 记者:别人猜你会猜多少岁? 王:别人猜,这段时间休息好,年轻了,我在马班邮路上走的时候,像50多岁,快60岁的人了。 记者:但是你为什么会看起来那么老呢? 王:我的工作太苦了,在邮路上路太远,山太高,工作太苦,这点就亏身体,走一趟马班邮路下来要老一两岁。

解说:王顺友所在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接合部,全县29个乡镇大都分布在陡峭高耸的群山之中,地理环境极其闭塞,邮政成为当地人和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当地有些地方,邮件只能沿着马班踩出的羊肠小路,用骡马驮着去进行投送,因此被称为马班邮路。全县现在共有马班邮路15条,王顺友走的是其中较长的一条,单程180公里,要走上整整7天。
记者:为什么要七天呢,180公里你一天走多少公里? 王:问题是我们那些山路不像平路,它海拔高,(让人)胸口要爆炸似的,
记者:多高?
王:4000多米。
记者:一天就只能走20公里不到? 王:一天只能走20多公里,我们山里的公里跟平地的公里不一样,平地的公里走了三公里,山上只能走一公里,山上的路边走边歇,路很难走。
牲畜也是有脾气的,边走边歇,这样走。毕竟牲畜有脾气的,驮着邮件,驮着人吃的东西,还驮着马料,这些就重了。马和我来说都是很多故事的。我工作20年来,我已经喂了30多匹马了。 记者:怎么会养那么多马呢? 王:马会老,在这个邮路上太苦,它有些地方用了几年以后就走不动了。
记者:你自己的给养呢?要带多少? 王:就是带糌粑面吧,一次带个三四十斤,把糌粑面炒熟了以后。 记者:什么炒熟了? 王:就是麦子、苞谷这些炒熟以后推出来。 记者:磨成粉? 王:磨成粉以后装在小口袋里面,在山上用山泉水舀起来调着吃。 记者:不能吃热饭吗?自己做饭能行吗? 王:有水的地方也能会煮点饭吃,带把米、带把菜就可以煮饭吃。
记者:为什么不住老乡家呢? 王:有些地方没有老乡,大山里没有人户,找不到人户的地方就必须在山上睡。 记者:安全吗? 王:要说不安全还是安全的,要说安全还不算安全。
记者:怎么说? 王:在心里想着,最怕的还是怕狼、熊。 记者:遇到过吗? 王:狼、熊遇到过,但是我的感觉,这些野生动物还是怕酒,喝了酒酒气大,野生动物都不到人面前来,跑得远远的,晚上就叫、吼。马看见野生的动物它就跳、抓,但是一个人,总还是睡不着觉的,都是喝了酒,自己麻醉自己,我迷迷糊糊就过了,但是心思是没睡觉的。有些时候不想干了,这么孤单,不想干了。
记者:怎么个孤单法?
王:时间长了,我都变成了一个不肯说话的人了。 记者:怎么排遣这个孤单呢? 王:喝酒,这个酒特别有用,在山上特别有用。 记者:怎么有用? 王:它能给你壮胆,喝了酒也驱寒。
记者:喝一口,哪儿过得了瘾,你怎么控制? 王:你喝酒,你要心里想着喝三种酒,一种是走累了,休息好了,喝杯酒,喝辛苦酒,过了平常喝,有伴儿喝,要喝人情酒,你倒一杯酒给我喝,或者端杯酒给我喝,我是喝人情酒,都是人情,过了还要喝一种酒,明白酒。
记者:那喝完了都是不明白的,喝明白酒? 王: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算了,不要看了,装起来,算了,这是明白酒。问题是你包里有邮件,喝得把东西弄掉了不好。
记者:一顿喝多少?还是一天喝多少? 王:白天不喝酒,白天走路的时候不喝,走到晚上了,到一个地方休息,把马喂好了,帐篷打好了,自己吃的东西吃了,就喝点酒,就自己唱点歌。 记者:你会唱歌? 王:当地的四句山歌会唱的。
记者:来一段怎么样? 王:我唱一段,就是我在邮路上孤独的时候唱的歌。 “太阳出来照山坡,照亮山坡白石头,要学石头千年在,不学半路丢草鞋,我家住在银盘坡,心里有话好想说,天天出门为人民,家里只有妻一人。”
解说:王顺友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妻子在家务农。20年来,王顺友每年在家的时间只有大概30天,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妻子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记者:那你二十年都这样 ,你妻子就没有怨言吗?
王:她也不会说什么。山里人都是不会说什么东西的。我想到不做工作,那我怎么向父亲交代?我父亲就会说我做逃兵了。 记者:你不做有别人做嘛。 王:我不做肯定有别人做,但是像这样时间长那是不可能的。大不了一至两年就退出了。 记者:你的意思别人干不了那么长? 王:干不了那么长。 记者:你为什么干得了那么长? 王:对我来说,我父亲给我撑着,经常教育我。
解说:王顺友的父亲王友才是新中国成立后木里的第一批邮递员,在邮路上走了24年。1985年,父亲退休,王顺友顶替父亲的班,也成为了一名邮递员。
记者:子承父业是你的选择还是你父亲的选择? 王:是我父亲选给我的,父亲他说了,干这份工作是很光荣的,你好好地干,班交给你了,你必须要干好。 记者: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愿意接父亲这个班吗? 王:当时来说是愿意的,高兴的,有一份工作了,好,高兴了。后来跑起来后悔。
记者:怎么后悔?
王:不接父亲的班就好了,这么苦,这么累。 记者:你父亲当时怎么交代您的?
王:他说不要损毁、丢失、请别人代运。 记者:20年你就没有出过差错? 王:没有,没有出过,邮包随时都不离身,邮件,一般来说,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在很安全的地方放好。 记者:丢失过吗,邮包? 王:没有丢失。邮包一般不丢失的,因为我时刻都想到邮包,它怎么可以丢失?
记者:20年一次都没有? 王:1988年的时候,雅砻江没有吊桥,是过溜索的,把索捆好,拴在腰上。溜过去的时候,刚要到对面的时候,绳断了。
记者:哪个绳断了?这个溜索断了? 王:溜索的绳,拴在我身上的绳,绳断了,弹下去,把我弹到沙滩上,邮包就掉到江里去了。 记者:人没到江里,邮包掉在江里去了? 王:邮包掉到江里了,我的水性不好,我到河边找了一根小树棍,插到齐腰深的地方捞了好一阵子,才把邮件捞上来了。
记者:邮包没有打湿吗? 王:邮包没打湿,但是我裹好的邮包,用塑料布裹好的。
记者:为什么要拿塑料布裹上? 王:雨季来说,下雨了,这个布袋子是透雨的,透进去邮件就不好了。要用塑料布裹好,下雨它都不透,送到他们的手里还是好的,干净的。
淋湿了雨了,里面的字就没了,这样不好。 记者:怎么能保证这个邮包不弄脏呢?这个很难,跋山涉水。 王:很难,下雨了最难了,下雨时保护干净的邮件是很难的,连自己的身全是泥水,包必须要用塑料布裹上,才能保护安全。
记者:这个邮包对你有多重要? 王:对我,在我心目中是无价之宝,跟我生命一样贵重。2000年的时候有一天,我走在察尔瓦山,离我两丈多远的路口上,有两个人拦住我,说站住,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我说我是送报纸,送信的,没有什么(财物),要命就有一条,什么都没有,我就边说话,边把柴刀抽出来拿到手上。
记者:真要动手,你一个人也打不过他们俩啊?
王:打不过,我肯定打不过,但是这两个人呆了一下,好像看到我穿着邮政制服,他们心里就有点虚了,我就趁机冲过去了,冲过去,后来就没出什么事。
记者:真抢你的话,你身上有什么呢,有东西吗?
王:他抢我,就只有邮件,邮件他抢去也没用,身上只有路上用的几十块钱,还有就是一点马料,还有我吃的东西,就是这些,其它没有,但是只是遇过一次,但是很多人在山上都遇到过。
记者:你把邮包给我,我放你一条生路。
王:这样的话,我肯定不干,我拿着柴刀呢,我肯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的邮包没有,那我也没了。
记者:这是你们工作守则上写了吗?邮包比我自己的生命最重要,还是你自己工作中这样认为的? 王: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 记者: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王:因为我干的这项工作就是,送邮包就是主要的工作,邮包里的东西就是重要的,我没有邮包,邮包里没有邮件,我做这个工没意义了。
解说:王顺友走的这条邮路路程长,而且十分艰险。沿途经过的察尔瓦山,海拔5000米、一年中有6个月覆盖冰雪,而穿越的雅砻江河谷海拔只有1000米、夏季气温却高达40摄氏度。此外,邮路沿途还有大大小小的原始森林和山峰沟梁。
记者:那路那么难走,受过伤吗? 王:受过伤。我这儿受过伤,在邮路上受的伤。 记者:怎么受的伤? 王:这个伤是在倮波乡一个小河边,下大雨就把小路冲没了,我牵着骡子在那个地方走,骡子打滑下去了,我拉骡子,连我都摔下去了,脑袋栽在树根上,就撞破了,这半边脸也撞到过,这个是小时候跟妈妈去背柴,摔倒的。
记者:你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王:最重的就是骡子踢我的肚子这次。 记者:怎么受的伤? 王:我送邮件到倮波乡,有一个地方叫九十九道拐,走到最险的地方,就是山岭这儿。
解说:九十九道拐地势极其险峻,是一条在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上凿出的拐连拐、弯连弯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还要手脚并用才能通行,即使是当地人也不敢轻易行走。
王:我把骡子放在前面走,我走在后面。突然林中飞出一只野鸡出来,就把骡子惊倒了,骡子就乱踢乱跳的,弄不好,如果是再溜下去,摔下去,连邮件都没有了,赶忙跑上去,刚一接近,去拉缰绳的时候,(骡子)朝我的肚子蹬过来,蹬在我的肚子上,当时我就坐下去了,后来过了几分钟,我说这儿完了。
记者:什么感觉呢,见血了? 王:当时我就觉得我一个人,这个骡子这样踢了我,怎么办?当时气都喘不出来,我说不能死啊,在路上。 记者:想到死,那么严重? 王:当时很恼火,我已经要到倮波乡了,已经离不远了,但是我起不来,后来我找根棍子,杵在地下,边走边歇,边歇边走。
空镜:当时,王顺友并不知道自己的肠子被踢破了,忍着剧痛,他送完了邮件。
记者:这样的状态你走了多远?
王:这样子走了将近4个小时的路,4个小时的路,走到倮波乡,到倮波乡把邮件交了,我就觉得最好再忍一下,也没有跟谁说。
记者:你为什么不说呢? 王:问题是我说了也没有办法,医疗条件没有,有医生,只是医生做不了手术,一个是这些药也没有,我就赶紧赶回木里,县里有办法,就边走边歇,边走边歇。
解说:受伤后的第九天,王顺友在县里接受了手术。当时,他的腹腔里已经全都是脓血,医生说,再晚来一天,王顺友就没命了。
记者:九天前的事了?
王:九天前的事了,一点东西都没吃,就是喝点水,喝点米汤,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觉是根本睡不了,又是冬天,太冷,在手术台把麻药一打,痛都不见了,就像在睡梦中,灯照在我身上,我想完了,我肯定要死,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的孩子还小,一个七岁,一个才五岁,如果我死了,孩子没有爸爸了,妻子肩上的担子更重,我不能死,再一个我也不想死,后来我就坚持了下来。
我的伤口好了,我就心里想,我不想干这份工作了,连老命都要送掉。
解说:王顺友最终从手术中挺了过来,在医院住了43天。而这43天,也是他20年来唯一的一次长假。手术后,王顺友体质受到很大影响,直到现在,肚子还经常痛得厉害。
记者:这次是自己不想干了,后来怎么转过弯了呢? 王:后来我出院以后,父亲来看我,他就说还是病好了,还是要把你的邮路跑好。 记者: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王:我想在邮路上的乡亲们对我也好,人们都不干的话,我觉得有些方面交代不了,还是坚持下来。
记者:20年这是一次,还有别的吗,打过退堂鼓吗? 王:这次是最严重的一次,经常想打退堂鼓,但是我想起来打退堂鼓,我对不起我老父亲,对不起邮路上的乡亲们,他们就把我当作是他们的亲人一样,每隔七八天,都在小路上张望着我。
解说:由于交通和通信条件闭塞,很多乡亲和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和途径就是王顺友所带来的信件和报刊。有时候,除了送邮件外,他还无偿替乡亲们带一些生活用品和种子之类的生产资料。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王:因为我们处得很好,人熟悉了,他们需要我带的小的东西我可以带,如果重的东西我也带不了。 记者:能帮你增加一点收入吗? 王:收入增加不了,我的收入大不了他们给我一顿饭吃,给我一杯酒喝,给我点马草,我的收入就这个,其它收入没有。
记者:感情已经处到这个程度了,可能没法说钱的事了。 王:没法说钱的,但是钱也不多,带的东西也不多,钱也不多,也不好说钱,人熟了,一说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东西,没法说钱。
记者:但是人家老让你带东西,这个五块,那个十块,这样下来你受不了。 王:问题是这样的,不是全体老乡全部让你带,因为只是一家两家,这样的,全部都让我带,我带不了,这次帮你家带点,下次帮他带点,这样的。
有时候我还帮他们写信,写完信还要给他们贴邮票,贴邮寄费,这样的事太多了。 记者:你自己掏钱帮他补贴? 王:嗯,自己掏。 记者: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呢? 王:我走到他的家,吃他的,喝他的,马草他给的,我就觉得邮票也不贵,信封也不贵,没什么跟他好说的,
记者: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个工作能挣多少钱? 王:我们单位现在收入不好,工资有时候都发不起,跨月跨月地发。一个月就是800多块钱。
解说:为了方便邮递员,各乡都设立了投递点,王顺友只需要把邮件送到乡里就可以了,可是他却常常绕道把邮件直接送到乡亲手里。
记者:按你的工作规程来说就送到乡政府就可以了? 王:送到乡上,给我签字盖章就算数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在路边顺路的,或者绕道走一点的,人熟悉的就给他带去了。 记者:绕道走一点点的什么意思? 王:几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的路。 记者:那叫一点点?
王:转一圈吧,转一下
记者:就送一封信 王:送一封信,贵重啊,(比如)就是一个录取通知书,他考一个学校,学生不容易,耽误时间了,他报不了名。 记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王:人熟悉了,为了娃娃出来读书,快点给他带去。
记者:你不那么送领导也不会批评你。 王:我不送领导不会批评我,但是乡政府不可能给他们送去,有时候他们跑来取一封信也不可能,时间耽搁长就害人家娃娃了。 记者:老乡的反映呢?你送过去以后? 王:送过去以后他们对我很感谢的。
记者:对你来说,你这个工作到底是做一个好事还是一项工作?在你的感觉上来说? 王:我的感觉就是做件好事,他对我很感谢,我也很高兴,很愉快。有一次有个陶老五,白碉乡的陶老五,他家隔乡政府十多公里。
记者:家里面离乡政府还有十多公里? 王:对,他的女儿外出打工了,没有音信,跟我说,如果有他的信,那就给他送去,或者跟乡政府说清楚,有一天下大雪,有一封信,我看是陶老五的,白碉乡呷咪坪村的陶老五,也许是他女儿写来的信,我就把邮件交到乡上,我又在雪地里走了十多公里,跑到他家,他说请我念给他听,他打开以后,里面就有些照片,他女儿和女婿、孙子的照片全在信封里,我就把信念给大家听,听完了以后,他们家就哭了。
记者:你说什么? 王:哭了,因为他女儿出来打工,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外孙了。他们高兴哭了,我也流泪了,我说我再累、再苦我都觉得值得了。
解说:王顺友常说,自己有三个家,一个在山上,一个在路上,一个在江边。路上的家就是马班邮路。江边的家是他住在雅砻江边父母的家。而山上的家是他和妻子儿女在木里城外的山腰上建起的小家。三亩地,三头牛,十几只羊,还有四间土坯房,这个家全部是由妻子一个人撑起来的。
记者:跑一趟以后,回家能待几天呢? 王:我们是有规定的,有班期规定的,去一趟回来,家里只能歇一晚上。
记者:你有多少时间管家里的事呢?有没有时间、精力?
王:儿女来说,我没有背过一天,也没有和他们玩过一天,对我妻子来说,在家里她支撑着这个家,抚养儿女,我对不起她。 记者:你上完班以后不就可以抱孩子,料理家务吗? 王:时间太短,差不多有些时候睡一至两个小时就要走了,要去取邮件。
记者:从你内心来说,你觉得歉疚吗? 王:很歉疚啊,对不起她,但是对不起她我也没有办法,我想给她补偿,但是我想补偿她的时候,已经老了。
解说:2004年,14岁的女儿小英自己到几百公里外的查布朗区打工挣钱,在建筑工地给人搬石头,干了整整5个月。女儿说她跑远了打工,就是不想父亲因为来找自己,而耽误了工作。
记者:那孩子会有比较,别人的父母不是这样的。
王:我这个是逼出来的,对我内心来说,我不想和他们分开,但是我的工作条件就有这个限制。
记者:你问过孩子吗,你怎么看爸爸?你怎么看爸爸的工作?
王:这个我没有问过。
记者:那妻子和孩子有没有说让你换一个工作,或者跟领导要求一下,换个短一点的线路,跑了20年可以照顾一下? 王:孩子没有说,我妻子说过,妻子她跟我说过,你的岁数大了,一个是你工作太苦,一个你这么几十年来,一身的病,你是不是跟领导要求在单位里面做一点轻巧的活,或者在街上送信送报。
记者:你说了没有? 王:我不敢,我知道的,我知道街上的工作,因为我在街上顶过班,代过班,我知道的,他每天都有送的,每天都要送报纸、信件,就像头发丝一样的,工作很多,我做不了,因为我车也骑不了,不会骑车,还有一个是在街上单位多,复杂得很。
解说:由于长年在高海拔的山区奔波,木里县的乡邮员最容易得四种病:头痛病、风湿病、胃病和肝脏病。他们往往干到47岁左右时,就再也没有气力跋山涉水了。47岁,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极限。因此在木里,乡邮员在45岁就可以提出退休申请。
记者:你这样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呢? 王:肯定是四十五六岁就走不动了,到走不动了为止。我真的走不动的时候,我再跟领导写申请,再跟领导说。 记者:你现在名气大了,又是全国劳模,又是五一奖章,回去会不会照顾你呢? 王:但是我的名气大,我还是一个人,不是铁棒,是根铁棒它都会朽的, 记者:回过头来说,对你会不会有压力,另外一种压力,本来身体已经不行了? 王:有的。
这种压力是有。问题是,我现在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工作更要比以前做得好一些但是我的身体就比以前都不好,不如以前了,但是这个压力有了,但是必须坚持。 记者:你会希望你的儿子接你的班吗?像你父亲那样?
王:我想现在不需要他走这个邮路,这个邮路是最苦的,真正苦的。孤独最苦,爬山最累,一个是娃娃读书,他读了书的娃娃不能坚持吃苦的,吃不了苦,山上孤单寂寞,他肯定把工作干不好的。 记者:你是担心他不行?
王:我担心他不行。 记者:但是你没有问一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你这个班? 王:没有问过。但是我不愿意他搞这个工作,我这辈子经历过了,太苦,太累,但是我想马班邮路是必须有的,而且山里的老百姓需要我们去送文件、报纸、信件,山里的老乡需要我们。
空镜:山歌:“云南那边歌最多,要用骡子马去驮,一垛山歌唱三年,山歌唱完又去驮……
![感动中国2012陈斌强 陈斌强[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https://pic.bilezu.com/upload/c/3e/c3eaf620313eb23e2771b790c6c465c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