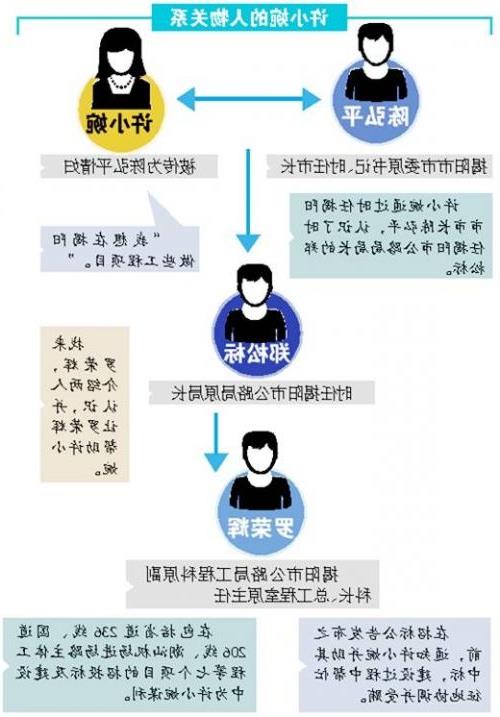许子东个人资料 如何评价许子东这个人?
近日,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凤凰卫视栏目“锵锵三人行”嘉宾许子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许子东讲稿”:《重读“文革”》、《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越界言论》。趁着许子东到北大和人大开讲座的机会,本报特约记者就其人生经历、文学研究,以及学者上电视等问题专访了他。

成长越界:从城市到乡下
下乡不是受折磨
在1949年之前,许子东的父亲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并且做过上海私人医生医师工会的秘书长。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就辞职了。幼年时,许子东并不知道自己家庭的特殊性。直到他上小学三四年级,看到二哥的入团申请书,这才知道三个哥哥中,二哥和自己是同母异父,大哥和三哥则是同父异母。只有自己这个小儿子,亲生父母都健在。

196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许子东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的大哥毫无预兆地回到了家里。此时,他已经是北京那个大学两派造反组织之一的小头头。临走时,大哥压低声音对父母说,家里那些西装、旗袍的照片,尽量烧了。如果有金银首饰之类,尽量处理掉……然后又恢复正常声调说,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大哥走后,家里的煤炉确实烧了很多照片。
不久,在东北石油学院上学的三哥给家里来信宣布,和父亲、继母划清界限,并称,再也不要你们的臭钱了。
小学最后一年,许子东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成为了红小兵,并去了自己班主任家里抄家。当他和同学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一条弄堂的别墅抄家时,另一个弄堂的小孩跑来叫许子东,说他家也被抄了。许子东一愣,赶紧跑回了家。
许子东的家被抄了三次,他很快丧失了造反资格。
1970年4月1日11时零8分,一列满载知青的火车在上海北站启动,父亲、母亲、二哥和几个没走的中学同学来给他送别。经过辗转换车之后,许子东到达了目的地——江西广昌甘州公社千善大队古坊生产队。这一次,他从城市越界到了农村。
上中学时,许子东曾经到上海郊县松江参加过几个月的“三秋劳动”,因此,他到古坊生产队后并没有觉得不适应,也没有觉得是受折磨。相反,他和农民在干农活的时候,看到了这些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者的职业道德。
古坊全都是梯田,而且弯弯曲曲。第一个人下去不能用绳子,必须靠目测,然后蹲下去插一条秧,要正好插到那个弯口,保证秧苗插得齐整,俗称“开头路”。在古坊,全队三四十个男人中,只有三四个人能干这个活。按规矩,开头路的人不用在这块田再插秧,一直休息到“转移阵地”。
开头路之后,插第二条大家还得谦让,因为第一条插得很好,插第二条的人俗称“跟头路”,水平也要高,如果插得不好,后面的人也没法插。开头路的人,一直受到尊敬,即使到了耕田、割稻时,开头路的人仍然拿10分,大家也不抱怨。政治队长、民兵队长等人,到了插秧的时候,一点也不神气,插得不好就排在后面,免得影响大家。
16岁的许子东,当时身高1米82,体重才115斤,他不会犁田、耙田,但是插秧不错,能够“跟头路”。在知青里面,许子东插秧最好。插秧需要不断后蹲,很伤腰,他的脊椎有问题,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在劳动中,最可怕的是蚂蟥,最多的一次,28条蚂蟥牢牢附在了他的双腿上。
上了田埂后,许子东一一拍了下来,满腿都是血。在许子东看来,“今天所谓学术界、文化界的某些人,完全失却专业水平,还自我感觉良好,彼此称为大师,在我看来远不如广昌的农民!”
1973年冬,因为患急性肝炎,许子东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图书馆看了一年书。回到乡下后,他的思想就很不一样了。在那之前不觉得折磨,许子东干农活,吃苦也不觉得,一直很开心,也不觉得周围有什么不对。看完书再回乡下,他觉得很多事情很无聊了,很没意思,觉得自己很可怜了。
“以前我看到领导,我是由衷地尊敬他们,跟他们说话;之后我在心里嘲笑他们,可是我脸上还得对他们笑,甚至笑得更努力,这个才是折磨,而那个折磨一直到现在,没停过。”许子东的经验是,对社会来说,工作创造财富,开会浪费资源;对个人来说,开会事半功倍,工作事倍功半。因为表现积极,公社准备培养他做生产队副队长和大队团委书记。
地理越界:从大陆到美国、香港
辗转三地,香港落根
1976年4月,22岁的许子东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钢八厂。接着,他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七二一大学。1977年年底,高考恢复。许子东报考了复旦中文系和新闻系,还有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按成绩,他应该被录取。不料,七二一大学升格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这样一来,许子东属于大专生,就没有高考资格。
一半时间读电气自动化,一半时间做文学梦的许子东心有不甘。正好他看到了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找到了父亲的朋友许杰,一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华东师大的教授。他告诉许子东,后门是不能开的,考是可以考的,你的外语一定要好。
他和一百多人参加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一共有政治、外语、文学史、作文等四五门,作文题目是《给友人的一封信——谈谈中国现代文学》。许子东用书信体谈到了自己对于郁达夫的阅读经验。最终,许子东进入了六个被录取的幸运儿名单。一个学电气自动化的大专生,越界成为了现代文学的研究生。
许子东的导师是钱谷融先生。他并不专门给学生授课,学生平时在下午都可找他闲谈。但是,一个月有一次讨论课。其他几位都比许子东大十来岁,都是老大学生。后来研究赵树理很出名的同学戴光宗,第一次作报告,就拿出了一份上万字研究胡适的讲稿。
讲完以后,许子东等人就全傻眼了。下个月就轮到许子东,他找到了钱谷融,钱先生说,你考试的时候说对郁达夫感兴趣,那你就写写郁达夫。许子东就用一个月的时间看郁达夫的作品,以自己的观察角度写了一篇读书报告。作报告的时候,许子东心慌意乱,他战战兢兢地读了一下。几千字的报告读完以后,钱先生帮他改了6个错别字,接着,钱先生说,看看能不能推荐到学报发表。
还是一年级的研究生,居然在学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对大学教授而言也算是学术成果,这对许子东无疑是一个大大的鼓励。读硕士期间,他继续做着郁达夫研究,写了十来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有一半经过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幕后英雄王鑫之手,发表在北京的《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上。
他到哈尔滨第一次参加有关现代文学的学术会议时,看见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努力想和《文学评论》的编辑套近乎,他们很惊讶,许子东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居然不认识谁是编辑。
许子东研究郁达夫的成果,后来结集为《郁达夫新论》一书,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里。这套丛书的作者,就是后来被研究当代文学批评者称为“八十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个基本阵容,其中包括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程德培、吴亮等。大部分人也成了许子东几十年的朋友。因为这本书,许子东在29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燕华并结婚。
1987年9月,许子东第二次赴香港讲学,其间遇到了海外学者李欧梵,李告诉他,已经获得了鲁思基金会资助,请许子东赴芝加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同时也请了刘再复、李陀和黄子平。等到几个月后手续办齐,已经是1989年夏天。
在芝加哥,以李欧梵为中心,聚集了一批中国学者,如甘阳、杜维明、林毓生、杜迈克、郑树森、王德威等,大家经常聚集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讨论,从形式主义、雅各布森、布拉格学派到德里达、巴赫金以及福柯等,以至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芝加哥学派”。
1990年9月,已经是副教授的许子东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家也在洛杉矶的香港大学陈秉亮教授被聘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两人一起吃饭时他告诉许子东,或许有新的职位可以申请。
第二年秋天,许子东再次“越界”,进入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去了以后我就懒了,不愿意再回美国拿学位,因为还要考法文,写什么报告。因为你不拿博士学位就不能做教授,所以我就在港大读博士,学费也是学校给的,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那些原来写作的朋友都已经是博导了。这些都是为稻粱谋,比起我在乡下的经历不值一提。”
身份越界:从教授到电视嘉宾和公共知识分子
开学者上电视之风
“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开始筹划时,曹景行就给许子东打电话,说有这么一个三个人的谈话节目,知识分子话题。许子东问怎么录像,他说每天都要录像,许子东说我不来了,我要上课的,就挂掉了。当时,来港后一直在无线电视台播普通话新闻的太太陈燕华知道后就说,有人找你做节目,你问都不问就把他拒绝了,做电视的人不会这样,就好像拍片的人,有片约你至少要拿过来看一看。
2000年,梁文道给许子东打来电话,说“三人行”想访问他一次,话题随意,许子东就答应了。
这期节目是和窦文涛和女嘉宾郑佩芳一起谈话。节目录完以后,窦文涛说我们正在附近茶餐厅一起吃午饭,问许子东以后可不可以再来,比如说每周一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就像今天这样闲聊,话题随意,衣服随便,形象也不必担心。许子东说,要先问问学校,应该可以吧。就这样,许子东由大学教授越界成了电视台常任嘉宾,一做就是十多年。
既然要上电视,太太陈燕华就成了许子东的技术指导,经常会提出一些建议,比方说衣服颜色不对,头发不好,说话太快,抢话了等等。许子东戏称,“上电视,也是一个逐步的‘堕落’过程。”不仅如此,他还把许多朋友“拉下水”。
刚开始,许子东的同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上电视,他们从私下里觉得,写文章把一个读书人的优点放大,上电视就把一个读书人的缺点放大。而且,学问再好的人,你常常说话,人家总会看出你的漏洞,你划不来,你哪能什么都懂?而且,人家至少会觉得你不务正业,你浪费了很多研究的时间。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这些朋友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子东看来,面对这么一个世界,如果只是读书,作为公民的责任都不尽,这个也说不过去。“另外一方面,事在人为,电视、报纸、出版都是媒体,媒体还是由你说话的人来决定,专栏可以很无聊,但是别忘了,《申报·自由谈》上,鲁迅写的也是专栏。
我们很难说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他会不会用博客。不能因为一两个人上了电视以后形象不好,读书人就全都却步。
时间久了以后,朋友们对于许子东上电视之举大为改观,许子东就拉他们“下水“,葛兆光、汪晖、陈平原等等都跟着许子东一起“堕落”,而李欧梵、白先勇等人,根本就没觉得上电视有何不妥。但是,许子东也知道,自己从读书人越界到电视传媒,甚至到网络,这个越界有得有失。
“读书人想借传媒说话,传媒也会改造你。我们想改变意识形态控制的框框,还有我更加看重主流民意的框框。我们做传媒的人不仅要警惕不要媚上,而且更要警惕不要媚世。”
有一次,“锵锵三人行”讲到黑龙江方正县为日本人开拓团竖了一个碑,网民们要砸这个碑,当地的人就把它拆了。许子东和梁文道、窦文涛讨论这个题目。讨论之前,三个人还稍微嘀咕了一下,估计这个事情说了要被人骂,但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想法。
这一集节目,我们侧重分析了这个开拓团跟日军的分别,他们不是纯粹的侵略者。在中国的网民一贯反日的主流民意之下,讲这番话肯定至少是不讨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出这个事情的复杂性。节目中,许子东说,过去中国人吃阶级斗争的苦太多了,所以现在不大用阶级这个眼光来看问题,只讲单纯的民族斗争,回到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说,以前毛泽东说,日军的侵略是帝国主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没想到,凤凰网摘出这句话来,一万多条回帖反驳,甚至有人说,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怎么样,就是因为没讲阶级斗争。在许子东眼里,“有些民意不一定是对的。”
南方日报特约记者 张弘
对话许子东
“文革”、文学与公众人物
说“文革”
上山下乡如果是自愿会让人毕生受用
记者:从你后来的人生来看,文革的经历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子东:那太多了,其实也不单是我,几乎中国整整几代人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一直到今天,很多人以为自己摆脱了文革,其实并没有。中国现在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世界上各个地方不同阶段都发生过,只有文革真的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独特的——文革是中国区别于世界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是非常深了。所以,这既是我的一段经历,同时也是我回头想研究的一个对象,很多人不愿意面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回避不了的。
记者:上山下乡要从事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折磨,这对你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什么变化?
许子东: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上山下乡不是一个折磨,其实全世界都有上山下乡,今天美国还有一种叫和平队,就是让大学生到很穷的非洲国家去生活两年,城市里的人到一个跟他以前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去生活,是非常有好处的。
以我的经历,以及我对现在世界的看法,我不会觉得,上山下乡是一个折磨,但是,坏就坏在它是全民迁徙运动,它是当时政治转移的策略,因为学生就业产生了问题,是不稳定因素,很难安置。上山下乡如果是自愿,到今天也还是一个伟大的事情,会让人毕生受用。
比如,我从“开头路”的故事,看到了农民的职业道德。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道德被家庭道德取消以后,职业道德始终没有受到重视,很多人都把现在职业道德的普遍丧失归结为社会转型。他们认为,几亿没有职业没有技能的农民工进城,来了以后不懂规矩,什么事情都不照规矩做,好像农民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农民在干农活的时候,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职业道德。修鞋的人,修钟表的人,刷油漆的人,都有一个自己行业的行规以及它的职业要求,他们都会从中得到职业尊严。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这些尊严都没有,以为谁赚钱多就有尊严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从根基上垮掉了。
做学术
研究张爱玲很“有缘”
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很注重对于作家的研究,你研究郁达夫,也是这样吧?
许子东:我那个时候做郁达夫,等于是一个作家论,不是一开始就写几个趋势,几大特点,什么潮流,什么现象,这种大题目我们还不会。作家论的研究基础,对我后来一直有用。你仔细读过一个作家的所有东西,然后你读他同时代的作家,然后又读“五四”的很多东西,这样做过以后,整个学科你就很熟悉了。
其实,当初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先做作家论的,陈平原做林语堂,钱理群做周作人,王晓明做沙汀、艾芜,陈思和做巴金,朱栋霖做曹禺……当时我们这一批做现代文学的人出来的时候,主要还是知人论世,作家论的方法很老土,很传统的,是19世纪的方法。
但是这个基础也不错。今天的很多学生做的都是很时髦的题目,但是完全没有作家论的一点基础,其实也不太好。
记者:你后来做张爱玲研究,又是一个什么契机?
许子东:契机是我1989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我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其间有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一半是讨论张爱玲。因为校区的停车费很贵,我老停在离学校比较远的一个免费停车的十字路口,过了几年后才发现,这居然是张爱玲最后住的地方,她去的邮局和复印店和我一样。
后来我问负责料理张爱玲后事、把骨灰撒入大海的南加州大学教授张错,他说你碰到她也不认识,你很可能已经碰到她了,她就穿着中国产的2.99美元的拖鞋,碰到她你也认不出来。我没想到她苦得要命,她租房子连两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
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写她的论文,同时讲上海小市民社会。此时,两岸三地的张爱玲热还没有完全开始,台湾已经有一点苗头。张爱玲在内地比较受注意,基本上是在她去世以后。后来,我经过陈子善的考证知道,我在上海原来住的房子居然是和她在同一条弄堂,都在南京西路,她是在那里看解放军进城的。我讲给人家听人家都不相信,说你在炒作你的房子。
上电视
知识分子的公共化是趋势
记者: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公共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吗?
许子东: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阻挡。第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所以,整个社会形态,包括政治制度都势必会慢慢有所改变。也许你从表面上看,制度层面一下看不出来,但是,社会形态的改变已经非常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表达渠道肯定会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地位变化很快,数量也变得很多,所以,知识分子对于政权的依赖性会逐渐减少,对于社会的依赖性会变大,这会促使知识分子更多地想到,你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社会成员。
这在经济上都会反映出来,你更多的不是依靠你的级别,而是依靠其他的事情。比如,那些靠版税的作家,他们说话,就和在作协里面的作家说话是不一样的,尽管他们说的话也不一定对,也可能不一定高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还是经济改变了这个世界。
记者:总体你对这个趋势是持肯定态度吗?
许子东:我也注意到很多令人不安、值得忧虑的现象,到目前为止,知识分子参与公众传媒的负面例子很多。尤其是对于现在在学院里读书的学子来说,他们会看到很多负面的例子,这也就使得很多非常好的学者不屑介入这一摊,他觉得,我怎么能跟谁谁一样呢?谁谁有几十万的粉丝,开玩笑,他是什么东西?他的文章是什么东西?很多很好的学者,不敢兼济天下,只求独善其身。
我写了一篇文章评梁文道,大意是说知识分子走向公众,不一定就是堕落——堕落这个词或许用重了,也不一定就不能再做知识分子。我觉得,在梁文道身上看出,还是一个正面的态度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