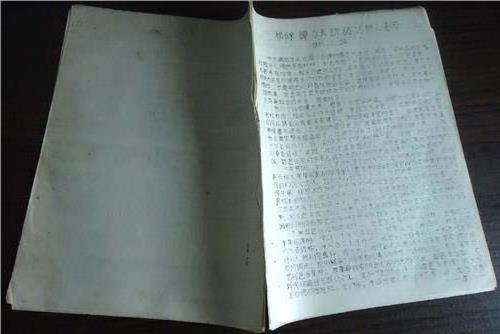胡宗南夫人照片 胡宗南夫人回忆录:我和他的爱 源于一张照片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 ,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1950年去台后,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等。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病逝。他与妻子叶霞翟相识于抗战前,却直到1947年才结婚,此时新郎已51岁、新娘也34岁。

一九三〇年,叶霞翟与胡宗南因一张照片结下情缘;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他们互定终身。随后她远赴美国游学,他奋战在抗日前线,但是二人没有忘记彼此的约定。十年之后,他们终成眷属。赴台后,相伴十二年,胡宗南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图:叶霞翟与胡宗南新婚时期的留影
本书由叶霞翟撰写,讲述与胡宗南相爱、相伴三十年的生活点滴,文字温婉质朴,情感真挚动人。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
文
叶霞翟
一切都是从一张照片开始。
那是一九三○年,我才十六岁。那年夏天,我考取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附设的高中——农高。和我一同考取的女同学一共只有三人,小姜、小朱、小江。我和小江是在入学考试时就认识了的。
因为投考的女同学很少,我们又恰好在同一试场,注册以后,我们要求编在同一寝室,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好朋友了。小江是宁波人,父母仍住在家乡,她的大哥是黄埔四期的,那时在杭州保安司令部做大队长,家在杭州清波门。
小江每个星期六都回家,有时也约我一同去。她的嫂嫂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子女众多,会做一手好菜。她对我也像待自己的妹妹一般,所以我很快就拿他们的家当自己的家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小江正在房里看小说,忽然听见一个粗重的男人声音在窗外问:“你们看什么书?”我抬头一看,窗外正站着一个又高又大的男人,三十光景的年龄,黄黄的长方脸,高鼻子厚嘴唇,两眼大而有神。
“看小说!”小江头都没抬地回答了一声,显然这位是他家的熟朋友。
我觉得小江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就对他笑了一下作为招呼,于是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正在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把书向他扬了一扬,他问我是不是喜欢看翻译小说,我告诉他什么小说都看。
事实上我正热衷于小说,尤其是许多俄国小说如《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等都看了好几遍。于是他告诉我,如果我们喜欢看小说他可以借给我们看,他那里什么都有。原来他是小江大哥的同期同学,那时在杭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一个报馆的总编辑家里,当然有很多书的。
小江听他说要借书给我们看,兴趣也来了,放下手里的书,开始和他聊天。
果然,这次以后他每次来江家都给我们带书来,慢慢地我也和他混熟了。他姓胡,我们叫他胡大哥,因为他的皮肤特别黑,我们又给他取了个绰号“老黑”。
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要看两三部小说,日子久了,他也记不清哪些书是我们看过的,哪些是没有看过的,有一次就提议最好我们自己去他家挑。那个周末,我们从笕桥进城,叫了一辆黄包车直接从车站到他家里。
身着便装的胡宗南将军
他有一个并不算大的书房,三面都是书架,只有靠右的一头有一空处,摆着一张大书桌,上面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我一走进去,还没有开始看书架上的书,就给那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是一个青年军官的照片,只见他身上穿着整齐的布军装,腿上打着绑腿,腰间束着皮带,姿势优美而英挺。那镶着军徽的军帽下是一张极为英俊的脸,浓黑的眉毛,炯炯发光的眼睛,鼻梁高而挺,嘴唇紧闭但线条柔和而带笑意,站在那里整个人是那么生动有神。
我对着它呆呆地看着,竟忘记去找书了。站在我后面的主人,看我对那照片看得那么出神,就笑着问我说:“你认得他吗?”
“不,不认得。”给他这一问,我猛然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满脸绯红,期期艾艾地竟有点答不上话来了。他倒不介意我的窘态,接下去说:“他是大大有名的胡师长,你们这些小姑娘不知道他,前方的军人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报上有他的名字吗?”
“怎么没有,你们看报只知道看副刊,看社会新闻,从不看国家大事,才不知道他呢!”
“你说他是师长,他看起来可很年轻呀!”
“自然年轻,他还只三十岁呢,他的升级不是一步一步升,是跳着升的。”
“你好像对他很清楚似的,他是你的好朋友吗?”
“自然是,不是好朋友他还会送我照片?你知道他是很少拿照片送人的。”他显然很兴奋,也很快慰,大约他对这位胡师长确很佩服,现在看我这小姑娘对他有兴趣,想趁此机会为他宣传一番。我呢,心里也确是对照片中人很是钦羡。我想,他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么年轻就做了师长,听说做师长要带好几千兵,够神气的。
记得我们家乡有一位孟明叔,是北伐军的团长,勇敢善战,北伐时屡建奇功。三年前,他带着太太回乡省亲,县长发动了全县士绅、地方团队和两所县小的学生,在北门十里路外列队相迎,说是接革命军。我们女子小学的校长,那位胖胖的张师母,还替孟明婶打着伞,陪着一同经过欢迎行列,她那圆圆的脸上,充分地表露出“我也有荣焉”的笑意。假如这位胡师长也到我们家乡去走一趟,县长不知道要忙成怎么个样儿啦。
于是,我又对胡大哥提出许多问题,问他这位胡师长是什么地方人,什么出身。他告诉我,胡师长是浙江人,和我们是大同乡,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才生,刚一毕业就参加作战,追随蒋总司令东征北伐经过了不少的战役。因为他作战勇敢而又很有智谋,每次作战都得胜利,人家称他“常胜将军”。
打到上海时,他已升为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他带着一团兵由闵行偷渡黄浦江,占领了莘庄、龙华和上海兵工厂,进而光复上海,把国旗插遍全市。
进入上海的那一天,他集合全团官长,随带武装卫士,乘坐敞篷汽车,直入法大马路、爱多亚路、跑马厅、南京路等热闹街道,绕行大上海一周,所经过的地方,人潮汹涌,民众夹道欢呼。
本来这些地方都是租界,我们自己的军队是不能进入的,他这一次以“不可一世”的声势,阵容堂堂、威风凛凛地长驱而入,租界巡捕看到这威武的情景也不敢出来阻扰了。这次不但替上海的百万居民出了一口气,更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从此国民革命军威震中外,全世界的人对我们都另眼看待了。
胡大哥愈说愈起劲,我愈听愈入神,那天回家以后,一直想着那张照片上的人,以及关于他的种种故事,心里想:假如他是我的哥哥多好。
记得那次孟明叔回乡后来看父亲,父亲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孟明,桑梓以有你这样的子弟为荣,我们老大将来大学毕业以后,我要把他送到你那里去磨练磨练,俾便能为国家尽点力。”
现在大哥快要大学毕业了,可是他是学经济的,哪里能举宝刀以卫社稷呢?真盼望有机会能见到这位胡师长,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个英勇样子。
从那次以后,我常常怂恿小江和我去胡大哥那里借书,顺便看看那张照片,有机会就请他再讲些胡师长的故事。同时也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国家大事,国内要闻。果然,“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不但常常会从报纸上发现胡师长的名字,也听到许多人的口中谈到他的种种传奇故事了。
他们说他不但会打仗,更会带兵,他对士兵就像对自己亲兄弟一般,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士兵穿什么他穿什么。据说当革命军北伐之初有“十不怕”的口号,就是“不怕死、不怕险、不怕饥、不怕穷、不怕远、不怕疲、不怕苦、不怕痛、不怕硬、不怕冻”,这位胡师长十项都做到了。
由于种种的传闻,我对他的印象愈来愈深,仰慕之心也愈来愈切,总希望有机会能见到他。可是,直到我高中毕业,都没有遇到这个机会。
毕业以后我去上海念大学,大学生的生活是自由活泼的,特别是像我这样比较喜欢课外活动的人,和男同学接触的机会更多,但是,谁也没有使我动心。人家说姻缘是前世注定的,也许月下老人的红线已经把我和他连在一起了。
在我念大三的那年春天,我和绮嫂去杭州探亲,一天早上,我去老师那里,他正在楼上处理要公,叫我在楼下客厅等一下。客厅外面是个大花园,那正是百花吐艳的时候,我就倚在窗边欣赏着园里的景色。
过了不久,听见后面响起了脚步声,以为是老师下来了,回头一看,进来的却是个陌生人。他穿着深灰色的哔叽中山装,中等身材,方脸宽额,浓眉大眼,鼻梁很直,嘴形很美,面色白里透红,下巴青青一片,显然是刚修过脸的。
当我和他的眼光一接触时,就像一道闪光射进我的心里,立刻感到脸红耳赤、心头乱跳,同时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什么地方看见过的,到底是谁却想不起来了。为了掩饰窘态,我只好又回过头去继续望向窗外。
他呢,既没有退出去也没有坐下,好像马上就绕着客厅里的那长方桌开始踱起方步来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当我等得有点不耐烦的时候,又有脚步声到客厅门口,我以为这一次一定是老师了,连忙转过身来。进来的却是王副官。王副官对那位客人笑笑,然后很恭敬地说:“军长,先生请你上楼去。”
“唔,好!”他口里应着,脚步已跨出客厅,只听见几步楼梯声就寂然了,我想他走楼梯一定不是一步步走上去而是越级跳上去的。他出去之后,我已无心再看风景,随便在门边一张沙发上坐下,感到心慌意乱地真想跑掉了。
随后,老师终于下来了,刚才那位客人也跟在他后面。他一进来就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然后指着那位已经站在他旁边的客人说:“这位是胡军长。”又看着客人指指我说:“这位是叶小姐。”
等大家坐下来后,老师问了我一些学校的情形以及我来杭州的事,又告诉我他中午就要去南京,因为那边打电报来有要紧的事要他当天赶去。最后他对我说:“这位胡军长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学问好得很,你可以多多地请教他。”然后又对胡军长说:“大哥,我还要上去理一下东西,你们谈谈吧。”说着,没等他作任何表示就匆匆跑出去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时我已经知道来客是谁了。原来,这几年他已从师长升到军长,他的样子有点像那张照片,又有点不像,时间相隔七八年,人的样子是会变的。
我觉得他的人比照片更有精神。七八年来我一直想着他,想认识他,如今,我们终于面对面了,我将对他说什么好呢?我能告诉他,他是我梦里的英雄吗?我能对他表示我私心的渴慕吗?
毕竟,我已不再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了呵。我脸红心跳,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幸亏他倒很能掌握情况,老师一走,他就马上移坐到离我较近的一张椅子上来,用温和而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叶小姐,听说你现在在上海念书,念几年级了?”
“三年级。”
“念哪一系?”
“政治经济系。”
“呵,小姐念政治,可了不起,将来一定是个女政治家。”
“哪里,哪里,念政治是最没出息的。”
于是他又问了我许多学校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容易谈,也最不会得罪人,慢慢地我的心平静下来,态度也自然了。等到二十分钟谈下来,我们已不再感到陌生。后来他说要等着送我老师去车站,问我要不要一道去,我心里是想说“不”的,口里却说“是”。
那时时间还早,他提议我们先去附近湖滨公园散散步,我心里想,刚刚认识怎么可以和他一同出去散步,正推辞间,郑先生来了。郑先生是认识我也认识胡军长的,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听见胡军长说出去散步的事,连忙对我说:“来,来,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因有郑先生同去,我也就不再推辞了。出得门来,三个人有说有笑地从第一公园一直走到民众教育馆。
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莺飞的时候,湖滨公园桃花盛开,香风阵阵,吹人欲醉。我走在他们两人中间,有些兴奋也有些迷乱,脚步有点飘飘荡荡的,像走在云里,当时忽然想到小江,很盼望能在路上忽然遇到她。她知道我对照片里的那位英雄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假如她看见我竟真的和他在一起,将是多么惊喜。
一小时之后,我们回到公馆陪老师一同去车站。车站里人潮汹涌,好像还有些部队上车,胡军长没有和我们同车,我想可能他还要送别的人。车开动了,我向老师的秘书何小姐挥手送别,老师是素来不喜欢这些婆婆妈妈式的动作的,一上车他就进入自己预订的房间,继续处理公事去了。
“叶小姐,我送你回去吧!”当我看着何小姐的手帕在远去的车窗消逝后,正转身要走时,忽听得后面有人对我这么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位将军竟又回来了。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不了,谢谢您,我自己回去。”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跟着我朝车站出口的方向跑。
我想,等到了车站门口再说吧。出得站来,前面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我想这车可能是他的,但又不敢断定,心里想在快到达车子时向他握手辞谢。哪知当我们走到离车子还有几步距离的时候,他却一个箭步跑到车旁把车门打开了。
我感到很是尴尬,口里叽叽咕咕地像是又说了一两句推辞的话,但他并不理会,只是笑嘻嘻地用他那空着的左手很自然地把我挽上了车。我想,这简直是软性的绑票嘛!天下竟有这种强要送客的事,虽这么想,心里却是很快乐。
到了家门口,已是吃中饭的时候,我想请他进去吃饭,又不好意思,毕竟我们认识还不到三小时,只好谢谢他就算了。他也没有什么表示,只说了一声“再见”就叫司机把车开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又有点失悔,觉得可能自己对他太冷淡了,得罪了他。
吃饭时,绮嫂问我这半天的情形我都懒得讲,只说去车站送了老师,匆匆吃了半碗饭就跑到房里关起房门,想安静一下,使头脑清静一点,把那紊乱的思绪理理清楚。谁知刚进到房里,外面的门铃就响了。女佣来报告,外面有客要见二小姐。
他已换穿一套西装,态度潇洒儒雅,实在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军人。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游湖或散步,我觉得有点累,不想出去,提议就在家里谈谈。他也乐于接受,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从杭州的天气谈到西湖的风景,再从西湖风景谈到有关西湖十景的各种典故。
原来他是老杭州,在杭高念过书的,对杭州情形非常熟悉。虽然我也在杭州念过三年书,还将杭州作为第二故乡,和他比,却像个陌生人了。他是那么健谈,说话的声音平和而有力,眼睛充满着感情,当你听他说话,看着他的表情,是不能不被吸引的。
坐到天快黑的时候,他看看表,说是有人请他吃晚饭,才愉快地辞去。
这几天情绪略为平静,回想起过去的一百天真像是做了一个悠长的噩梦,可偏又不是梦,如真的是梦倒好了,梦醒后一切仍是美好的,而我所面对的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啊!
一九六二年六月,数百位亲友伴同我和孩子送将军于阳明山上的纱帽山麓,墓庐依山面海而筑,他在那里可以看见海那边的家乡。送他那天傍晚,我伫立墓前,俯仰之间,但觉天地悠悠,沧海茫茫,三十年岁月,只是一梦。
记得当南兄那么骤不及防地离开人世时,我真是忽然从鸟语花香、绿草如茵的原野坠下了黑暗恐怖的万丈深渊。迷乱、绝望,极度的悲伤使我变呆了,脑子是那么乱哄哄的,对事物完全失掉理解力,情感也枯竭了,甚至连母爱的天性都隐没了,感到人世间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有时候,自己都在怀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日子过得昏昏沉沉,就像一架机器人似的对付着日常的生活。白天,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很多的朋友来看我,人像潮水似的涌进涌出,每个人来谈的都是同一个题目,南兄的死。
起初,只要一提到,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出来,真可以说是整日地以泪洗脸,后来连泪泉也像枯竭了,说到伤心处只感胸口发闷,喉咙哽塞,眼睛是干涩的。夜里亲戚朋友都走了,孩子们也睡了,剩下我一个人,静寂使我的思想开始活跃,于是就仔仔细细回想着南兄得病的经过,在医院里的种种情形,医生对我所说的话,越想越不相信他是真的死了。
只病了那么短的时间,不久以前还是生龙活虎似的,就是在病中也是头脑清楚,信心坚强的,在我的心中从来都没有一点点他会死去的暗影,就是去的当天晚上我们还是说笑着的呀,这教我怎么能够面对现实?怎么能够甘心?一百个疑问盘旋在我的脑中使我无法合眼。
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他确是不在我身边了,等到那最后的疑团也不存在时,我的心死了。俗语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死了的人确是可怜,我本来是一个有多种兴趣的人,爱花、爱树、爱音乐、爱看电影、爱读小说,也爱和朋友聊天,可是到了那时却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了。
在我书房的窗前有株扶桑,它那绿油油的叶子和挂满枝头的红花常常是我灵感的源泉,有时当我伏案写作时,想不出佳句就抬头向它看看,欣赏一会儿以后好句就从笔尖出来了。后来几番春雨后它的叶更绿了,花更红了,但我这赏花人却无心去欣赏了。
我那小小的院子里种有几株茉莉和杜鹃,也有好几盆兰花和菊花,过去,拔草、浇水都是我日常的工作。自从南兄死后,我再也无心去料理,任它花谢、叶枯,一条小径长满了荒草,我偶尔在那里走过,也懒得去看一眼。
我并不懂音乐,但喜欢听,平常在晚饭以后,总要叫孩子们放几张唱片听听的,这时候对它却一无好感,只要孩子们一打开收音机或放一下唱片,就觉得心里烦乱不堪,叫他们赶紧关掉。那些雄壮的交响乐章,那些婉转歌喉,对于一个寂寞凄凉的心,似乎都不能交流了。
书报本来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这时候我对它们也没有胃口了。有时,夜深人静,百无聊赖,我也会顺手拿过堆积在案头的报纸翻开来看看,但那些国际要闻、国家大事,对我都无关了,再大的标题在我的心目中只是几个大号的铅字。
至于书,我也很少摸了。在这期间也曾经接到过几位朋友自己写的作品,他们是希望我能够从那些书中得到安慰的,可是我拿到之后,翻开来看了一下,也许还不到三行,我的心就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有时候会在一页书上停留个半小时,而对书上的意思仍是一点不懂,最后只好翻两下就摆开一旁,真不知辜负了朋友们几许好意呢!
对物如此,对人又何尝不一样,多么奇怪啊,一个人伤心到极点时竟连被爱和爱人的能力都丧失了。亲人、好友,她们对我说了多少劝慰的话,流了多少同情和怜悯的眼泪,虽然那些语言和眼泪也曾使我的心灵微颤,但再真的感情好像都无法穿透这颗冰冷的心了。
他们在面前时我还是会哭、会诉,他们一走,我就觉得茫茫然了,在那么多天里,多少的友谊和爱心,都不能给我一点安慰。
最可悲的是我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爱了。
过去我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笑声是我快乐的源泉,他们的成绩是我最大的安慰,只要他们健康活泼,他们读书成绩好,我就心满意足,觉得这世界真可爱,做人真有意思,如果他们有点伤风咳嗽或其他的小毛病,我就坐立不安心乱如麻,惶惶不可终日。
我每日一早起来亲自为他们预备早点,亲自送他们上学,下午计算着时间等他们放学回家照顾他们吃晚饭,晚上督促他们做功课,安排他们睡觉,星期假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安排节目,为的是要空出时间带小孩出去玩。
南兄常常笑我,说我像个老母鸡带领一群小鸡,我自己也承认,我的爱护子女实在不亚于天性慈爱的动物,哪晓得南兄一死,我会变得那么厉害,竟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爱惜了呢!那时候我不但已无心照顾他们的功课和起居作息,对他们的一切也好像不再关心了。
可怜的孩子们,没有了爸爸,又几乎失掉了妈妈!当我最伤心的时候,就是他们亲亲热热地来到我身边,轻轻地叫着“妈妈”,我也只是对他们看看,点点头,心里却无亲切之感。我的悲哀和冷漠使得孩子们无所适从了。
大的两个只好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埋头在书本上,他们已不再去打球,不再去下棋,不再去找朋友们玩,也不再打开收音机听故事了。小的两个,尤其是最小的明明,素来是和我很亲近,老是挨在跟前的,这时候看我对他们那种不闻不问的样子,就不敢再到面前来。
许多亲戚朋友怜他们幼小,都自动来照顾他们,带他们出去,买东西给他们吃。这种生活上的突变,和太多的照料和关怀反使得他们不知怎么适应才好,在很短的时间内生活习惯都变了。他们已不再像过去那么文静听话,他们的脾气变得很坏,常常哭闹,还会打人骂人,有时当我听见他们在那里大声叫嚷或对人无礼时,也想去教训他们一番,但都提不起精神,只好让他们去了。
在这段时间内唯一系住我心,使我继续生存下去的原因就是南兄的灵柩还停在殡仪馆,我想:“他的灵魂虽已上天,他的身体还在那里面,只要我能亲近他一天,我就要亲近一天。”
因此,每天一天亮我就急着想往殡仪馆去。我无意梳妆也无心吃饭,只等孩子们一去上学就马上跟着出门,有时因为客人或其他的事使我不能趁早前去,我就心急如焚,连人家问我的话也会答非所问,他们以为我伤心过度精神恍惚,反而坐下多方劝慰,哪知他们的好意反给我心更大的煎熬!
到了灵堂我的心就安了,我确实地觉得他的存在,如没有别人在旁,我会用我的头依靠着棺材的一边,流着泪向他细细倾诉。
我对他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相思,好像我们又回到恋爱时期了,在那里时间是永远不够长的,往往已晌午我并无意离去,总要别人再三催促才勉强举步,每次临走时我都抚棺和他说:“明天见,亲爱的!”虽然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想象着他一定会微笑点头的!
后来他的墓快修好了。我开始着急不安,我知道连这点亲近的机会也将没有了。我心里真不愿意把他送得再远一点。可是大家都说落土为安,还是早点安葬的好,我虽是一千个不愿意但又怕人家说我不通情理,说我自私,说我会使他的灵魂感到不安。
想着他活着的时候,每次他出远门时我都是心里舍不得,脸上却只好装着若无其事般送他走。现在,这是最后一次的行程了,我这做妻子的,是不是也应该勇敢一点呢!天啊,做一个勇敢的妻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终于在六月的一个早晨,我披上黑纱送他上山,送他到最后的安息所在了,当我眼看着砌墓的工人把最后的一块砖头封住墓门时,真是巴不得自己也能从那夹缝里钻进去和他一同封在里面呢!
在他安葬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地方好去了,茫茫然无处着落,只好把自己关在客厅里对着他的照片发呆。一会儿客厅的门开了,老大轻轻地走到我身边,亲热地叫了一声“妈”,接着其余三个也进来了。
德德拉着我的手问:“妈,您今天不出去了吧?”美美靠着我的肩膀说:“妈,我真想你呢!”站在后面的小明,一下子投入我的怀里,用她的小臂膀围着我的头颈说:“妈我爱你,我真爱你啊!”
这一连串的稚气而甜美的声音终于打动我这空虚的心了,我抬头看看他们,才发觉他们都变样了,他们的头发是那么长,脸色那么青,一个个又瘦又黄,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像泉水般的涌出来了,我张开两臂把他们四人都搂在一起,语音颤抖地对他们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宝贝,妈妈爱你们,妈妈也真的爱你们啊!”
于是孩子们也哭了,母子五人哭作一团,可怜自从爸爸死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想到孩子,为了孩子而哭呢。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心也随着母爱的复活而复活了。
一道闪光照亮了我的心灵,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必须振作起来,爱他们照顾他们,你丈夫的生命并没有死,他的生命就寄存在这四个幼苗身上呀!”
当我再抬头起来看着南兄的照片时,我看见他在向我微笑,像是在对我说:“霞妹,我真高兴你终于领悟了,此后你要坚强起来,好好教养这四个孩子,要知道只要他们将来有出息,你我的生命也会继续地放着光辉的。”
现在又一个多月过下来了,这些日子里我在试图振作,愿上帝给我力量,使我能负担得起未来的这副重担。
一九三九年因抗日战争延误婚期,我远渡重洋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
叶霞翟(1914~1981),1947年春与胡宗南结婚,台湾著名教育家、散文家。上海光华大学毕业,获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学士学位,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光华大学、金陵大学。1949年后任台湾教育部门特约编纂,台北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退休后专任文化大学家政研究所所长。著有《家政概论》《家政学》,论文集《婚姻与家庭》《主妇与青年》,散文集《军人之子》《山上山下》等。
摘录自《天地悠悠:胡宗南夫人回忆录》,叶霞翟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以上图文感谢凤凰读书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