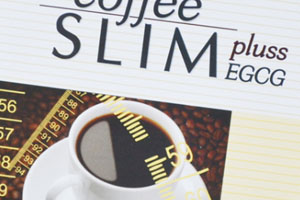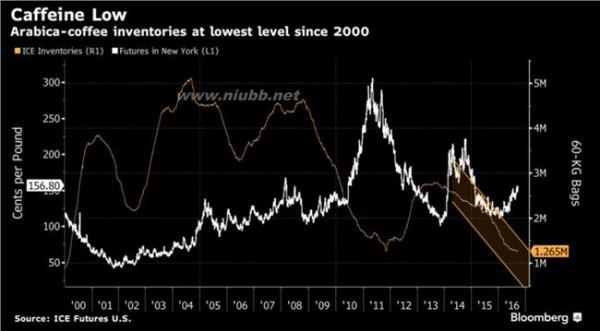罗伯斯塔咖啡豆 罗伯斯庇尔悖论:我死了 你们才能好好活着
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按照之前在他支持下颁布的法律,作为反革命,他无权为自己辩护。
不需要确凿的证据,甚至不需要经过正常审判,法官仅用三十分钟就决定了他和其他21名被告的命运:死刑,当天执行。

押赴刑场的路上,他被绑在囚车栏杆上示众,士兵用剑背支起他已被手枪打碎的下颚羞辱着他,两边是群众潮水般的怒吼和诅咒,特别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下地狱吧,你们这群恶棍!记住,在地狱里你们也别想摆脱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诅咒!'

罗伯斯庇尔充耳不闻,保持着冷峻和威严,目光凝视远方。用来包扎下颚的白色绷带浸透了一层又一层鲜血,已经完全发黑。
行刑者是刽子手桑松,一年半前,是他处死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四个月前,又是他处死了丹东。

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不知罗伯斯庇尔是否会想起丹东在刑场上最后的诅咒和预言:“下一个就是你”。
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桑松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像一头绝望的野兽般歇斯底里地咆哮。刀刃落下,革命广场陷入盛大的狂欢,人们久久不愿散去,仿佛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夜,罗伯斯庇尔的房东太太被狂欢的暴徒绞死。
几天前,他曾希望留下遗言,但没有人肯给他纸笔,从未有一个死刑犯遭到他这样屈辱的待遇。他沉默的死去。有人给他写了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就得死!
曾经的人道主义者罗伯斯庇尔
这位声称“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坚定革命者,早年却是死刑的激烈反对者。
罗伯斯庇尔早年担任律师和法官时,在一次死刑判决中,他的同事回忆:“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他的妹妹夏洛特写到:“哥哥那天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一连两天什么也不吃。”一场法庭辩护中他声称:“一见到如此多的淌着无辜者鲜血的断头台,我就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内心呼喊:永远摈弃那种仅仅根据假设就判罪的致人于死地的倾向!”
1791年在制宪议会的演讲中,他要求废除死刑,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死刑是以整个社会的力量对付一个人,是一种谋杀行为。死刑完全是专制暴君的政治手段,是滥用威力来威吓人民,“问题不是在惩戒罪犯,而是为君主报仇。”他热爱古代民主国家,认为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代,人民不会受到国家的威胁,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才会泛滥着死刑。
这时的罗伯斯庇尔无疑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深信断头台是专制国家的产物,而专制政体的工具就是恐怖,必将随着人民的觉醒和正义时代的到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被愤怒的群众处死。一周后,财政部长富隆因为宣称穷人饿了可以去吃草而被群众吊死在路灯上。此时,曾经对国家暴力十分警惕和反感的罗伯斯庇尔,已经陷于革命的狂喜中,他在书信中评价道:“基于人民的审判,富隆先生昨天被吊死了。
”他又评价巴士底狱起义:“流了少量的血,获得了公众的自由。无疑,曾砍了几颗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正是通过这次暴动,国民才获得了自由。”
但流血仅仅是刚开始。在巴黎乃至法国,群众开始发起一场场的“革命行动”,不经审判就随意处决心目中的敌人。最终,随着对外战争的不利,九月大屠杀开始了。群众和民兵冲进监狱,一千多名犯人被屠杀,其中大多为普通刑事犯。
很难推测罗伯斯庇尔此时的想法,也许,人道思想的悲悯和人民正义的信仰正在天人交战,尽管他对此保持沉默,但他领导的巴黎公社对此事采取了默认和纵容。随后,他遭到吉伦特派指控:挑起九月事件,以屠杀和恐怖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
一个星期后,罗伯斯庇尔上台申辩,宣称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向同事和政敌尖锐指出一个冷酷的事实:如果现在人民的举动是非法的,你们之前所做的算什么呢?摧毁巴士底狱、废黜国王、处死贵族,哪些不是非法的?从革命开始到现在的所有革命事件,有几个不是非法的?难道自由本身也是非法的么?
于是,杀戮似乎是错误的,但已是革命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共犯,自然也无法指控。在对人民正义的绝对崇拜中,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没人可以后退,曾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就用尽全身力气的罗伯斯庇尔,已和众多革命者一样,被时代洪流吞没,变得面目全非。
处死路易十六是大革命的转折点,被后世不少评论者视为“理想国覆灭的开始”,随着“铁柜事件”发生,国王被认为是叛国者。对于如何处理国王,国民公会陷入了争论,按照1791宪法,国王是不能审判的,于是事件的性质超出国王本身,演变成要宪法还是要革命的问题。最终,国民公会认为1791宪法已经失效,却又未颁布新的宪法,于是革命胜利了,限政的外衣被抛掉了。
吉伦特派则认为,国王也是公民,应按照公民方式来审判,由于其身份特殊,可交由人民来表决。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代表的山岳派坚决反对,认为鉴于局势紧迫,国王必须立即处死,人民没有时间来表决。国王并非公民,而是革命的敌人和反动派,他需要的不是审判,甚至是否有罪也并不重要,他是君主制的象征,必须接受革命的惩罚。
最终,1793年1月21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在此事件后,雅各宾派获得了实际权力,不再有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以决定谁是公民,谁是国家的敌人。公民的身份和人权不再是天赋的,而是必须融入不可质疑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得到认可。国王之死将法国人分成两类,一边是共和国公民,另一边是共和国敌人,敌人一旦被确认,需要的不是证明他们有罪和按法律如何判决,而是直接用暴力消灭。
如果说从巴士底狱到九月事件的一系列滥杀,还是由群众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完成的,革命者掌握的共和国或许出于对民间暴力的无力,或许出于对人民绝对正义的崇拜,而默许了这一事实,那么现在,国家则抛弃法律,从群众手中接过屠刀,一个可怖的巨兽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大规模的恐怖专制开始了。在罗伯斯庇尔“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宣言下,巴黎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人被处决。
一直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丹东,在血腥面前退缩和悔悟了,他开始主张宽容,要求“爱惜人类的血”。最终,他所代表的“温和派”被送上断头台---比罗伯斯庇尔早了四个月。
罗伯斯庇尔被认为是史上最残酷政体的罪魁祸首,正如菲佛尔在《法国革命史》所说:“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对所经历的恐怖永远难以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后来的革命者对他的评价则两极分化,有的批评,有的崇拜,像一面镜子般体现了其意识形态。
在恐怖政治中,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国轰然覆灭,无论是宪法法律、人道主义和程序正义,都在“人民意志”面前轰然倒塌,革命的结局是产生了一个不受法律制约,在激进主义和狂热主义中为了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而陷入疯狂的国家意志。罗伯斯庇尔的死亡并未改变一过程,此后当政的仍然是恐怖专制者,随后,法国开始走向“五百万人的坟墓”,在拿破仑掀起的欧洲战争中,数十倍的法国人因此丧生。
这位大革命中的暴君,只是革命的一个缩影,在那场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法国社会必须让一个人为所有的恐怖政策负责。而在那场群体性的疯狂中,罗伯斯庇尔的辩护言犹在耳,有多少人能正视自己的黑暗内心,扪心自问有谁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