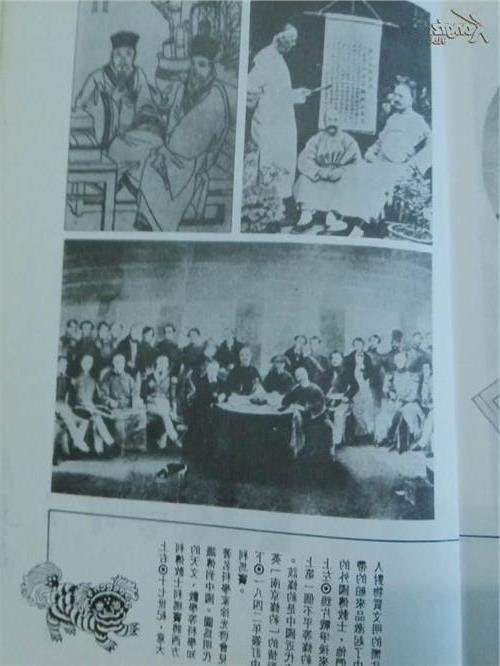蒋梦麟西南联大 赶潮的人:蒋梦麟 在西南联大时期创造的奇迹
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坚决主张沿袭长沙临时大学时的体制,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

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原定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上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一人,并一直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负责联大日常事务,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

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据比较接近他们的郑天挺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
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联大三校各有相沿已久的特殊传统和做法,因此三校能否在整个抗战期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实在是对三校同人尤其是三校领导的重大考验。在整个联大时期,三校之间有联合的部分,也有不联合的部分,在联大之外,各校还保留着自己的某些行政机构和教学组织系统,各自设有办事处,负责处理纯属各校自己的事务。

北大办事处内设有校长办公室,秘书为章廷谦;教务处,教务长为樊际昌;秘书处,秘书长为郑天挺。另外还设有文牍组、会计组、事务组、出版组及图书馆等。
北大教职员参加联大工作,除由联大发给聘书外,北大还发给聘书。北大并建设有自己的宿舍区。北大学生战时入联大就读的,仍然保留北大学籍,并在毕业时领取北京大学发给的毕业证书。自1938年起,至1946年止,北大毕业生总计三百七十二人。
由于战争而停止活动的北大研究院,于1939年夏在昆明恢复活动,开始招收研究生。北大研究院属于北大系统内,不受联大领导,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属北大学籍。到抗战结束,北大研究院共设有三个研究所十二个学部。
梅贻琦说过,西南联大好比一个戏班子,总要有一个班底,这个班底就是清华。因此在联大校级办事机关的职员,便以清华人为主,北大、南开只是派出一些名角共同演出。这种演出基本上说来很成功,配合也很协调。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出去的几个大学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他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①
反观西南联大,由于是独立学校的联合体,又由于联大基本班底是清华人,因而蒋梦麟所领导的北大同人中对于联大课程安排,经费分配,以及学生指导等不免常有不同意见,有时要请校长出来主持并力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北京大学以不动一草一木为原则,未运出任何设备,只有物理系将一个得到不易的凹面光栅及光谱仪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极少数部件带出。
北京大学自己只有很少经费,加上维持一个驻昆明的北大办事处,没有力量维持多项研究工作,②因此三校之间在经费使用上便不免有时要闹些不愉快。但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蒋梦麟总是耐心劝大家容忍退让。
其实,早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时,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是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
南开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恪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基金。蒋梦麟和叶公超一些教授,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有事就出去游览山水。
晚上聊天的时候,关于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的消息,究竟他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只说他们的电报转给张校长了。
梅校长也迟迟没有确实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到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大家就拆伙好了。蒋梦麟的反应是非常能够表现他的性格的,在饭桌子上他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
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
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后来,张伯苓、梅贻琦终于都到了。亲历其事的叶公超多年之后依然感慨地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为政府继续培养人才,蒋梦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经历过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普遍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始终如一的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他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和夭折的东南联大以及一时联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联大相比较,西南联大九年的历史是值得珍视的。①
西南联大的真正困难是由于时局动荡,物价暴涨,经费短缺。当时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时就规定,联合大学的经费由三校分摊。各校按统一规定的比例提成交临大。三校原来的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由于是国立大学,其经费完全依靠国民政府的支持;南开为私立大学,抗战爆发后经费来源枯竭,于是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的经费在抗战开始时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支付,一般说来经费来源最为可靠。
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来源也告中断。
从这时起,西南联大的全部经费都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然而从1937年9月开始,国民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教育事业经费,将原核定的各国立学校的经费改按七成拨付。长沙临大时期,北大以所领七成经费的一半上交给临大,作为教职员薪金和维持教学的费用。
余下的一半作为本校校产保管和师生特殊救济之用。自1938年4月以后即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改按七成中的四成交给联大,所余三成经费,又被教育部以所谓“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为由规定全部上缴。
从此以后,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个学校就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费。三校各自办事处的开支,则由教育部在上缴的三成经费内酌情发给,实际上难以维持所需。西南联大每年经费的预算数为法币一百二十万元左右,仅及抗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额。
然而由于抗战时期的实际困难,这个数字的经费国民政府也很难保证及时付给,总是一拖再拖。至于联大校舍建筑和图书设备所需临时费用,国民政府更是无法顾及。
直到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才拨给联大设备费三万八千美元,其中三万四百美元作为图书购置和仪器设备费,其余作为购置行政设备和装运保险等费。在三校合并,人员倍增而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联大在经费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西南联大的困难首先体现在教师的生活上。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
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
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像刘文典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他在联大时期虽然心情可能比较郁闷,但物质生活实在说来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因为他的古文作得好,很受当地富贵人家的欢迎。
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冯友兰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
当基本的生活难以为继时,那真是斯文扫地,教授也就只能重回世俗,为温饱而奋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和知识界有一部分人出于不同的考虑,设想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向大后方这些宝贵的知识分子提供援助。当时情形似乎正如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费正清所描述的那样:“我个人的奋斗目标逐渐在心中明朗起来帮助和保护那些留美归来的中国教授、学者,其中有些是在北京的老朋友。
这就是我对当时形势所作出的反应。在当时的中国,抗击日本的事业实际上已被中美两国的军方所垄断。
我采取的对策是,把注意力转向它处。当时,被动员起来的教授很少,甚至学生们也被看作是国家的稀有资源,必须保护他们健康成长,以备将来之需,而不要在战场上消耗掉。一些被派驻在战时中国的美国文职官员对中国前程感到幻灭,于是以救济妇女、儿童或者搜集明代青花瓷器来解除心头的郁闷。从我个人来看,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是我认为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拯救残存的自由教育。”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援华会负责人在宣布这项消息时竟然说这些援助款项将用于补助中国高等学校里教授们的生活。于是将这条消息在报上一经披露,立即在中国引起极其强烈反响,有些人反对靠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中国国立大学教授们的生活。
蒋介石听说后也勃然大怒,并立即将此项援助予以取消。据费正清记述,大约在1943年1月的一天上午,蒋梦麟因事来到费正清在重庆的寓所,他和费正清谈到了美国联合援华会的破产计划。蒋梦麟的外貌很像梅贻琦颀长身材,风度翩翩,是个富有思想理智的人。
他与梅贻琦均是昆明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并以他们苦行僧的形象闻名。蒋梦麟此时早已不在北大工作,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他的太太想找个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经济上梅贻琦或许还更糟。梅夫人好不容易化名找了一个工作,但终究被人认了出来,于是只好放弃不干。
蒋梦麟向联大教职员通报了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大学教授计划被否决时,引起了大学教职员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大学教授生活如此艰难,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既然国家可以接受租借法案,那么教授们迫于生计,接受美国援助何尝不可?蒋梦麟费了很大口舌劝阻教职员不要发表抗议文字。
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能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保存骨干力量,让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战争中丧失殆尽,将会使原来已经不振的高等教育更为混乱。蒋梦麟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当时情况看,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①
中国政府不愿意使用美国人的捐款解决中国教授的生活,而自己又拿不出钱来改善甚至可以说保证教授们的基本物质需求,于是教授们依然故我地在饥饿线上挣扎。到了1943年下半年,西南联大教授每月薪俸已由战前三百多元降至实值仅合战前八元三角,仅能维持全家半月的最低生活。
中国教授生活苦不堪言,但西南联大所获得的成绩却是举世公认。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不仅克服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称说的价值。在科学研究方面,蒋梦麟于1938年冬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时,特约各系教授撰文编印纪念论文集,其中所收的一些文章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如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所撰有关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的专论,就是一篇具有相当价值和独创性的论文。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联大的成绩也极为可观。培养出许多后来在学术界具有极大声誉和成就,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学生。据他们当时的指导老师吴大猷教授说,当年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以三菱柱放置木架上作分光仪,继续进行研究。
但在他担任讲授“古典力学”课程时,仍于学期结束时拟出十余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自行选择进行研究,而杨振宁即选择了其中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的题目。到了1957年冬,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金时,他们不约而同致函吴大猷,说明他们多年以来的研究工作,均可追溯于吴大猷西南联大时的启示和那个论文题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