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仲山水画 王学仲|论文人画(附山水画作品欣赏)
积淀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在文学领域最集中地反映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在绘画领域则最集中地反映于文人画中。文人画早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诗文、书法等多种文化形态所滋育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可称得上是东方的综合交响乐章。

就其所达到的艺术深度而言,它是诸种中国文化所垒成的高塔,极其丰厚艰深,因而不易为一般观赏者所理解,以至在近代遭到了被抑制、被冷落的命运。不过,由于文人因蕴蓄着文人的“土气”、“雅谑”、“超形”、“机趣”等,可以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高难度和深沉度的代表。所以虽不能把文人画说成是中国民族绘画之神魂,毕竟可以视之为中国最独特的和富有魅力的民族绘画。

文人画的界定
文人画出现于唐代,而界定于明代。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的先灵就已开始浮游了。庄子就曾认为有画士度的人是解衣磐礴的真正画者。晋代曾被称为“才绝、画绝、痴绝”的顾恺之,应该说是真正的文人画画家之始祖。

他有极高的文才,长于传神人物画的创作,并具有文人画画家所特有的那种雅谑痴颠的气质。文人画的标志即在于有一种超越凡俗,遗世独立的精神;其画家则往往被人目之为“痴”。从历史看,对文人画的界定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代张彦远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他把文人画限制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之间。到了北宋的苏轼和明代《唐六明画谱》又提出了“士夫画”一词.以区别于民间画工和画院供奉待诏等的职业绘画家,而成为文人画的别称.
元代的钱选首失提出“士气”说,在其影响下而后又出现了董其昌的“文人画”说。董其昌正式提出“文人画”这个概念见于《画禅室随笔·画诀》中的一句话:“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即王维)始。
”另一位明代评论家顾凝远在《画引》中则说:“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深致也。”至于钱选所提倡的“士气”究竟是什么,赵孟頫曾就此向钱选提问,得到的回答是:“隶体耳”。
这里又牵涉到绘画与书法的关系。生活于元代的赵孟頫本人即曾谈到“石如飞白木如籀”,强调文人画中的书法趣味。董其昌则进一步提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清代石涛的“古人以八法合六法”,“画法关通书法津”,则是更进一步地把文人画和书法联结在一根纽带上去了。
最晚论述文人画的文章是民国初年的陈衡恪,在他所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才界定了文人画的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在这四大要素中,重点是“人品”与“学问”,而在这两个重点中,作为文人画的标志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学问”。
如果没有学问,也就必然失去文人画的特色。文人画讲求超形的意趣,宋代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元代画家倪云林所追求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近代陈衡恪所谈的“草草数笔而摄其全神”,就都反映了这方面的观点。
为《中国文人画之研究》 写序的姚茫父则认为:“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
”又较重点地强调了诗的性灵和情韵。可见文人画与一般绘画的不同点,即在于它不只是需要绘画技巧这一个方面的才能,而且需要动用文人画家在古典文学、诗词、题跋、书法等许多方面的学问、才智和技能,需要集合文人与画家、书家的全部智能于一纸,从而创作出超形传神、意趣盎然的画幅。
在论述文人画的历代文献中,常常忽视了雅谑和机趣这一带有东方意味的美学特色。这一特色来自魏晋六朝时代盛行的清虚谈玄的风气。晋代顾恺之的雅谑即来源于他的“痴绝”。关于他“痴绝”的故事很多,如他认为他失去的画是“登仙”而去。
在晋代还有个坦腹东床的王羲之,在宋代则有拜石的米颠、号称梁疯子的梁楷,在元代则有山水画家黄大痴、具有洁癖的“倪迂”“懒瓒”(倪瓒),在明代则有患了疯颠病的徐文长等人。他们都带有某种貌似痴颠的性格,甚至有的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自嘲式的谑称。
他们的这种性格特色,体现在绘画实践中,就形成了一种亦庄亦谐,自然清简的风格。《富春山居》 的简约和夸张,《 泼墨仙人》 的恬淡和机趣,就是这种文人画风格的典型体现。难道这些文人画的作者是真正的痴者吗?笔者认为,与其说他们性格痴颠,倒不如说他所具有一种印记着时代色彩的独特的艺术家气质,文人画的雅谑和机趣的特点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状态的投影。
中国文人画不以直接说教的方法进行创作,而是以一种变形、夸张、雅谑的笔调,调侃的意趣,直抒通脱之气,使某些哲理禅眼从深层透入内涵,从而具有一种异于流俗的深沉含蓄的特点。这种风致格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因而为中国艺术所独有。
中国文人画在现代作为一门传统艺术,也曾与其他许多姊妹艺术一样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和不科学的评价,有的甚至把这种艺术看成是反现实主义的,或根本否认文人画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对于那些对文人画的误解都应该加以廓清,从而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给文人画以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文人画的哲理和体格
文人画的美在历经千年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堂庑宏大的体格,在其体格中流贯着道、儒互补的哲学思考,从而基本完成了东方美学血型与审美形态的构架。宋代的文人画画家苏东坡即提出过这样的哲理意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而“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并主张“云无定形,而有定理”。
这类哲理思考与宋代理学思想的活跃以及尚意画风的形成不无关系,同时也是对于唐和五代的重彩勾勒等典丽形式所蕴含的审美情趣的逆反,它促使水墨渲淡、野逸中和的审美意识萌起。
唐代的美术领域深受佛教影响,倾心佛教经义、自号摩诘的王维,即已本着禅宗的明心见性的精神,在绘画中创造了水墨渲淡的一体。宋代的苏东坡便奉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并提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论点。
他所提出的这一画中有诗的标准十分重要,这就规定了文人画的综合性,形成诗、书、画一体的格局。人们逐渐抛弃了追踪形似、模拟自然的画匠习气,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儒、道、佛等中国古代哲理的意蕴。
因之,民国时代的陈衡恪才十分慨叹地写道:“若以画家之画与文人之画执涂之人使观之,或无所择别,或反以为文人画不若画家之画也!”可见文人画的由于其内涵之深奥而较难理解。
文人画画家顾恺之、宗炳、王微等人,由于生活于六朝佛儒交替之世,因而多有超世绝俗之思想,为发挥其自由的文人情致,则往往在绘画中表现出寄情于高旷、荒率之境的描绘,以及意出尘表的构想。唐代的王维则以“谈玄终日以为乐”的禅宗情怀去构思作画。这就为后世董其昌的以禅论画与分宗给予了启示。当然,董其昌把南宗奉为绝对纯粹的文人画并不尽合理,而文人画以禅悦之观念融入绘画,则是客观的事实。
在文人画中,还体现着道法自然与超脱玩世等观念。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文人画虽法自然,却不机械地搬移自然,乃是以道家的“内我而外物”的自然观去观察自然,即以人的精神情怀作为内在的主宰,借助外物而加以运用,使之彻幽察微,从而形成文人画的精神境界。
既然文人画以佛家的明心见性和道家的内我外物为自己哲学上的旨归,它就必然地“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元·黄公望《论山水树石》)了。
文人画看似雅拙而失去真实,而实为排除甜俗而内含哲理。以至“以文人之画而使文人观之,尚有所阂”。可见,以前有些观赏者对于文人画缺乏深透理解,以及现代对于文人画急于做出非现实主义或封建时代畸形艺术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在文人画画家的眼中是哲理高于形质之美的。所谓形质之美是指艺术的造型。在西方绘画中,强调物状的准确度及材料感的真实度,而我国的文人画却如以禅宗论画者董其昌之所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又如庄子之所说“目击而道存”。
这种神之离、道之存,主要就是追求画家的哲理与禅机,就是以哲理主宰形质。文人画的理趣,虽非一般画手所能理解,也为一般观赏者带来很大的阻隔,但不能因此而作为文人画的一种过失。文人画看似七巧宝塔,七拼八凑,有似菜品中的一道拼盘。
譬如元代四家之山水,离真实之形渐远;石涛之绘画,长题大跋,洋洋洒洒而布成画局,这些就都是文人画独特体格的表现。文人画把诗的可读性、书法的抽象性和绘画的具象性统一于东方的艺术美和民族的接受美学。
文人画的体格与中国戏曲以综合诗文、音乐、舞蹈等多种因素而构成,及其以虚拟手法而追求神似的特点,是十分相似的。它们都是在东方审美理想和传统民族心态的条件下而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形式,都是我国古代一定的哲理观念的产物。
如果说西方的写实绘画主要是追求造型的真实性,最多只是在画面上签上一个作者的名字的话,那么中国文人画就是以综合的体格,隐喻的形式和损益过的尺度,而使观者在产生若即又离之感的同时领略到某种深邃的理趣。
不能说文人画所提供的境界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它是一个文人雅化过的,渗透着一定理趣的境界,体现了中国文人画家所追求所向往的恬静之境,归根结蒂它依然是现实世界的折光式的反映。在文人画中,通过对于如梦如诗的仙境般的画面描绘,折射出在长期封建时代的文人画家的心理特质,他们似乎己十分厌倦扰攘的战患和利禄,转而追求一种近乎虚幻的美好的理想世界。
对于这种独特心态的反映,当然不宜采取过于求真的形式,而只能假以曲度的境面,雅谑的笔调,以及诸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哲理高于形质的特殊的艺术形态。
中国传统美学的迭次审美方式的体现
若问哪一种艺术最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美学特色?那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书法与文人画。书法在外国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书法的审美具有着迭次性,它把本来性质不同的文字与书法意象化合在一起。鲁迅称书法的特殊现象为:“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从书法的审美程序来看,审美的第一直觉是线条所组成的视觉形象,其次是文字的读音所构成的听觉感受,再次则是对于书法通体之意象美的领略。
文人画的审美形式也具有这样的迭次性,不过较之书法表现得更为复杂些。一种情况是,诗、书、画直现于画面,画意是直觉的享受,题字是内容的明示,书法美是迭次欣赏的深入;另一种情况则是,画中没有诗的形式,其“士气”与书法深藏于绘画的底里,把美术的具象书法化,诗的韵律与可诵性又在底里的底里,是深层的内核,画面上没有诗句可资诵读,而整幅画的画意和美感,则在画的形象中以含蓄的形式迭次地显现。
由此可见,文人画是具有可读、可视、可以体味等综合功能的画种。
因而,每个文人画画家必须首先是个诗人,但不必每幅文人画作都有题诗;文人画的创作虽极其强调必须具备相当的书法功力,文人画家也必须同时是一位书法家,但在文人画作中,却不一定都有具体的书法存在。
文人画称“写”而不称“画”,即是因为画是书家“写”出来的有表意功能的图像,题诗则是可供咏叹的音乐,它们共同组成了综合性的欣赏结构。任何一种欣赏心理与欣赏习惯的形成,都与两种因素密不可分,一是历史的文化因素,一是民族的心理因素。
中国人一般不大喜欢长达数万言的叙事史诗,而喜有哲理与情致的短歌。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即反映了这种状况。这并非是由于中国诗人的低能,而是出于民族的欣赏心理,即习惯于在含蓄中运用汉文的蕴藉,以浓缩的体格抒情叙事。
民族心态的又一个特点,是喜欢多面性、综合性的欣赏。如果忽视了中国艺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审美心态的制约下所形成的审美特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让中国艺术接受西方美学的种种法则的审查,一一对号入座后请君入瓮,则不仅中国的书法、京剧、文人画等等都未见得能符合标准而称得上是艺术,而且连中国传统的美学体系及其应用也都得付之东流了。
总之,文人画在审美上的迭次性,正是文人画作为诗、书、画共同构成的综合艺术所带有的审美特色。这种特色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因而不但不应随意加以否定,而且应很好地研究和发扬。
文人画家的性格
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理是有其病态美的,其性格中总有着一定的痴、怪、迂、狂等成分。中国文人画正是赖以存在和生长,使之在历史的长河上终于没有悄然而逝。我们奇怪地发现,这种性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竟然得到了欣赏者的肯定和崇拜。
如上文所述及的顾恺之为画痴,米芾为米颠,倪云林号称迂,还有集体的扬州八怪等等,不胜枚举。他们都是能诗能文的文人画家,他们虽处于不同历史时代,而在性格上都具有一致性,即都有某种痴怪的性格特点,对于他们的奇行怪癖,人们不仅不引为非议,而且传为佳话。这种现象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西洋美术重技术,并重个性,而与哲理和人的意念去之甚远,与中国文人画的重学问、重人品亦大逆其旨。从某些方面看,中国文人画是重道而轻器,西洋画是重器而轻道的。因之,文人画把人品和学问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虽是一幅草草不拘的文人作品,亦能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囊括着道德学问的经纶。唯其这样的画才可以显示出中国文人画所跻攀之高度。
黄山谷认为,“惟俗不可医”。清代文人画家则提倡从黄山谷以来的脱俗之议。石涛在《画语录》中专列“远尘”、“脱俗”两题,他以为“劳心于刻划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郑板桥更对人生提出“难得糊涂”的意识。其他文人画家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或疏狂懒散,或迂狂痴怪的性格。
而这些行为与观念难为人们所理解的画痴们,却创造了精美不朽的传世之作。痴与梦常常是互相联系、相伴而生发的。痴怪脱俗的性格,使文人画家的心态似乎处于梦幻迷离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它体现了艺术家的一种炽热狂烈的追求。也只有有了这种境界,才使之在创作中流露出一派赤子之心。最坦诚的自我,使画家自身的人品和学问在画幅中得到充分的显现,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天真烂漫是吾师”,是一种极其净化的境界。
文人画家的性格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重痴,也就是以“痴”为其性格之美。戏剧家汤显祖有两句诗是:“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就含有以痴为美的意思。晋代的顾恺之有“才绝、画绝、痴绝”的美称;到了南北朝时代,梁元帝自画、自书、自题像赞,这时则由顾恺之的三绝转为梁元帝的画、书、赞三绝了;到了唐代又有郑虔的诗、书、画三绝。
梁元帝、郑虔的“绝”里仍然包含着痴的成分。正是由于在文人画家的性格中具有重痴的特色,所以在文人画中才带有一般非文人画所不具备的雅谑意味。如宋代文人画家梁楷笔下的“李白”,就有着痴与狂的个性色彩和雅谑意味,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启示性,是缺乏文人的个性和素质的非文人所画的李白画像无法比拟的。
文人的痴怪性格是有其特定的规定性的,即把痴当作隐德来看待,是指一种对崇高美的追求、不杂物欲的心态,是精神心灵的最高天地。晋代的王湛被他的侄子王济比美于“山涛以下,魏舒以上”,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痴之美。这样以痴为美的隐德,是对封建统治阶级侈言美德而在实际上暴戾横行的一种逆反。
文人追求真诚的隐德之美,故无论其为颠为狂,为迂为痴都是其言与行、品与艺德范一致的表现。于是,也就形成了中国文人画的画以人重和画如其人。
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了注重传神,而对于物象的自然形态的真实面貌的传达并不是最主要的审美意识。另外,痴也指一种用志不分的,长期处于“进入角色”的投入状态。文人画家常常处于“进入角色”般的进行艺术创造的陶醉之中,从而失却常人规范,于是也被人目之为痴了。
文人画家的这种以痴为美的性格,反映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就是雅谑脱俗的独特品格。
文人画的失落与回归
大概可以这样说,以陈衡恪、黄宾虹为代表的近代画家己成了最末一代的文人画家。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文人画的日趋衰落从各方面显露出来。如前所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文人画被视作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和封建主义的艺术,从而处于被抑制、被批判的位置。
青年的一代不是把这一种艺术淡忘,就是视之为淘汰物,还有的青年即使不认为文人画应该淘汰,而基于所受的现代教育,得不到必要的诗、书、画方面的基础培养,也只能对文人画望而却步。可以说文人画的审美基础已几乎不复存在,文人画在现代中国的画坛已行将消失。
在外国艺术评论界,自十九世纪以来,也不是一概对中国文人画视而不见,见而不论的。那么,他们对文人画的评价又如何呢?如奥地利学者弗洛伦斯·艾斯卡芙在其《中国诗书画的关系》这篇论文中,就曾对文人画的综合性及其分类作了分析,并注意到了文人画既可有书法、诗词、绘画综合成图的画面,也有以绘画独立体现诗、书意味而不必有诗词、书法出现的画面,二者都具有文人画之价值。
又如,匈牙利的评论家巴拉·米克洛沙在其所著的《符号学与艺术创作》一书中,则发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美学价值在其诗、书、画溶为一体的整体性中。
他不是把文人画中的诗、书、画看作连体的婴儿,而是把三者作为息息相关的整体进行研究。应该说这些外国评论家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对于帮助广大美术爱好者欣赏中国文人画之美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出自外国评论家的评论也告诉我们对于文人画应加强研究,任何全盘否定的做法都是轻率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推行,人们的审美眼界大开,书法热很快地形成,书法教育也局部地得到恢复,人们的审美趣味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势下,对文人画给予正确的评价和更好地进行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人们审美趣味的提高,总是沿着喜新厌旧与返祖寻源这两条逆向线循环往复和螺旋上升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便有新质的嫁接与溶入。要为文人画招魂,那就要使其植根于民族之沃壤,再生现代之意识,不断地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再拓展、再引入、再更新。
今天随时代而产生的文人画虽不会是古代的《醉仙人》,但却可以创造性地运用文人画这种艺术形式表现今日现实中具有隐喻哲理的山水与人物,使之成为现代文人画。
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烦嚣、污染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气,现代文人画家要表现其热爱人生、热爱自然、热爱生物、净化环境的潜在心声,在绘画中将其纯真而雅谑的人品和艺品再度完善地统一起来,从而创造出现代文人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广大美术爱好者和社会所十分需要的。
总之,文人画的回归与复兴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大有希望,文人画的高度美学价值正在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认识;而文人画的复兴与创作,又不是对古代文人画的模拟,在艺术手法上也不是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基础上,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将赋予它一定的新的内涵。文人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会再显异彩,重现新姿。笔者相信我国的文人画是能够成为新世纪艺坛上的一枝奇葩的。
关于现代文人画的新机趣
作为文人画要素之一的学问一项,应视之为文人画的基石。而文人画家的学问又是随时代而更新的。在当前,中外知识已成爆炸状态,重习经史百家的大量典籍将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文人画家只能适当地掌握和具备古典文艺的精髓,同时大量了解现代艺术史、论以及美学知识,在哲理思想方面更要有新的延伸,具备新型的现代哲理意识。
文人的题跋,字约文深,诗词又束缚于格律,给创作带来困难。在今天创作文人画时,则不一定都使用艰深的文言、韵律极严的诗体,当代的隽语,言简意赅的漫诗,也可以和谐地交融于文人画的乐章中,因而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何况文人画的表现,是以文人的情致为第一性的,而并非每幅作品都要长题大跋。文人画的题材是广阔的,既可以有传统的命题,理想与自然交互生辉的山水与隐士型的人物,都不妨在新的审美眼光照应下入画;对于当代的生活画面,也完全可以本着“街头巷语皆入诗”的精神,经过提炼,纳入现代文人画的题材范围。
现代文人画的创作不仅要在外在形态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在画面中透出现代人的意识和新的机趣。文人画应是画家崇高人品的体现。做一个现代文人画家就须具有现代人类思想的高度、美化陶冶众生之心灵的使命感、以及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的情感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的灵感和新的机趣。
在这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处于商品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现代文人画家,自然要受到商品价值的冲击,对此如无必要的清醒与觉悟,则使得文人画家很难在创作中展现其全部才华,一旦成为拜金主义画家时,其作品的崇高思维也就会有所减损。
现代人类的不幸诸如战争、环境与生态的恶化、社会风气的污染等等,促使具有美善之怀的诗书画家在对于社会发展、前景美好感到由衷喜悦的同时,亦有令人忧心的危惧。也只有当现代文人画家具有这种真诚而强烈的社会情感时,才可能在某种契机的触发下获得生动而别致的新的机趣,从而创作出具有新的意味的文人画作品。
中国本世纪九十年代以下至下个世纪的艺术将经历着巨大的变动和发展。古老的文人画艺术重新回归艺坛之际,将是中国艺术全面振兴之时。我们顺应着经济的日益发达、人文的昌盛、审美水平普遍提高的形势,而对现代文人画发出呼唤,并不是出于某种怀旧的心情,而是为了适应和满足社会主义文明广泛的文化需求。
未来的历史将可以证明:当现代文人画得到充分发展之时,那时文人画巨匠的作品将陶冶着抚慰着那些渴望得到更高级精神境界的广大群众的心灵;在现代的艺术领域,文人画所充当的角色和它所能完成的任务,远非其他形形色色的昙花一现式的画坛流派所能充当和代替的。
——月雅往期经典,点击以下链接直接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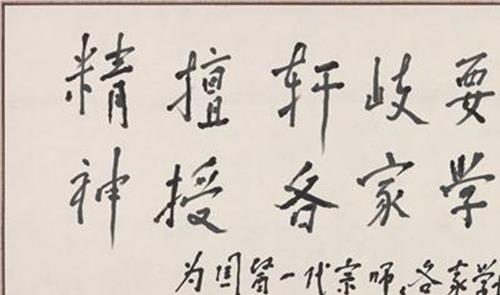









![>徐福顺王宜林 [青海日报]徐福顺会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一行](https://pic.bilezu.com/upload/e/f2/ef201d2b929a8b280ee064556f085b8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