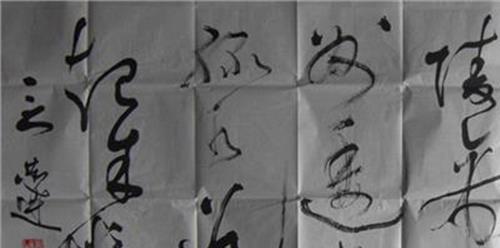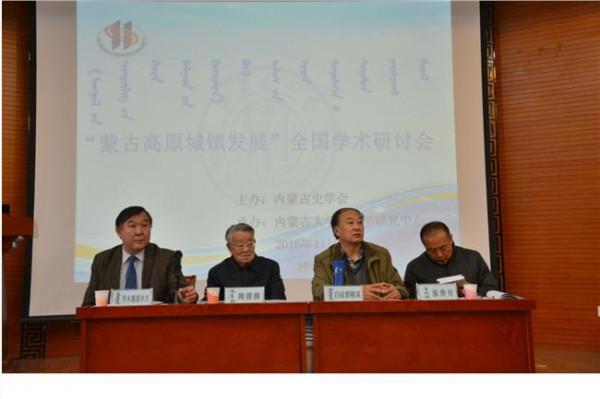何中华人品不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篇/作者: 何中华】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当代启示(下)
何中华
(接上期)
二、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性的冲突及其困境
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遭遇、对峙和激烈的碰撞,大体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心理结构”层层深化的过程,它们在时间上似乎没有先后,西方的坚船利炮隐藏着制度安排,进而取决于文化动机,而文化观念的同化也总是需要借助于物质手段和制度安排。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人遇到了一个特有的文化心理上的爱憎情结: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我们是因憎而爱,即如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本位文化,我们则是因爱而憎,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之深,责之苛”。这几乎成为国人的一个难以打开的情结,直到今天依然困扰并折磨着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所内蕴的现代性之间冲突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刻画。这里尝试着做出一种可能的描述:
1.群与己。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传统蕴含着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具有重视个体的权利和价值的取向;当群与己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两者不可兼得时,己无疑具有优先性和至上性。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群体的至上性。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传统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2.义与利。中国文化重义轻利,更强调道义至上。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辨,应该是“以义制利”,“义然后取”。这同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精神中的功利主义取向相抵牾。因为西方文化更看重利益。殖民扩张历来是西方文化的传统,而殖民统治的背后,总是隐含着功利动机。

3.德治与法治。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本位主义传统,所以政治上推崇德治,尽管历史上也有严刑酷法,但它本身的合法性仍然需要借助于道德来得到辩护。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和古罗马的法律传统融合而成的。
法治精神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德治总是相信人格的道德魅力,从而缺乏一种制度上的制衡和保障,特别是当现代性的因子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后而出现道德失效时,德治传统就缺乏足够的疗治措施和有效手段。
4.道与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及至启蒙精神对人的“发现”,重点在于以理性视野发现了肉体存在的人。对人的需要的肯定也必然着眼于经验意义上的对象。由此决定了人的物化倾向。这也正是现代性语境中人的异化的实质。中国传统文化则着重超越性,从道的层面提升人的境界,追求人的精神的安顿和心灵的皈依。由此决定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性善论与性恶论的根本分野。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西文化在近代的遭遇,乃是中国的伦理本位主义传统与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因为文化原本就没有对错是非可言。关键在于具有不同偏好和旨趣的文化相遇了。这是具有悲剧意味的。
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质何在?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价值的人文关怀之间的冲突,规定了两种文化传统在总体上的摩擦。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具有象征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二元分裂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表达,所以极其深刻。它体现着人类学本体论悖论。
晚清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是:被抛入一种客体化的命运——注意这里的被动语态。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式的现代化”(美国学者布莱克语),它实际上不过是“被现代化”而已。文化本来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一个民族成其为这个民族的最为本然的根基,是民族的标记。
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文化的,而不是地域学和人种学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化只能作生命观。所以,文化只有作为主体性规定,才能以其本真的方式彰显出来。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国文化却陷入了被对象化的命运,中国其实是“被发现”的,东西方文化不是“相遇”,而是西方“发现”了东方。
这种不对等造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西方的镜像,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化,但这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一种对象来加以审视,这本身就已经使其变成身外之物了。
因此,吊诡的是文化的自我发现,同时也就是文化的自我丧失。这正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产生文化焦虑的根本原因。
文化客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自我殖民化”,也就是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性迷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去?”找不到答案。这是中国人文化信心重建所面临的最深刻的障碍。这有点类似于女性解放面临的难题。其后果就是文化自主性的丢失,陷入“文化孤岛效应”。
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解构,为我们的文化拯救提供了历史契机。西方文化出现了一种自反性的辩证法,即以自然界的祛魅和人之生为特征的启蒙精神,导致的是自然界的返魅和“人之死”的辩证法。后现代对于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和对主客二分模式的颠覆,意味着西方文化本根处出现了致命的危机。
它不再是枝节性的和个别结论的问题,而是根本预设的问题。西方思想家的绝望源自这里。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解构的确深刻地触及到了现代性的缺陷,但是却未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拯救之道。
它的自身逻辑内在地决定了它只能带来纯粹颠覆性和绝对破坏性,而无法给出一条积极的思路。西方文化的后现代维度所造就的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和拯救价值得以彰显。
例如天人合一的文化原型,对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伦理本位主义的取向,对于优化人际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诗意化的文化偏好,对于矫正技术的工具化格局,同样不乏启迪作用。中国文化对于人的欲望的看待方式,对于约束现代人的放纵,同样会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如此等等。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背景下的启示价值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益深度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市场化取向和全球化趋势,构成了当代文化的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为现代性提供了历史基础,同时也暴露了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自我解构之时,西方文化恰恰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在后现代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则有可能得到重估和彰显。
1.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尺度意义和启示意义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所属的文化传统都具有生命的意义。“文化”就是“生命”,“传统”就是“我们”。分别言之,“传”乃是通过给出文化基因而在时间上实现延续(复制和再现)而实现的文化整合,“统”则是通过提供文化原型而在空间上的涵摄(识别和选择)而实现的文化整合。
从尺度意义上说,对文化传统持一种敬畏与同情的态度,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乌托邦”,它仅仅是为了从文化源头上寻找一种参照和判断的尺度。毫无疑问,没有谁会天真地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完全的和绝对的意义上被现实生活所再现和重演;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就因此而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起源就是目标。汉儒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与时俱进并不是绝对的。永恒之物其实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永远的参照系,它就积淀并浓缩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所以,保持对永恒之物的敬畏,就必须首先保持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应有尊重。就启示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启示当代人类内在地约束和限制人的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当代人类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
启示意义是永恒性的,它将永远伴随现代人,成为一种不能也不应被遗忘、即使遗忘也必将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重新唤醒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智慧的魅力之所在。
传统文化的上述意义都是“后现代”的。如果说,它对于西方文化还存在民族性距离,从而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这种意义的实现,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则是本土化的资源。就此而言,也就更容易被“激活”,从而更容易得到实质性的认同、弘扬和传承。
2.在人与自我的关系维度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助于强化文化意识上的自我认同和德性人格上的自我实现
人在现代性同化中的自性迷失,造成了人的文化认同危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內源性的现代化,它不像西方国家是以回归传统为姿态的,而是以“置换”掉本土文化为代价实现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西方强势文明的扩张,文化多样性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对于人类的存在而言,文化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现代人的最深刻的危机也许不在于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在于安身立命的问题悬而未决。我们面临着“文化失忆”的危险。我们突然发现,在传统丢失之后,无法真正融入西方文化。
因此,重建文化认同的基础,复兴传统文化精神,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回忆和唤醒被遮蔽、被遗忘的文化基因,进行文化上的“寻根”,在当代背景下具有迫切的拯救意义。
在人格意义上,真实的自我究竟是什么?是肉体还是精神?人始终面临一个“做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把道德作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人的德性人格的充实,也就是人的自我实现。孔子所谓的“杀身成仁”,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都鲜明地体现了超越人的肉体存在的取向。
“真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的冲突,使“做人”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人是选择的动物。人们面临的选择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做想做的事——任性;二是做能做的事——符合自然律,按科学行事;三是做应做的事——道德律的要求。
16世纪的法国人拉伯雷有一本书叫《巨人传》,其中描述德廉美修道院作为个性解放的象征,它的唯一规则就是“做你想做的事”。
这让我们想起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科学无政府主义的那句有名的口号“怎么都行”。其实,只有“道德”才体现着人对自然界的超越关系,从而构成“真实的自我”的“标志”。“应该的”也就是出于人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的规定。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导我们的。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顺天体道”的文化取向有利于改善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
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取向内在地蕴含着理性的独断化姿态,其结果只能是戡天役物。这种逆自然而行的诉求所导致的实践后果和观念后果,正是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期的突然暴发,从而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的原因。现代社会违背自然的表现在于:一是人的欲望的人为塑造(市场逻辑);二是对大自然占有的姿态(工业逻辑)。
近代英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培根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
”([英]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在他看来,“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同上书,第113页)这里所谓的“服从”,其前提乃是“认识”,其过程乃为科学之探索,其结果乃为科学之理论。
由此不难看出科学的用意所在。“戡天役物”的取向典型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特质。培根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是“知识就是力量(或曰权力)”这一名言的最好也是最贴切的注脚。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认识自然”并非为了“顺应”自然,而是为了“改造”和“创造”自然。
他们相信“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因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同孟子所说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可谓大异其趣。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中国人对于“天”有着一种宗教般的情感。
现代工业把生产变成了科学的应用,亦即技术的宰制。“归真返朴,顺其自然”乃是恢复科学技术的古典精神的唯一可能的选择。海德格尔区分了古典技术和现代技术。他所描述的古典技术尚不存在与天道对立的性质。只有现代技术由于离开了“在”而把持“在者”,才形成了今天的困局。
他开出的药方的技术的艺术化。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如果说科学技术使“在者”之“在”遮蔽,那么“艺术却是把在者之在敞开”([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3页)。
而艺术不过是真理的澄明,真理的澄明归根到底不过是本来如此者的显现。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话说,亦即所谓“道法自然”。因此,使现代科学技术由对“在者”的把持回归到“在”本身,真正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恢复技术的道法自然的原始本性。唯其如此,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回归。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主义取向能够为现代人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
4.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仁者无敌”对于“争于气力”时代的昭示意义
古希腊神话有所谓“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之说,中国先秦的韩非子也说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现代性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上颠覆了道德的合法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这一从进化论模式考量应该是最文明的时代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手段最残酷的杀戮。强调必然性逻辑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剥夺,使人们无法也不愿充当道德责任的主体。
科学理性只教会人们做能够做的事,却不能教会人们做应当做的事。市场逻辑在事实层面上解构了道德存在的基础。因为“零和等局”的博弈论范式,把人们抛入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格局之中,使“利己”与“损人”之间无法剥离开来,并且具有了内在的因果关系。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时局,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当代人类无可逃避地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按照肉体原则向物的世界沉沦,还是按照心灵的原则向精神的世界拯救?可以说,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相信“德性就是力量”?中国文化主张选择道德的拯救。这才是人类在未来的真正出路。
按照《说文》的解释,“儒,柔也”。一个“柔”字,颇值得玩味。老子曾说:“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的确,道德在表面看上去是孱弱的,因为道德就是人为自己立法,属于人工规则。作为人工规则,道德规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可违反性。
因此,道德往往显得很脆弱。这也正是许多人之所以不相信道德的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只有道德才能彰显人的崇高和尊严。它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根能思想的芦苇。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又是一种最强大、最坚韧、最深沉的力量。
所以孟子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相信德性的力量。中国文化传统讲究“以德服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长城这个最大的建筑工程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征服和扩张性的。
郑和下西洋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显示了东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的旨趣和性格。在出现道德衰弱的今天,我们欲拯救世道人心,改善并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就不得不回首被人遗忘了的古老传统。正是在那个遥远的绝响中,我们依稀听到了希望的声音。□
(作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