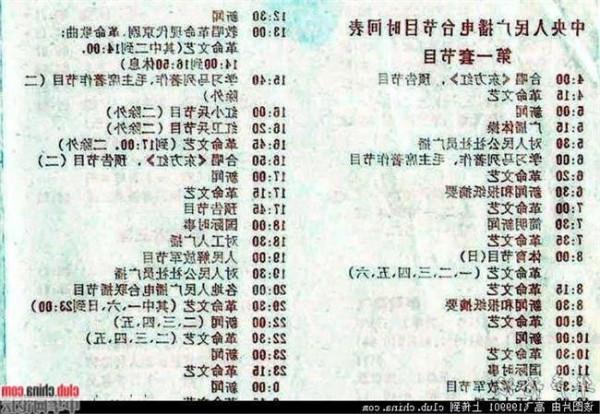王实味之死:思想是如何被扼杀的
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位更“出色”的女性,这位“出色”的女性后来的一部作品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位出色的女性就是丁玲。丁玲是“文抗”的代表,整风运动之初,同样主张文学作品应暴露黑暗,她的《三八节有感》同属暴露黑暗的作品,按说应该与王实味志同道合。
但毛泽东先生表态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丁女士便诚惶诚恐,感激涕零了:还是我党英明伟大,党恩如太阳高照。她在取得“同志”的权利之后,惟恐自己的反省得不够彻底,来一招釜底抽薪,将昔日的“同僚”一脚踢开。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恶毒的语言是如何从一个女性的口中讲出。丁玲当时虽然也受到批判,但绝对不至于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更不至于严重到非得置王实味于死地才能脱身。她将王实味的事情这样无限地上线上纲,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是有生命危险的。
丁玲是一个聪明人,这绝对不会不知道,在这近似谩骂的批判背后肯定有着阴暗的动机。艾青、丁玲们对王实味的批判,实际上开了文人相咬的先例。艾青、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一员,在这过种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他们不但没有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担当起批判社会黑暗和捍卫社会正义、人类尊严的重任,而且在政治的高压下毫无条件地放弃了自我和尊严,充当了政治的打手。他们的行为比一般“群众”表现得更差,影响更为恶劣。
一般的群众尚可以以“愚昧无知”作为开脱的借口,而丁玲、艾青们绝不能说是“愚昧无知”,在他们无耻下流的行为(请原谅我用如此激烈的言辞)的背后,是人格的萎缩和自我尊严的缺失。
有学人说:在所有人的错误当中,知识分子的错误尤为不可宽怨。(大意如此。)因为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它代表的是这个民族的良心和正义,他们应该凭着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引领着这个民族走向更加理性、更加高贵、更加美好和幸福的天国。
他们的表现应该比任何人都出色。任何人都可以堕落下流麻木不仁,惟独知识分子不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放弃自我放弃思想放弃尊严放弃良知,惟独知识分子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一个民族将不再有扭转苦难现实、走向新生的希望。看看延安整风中的丁玲们的表演,你就可以明白,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存空间是如何一步一步窒息下去的。
就王实味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写出举世闻名的文学作品,也没有提出洞烛千古的原创思想,他的唯一可贵和让人钦佩的,就是他坚持了人格的独立和捍卫了自我的尊严。在所有的作家争先恐后地歌颂“大好形势”时,他孤身一人将“暴露黑暗”进行到底;在大家取消了思想,听从一个领袖的指挥时,他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微信:lishicfda在所有的作家膜拜于权杖之下时,他独自一个对抗着权威。
这一切的一切,都闪烁着作为一个人的光辉,——所谓一个人,不但是在肉体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更是在精神意义上、灵魂意义上成为一个人。
这就是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这样的人,必得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自由的意志。王实味曾就读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自觉继承了北大的自由批判传统,他始终将思想的启蒙与社会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正是这种对自我使命的偏执使他陷入悲剧。
王实味又是最“正常”的一个人,他对事物总能作出正常的反应,他总能保持着对事物最真实的感觉。直到最后,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等“托派分子”依然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正常”,即人对客观事情的一种情感反应,该爱的时候爱,该恨的时候恨。
任何外在的事物对人“正常感”的干涉,即是对人精神自由的压抑。人的精神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就会逐渐走向冷漠和粗鄙——即失去正常感:应该同情怜悯的,只有冷眼拳脚相向;该批判痛恨的,却又“颂”声喧哗。
一个有着正常感觉的人,他对事物的判断就不会迫于世俗的权威或压迫而改变。正是这种正常感,使王实味看到了延安生活的黑暗面,也是这种正常感使他不能如艾青们一样对黑暗不批判反而是歌颂。
如果艾青、丁玲们有着正常的感觉,他们就会根据自身对现实的体验来看待王实味对延安的批判,也会根据平时与王实味的实际交往而非政治权威而决定对王的态度,而不会在王受到zhengzhi迫害时把自我对现实的把握一手抛开,把昔日的朋友一脚踩在地上,批死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