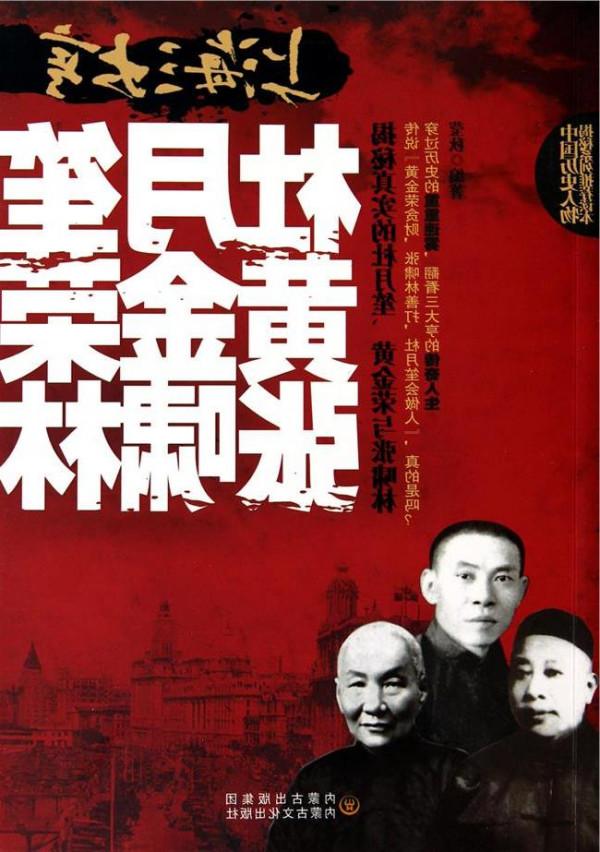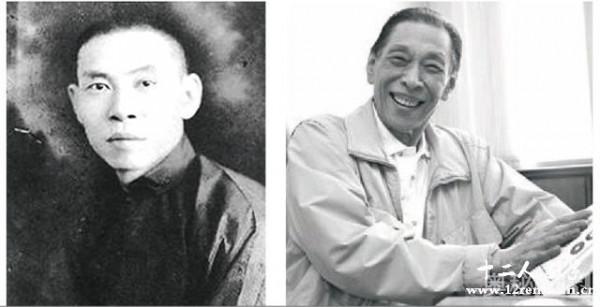章炳麟与杜月笙 章炳麟:革命不忘讲学
每回下苏州,便想起郁达夫《苏州烟雨记》中的那些话:"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争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地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请你们跟了我来,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乞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可如今的苏州亦非往日的苏台,但比起北京喧嚣,这里委实能让我悠然地吸上几口清新的气息。

傍晚,和友人沿道前街散步,竟不知不觉到了锦帆路,路过章太炎的故居。两幢被称之"国房"的青砖"民式"老楼,掩现古树浓阴之间。高围深院,亦如先生之门墙,不可企及。我曾多次从门前路过,大概因为门口挂着什么会的牌子,以为公家办公场所,谅是不便入内。门前已不见"章氏讲学会"和那"制言半月刊"的牌子。从知堂先生的文章中获知章先生的墓曾在故居的后院。我生也晚,章先生自不可见,章墓是应该一谒的。

章太炎大名鼎鼎,其学谅也深不可及,故而章的那些太学术的著作我也未曾读过,但对章的生平行迹却兴趣十足。周劭先生有篇旧文《半小时访章记》(署名周黎庵)发表在1935年第78期《论语》杂志上,记叙三位年轻人贸然造访章宅的有趣片段。
比如,写章的出现:"他步履端详,声息全无地从后门踱进来……章的身子本来已有了十五度,再略加几度,便算宾主揖让过了。"又"他穿着一件蓝色缎子棉袍,加上一件玄色大花对襟半臂,脑袋大得惊人,估量里面不知藏了多少‘国故’。"
今天,只能从这些文字里揣想着章先生的风度。
说来真是"故事"一般。从章馆门前走过,我还依依不舍地回望几眼,想当年章先生在此开馆授学,生徒云集,好生热闹,我若赶上,定也若那三位访章人一样投刺而入。正想着,走到了定慧寺巷口,朋友告之,双塔边有位宜兴人购下小楼,经营一些什件字画。
便随之而入。长话短说,小坐片刻,主人竟出示章太炎行书条幅,一见大喜。主人倒也慷慨,拱手相让。并说:本想挂在橱窗,朱老头每天路过,让他看看。所称朱老头便是章先生晚年的学生朱季海先生。早就听说朱翁常在双塔吃茶,而访朱之意早在10年之前,未知是机缘未到还是生性懒散,一拖再拖。趁新得章字兴味正浓,次日一早,便约三两闲人赶来双塔。
以上是我《过章太炎故居访朱季海》一文的开头。虽说往事如梦,却总是耐人回味的。如今,章先生的书轴挂在我的书房,便也常常勾起我的江南之思。
鲁迅曾说,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留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这位章炳麟先生积极参加革命是实,盖因他天生反骨。他虽是荫甫太史的高足,其行径绝不走翰林进士的科举之路。他治国学,以古籍为考据的工具;而他的文字则竭力鼓吹革命,即逃亡日本,亦推行新进思想。次年归国,遂与邹容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革命失败,他与邹容、陈吉甫、钱允生等人被指为"伪作革命军匪人"入狱,却俨然豪烈,口呼"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
及至清亡建立民国,章已绝意锐进,唯以学术为乐。袁项城行帝制,章太炎又犯起革命的脾气,自由言论,被袁软禁于故都龙泉寺。章在狱中绝食抗议,似无一般书生的软弱。但这种凭着血气的刚强毕竟难敌时间的考验,无望之际,他寄信与夫人汤国黎,感叹"我死了之后,国粹便中断了"。
由此可见,章氏的骨子里还是作学问的读书人,如许寿裳所说的"革命不忘讲学"。在章的眼里看来,所谓"国粹",一是他的学问,二是他的风骨,追求自由反对保守的革命精神。
太炎先生的叛逆,积极的入世态度,故往往遭遇苦闷,不平则鸣,其言行在常人来看多少有点怪异,久而久之,便目之狂狷疯子之类。章太炎也并不忌讳人家呼他"章疯子",他反对作古文,虽然他一生埋首典籍,他著《国故论衡》,却署《或古仑鱼》,怪特荒诞,也是他狷介的一个侧面。
《国故论衡》是太炎先生谈论国学的经典。前些时,报上见某教授称:现在谈论国学的人很多,如果你读不懂《国故论衡》,就免谈。从《国故论衡》到《章太炎的白话文》,章太炎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始,他既不反对白话文(却反对白话诗)又不积极支持,也不能说是他对古文的怀念,可能更多的是他对当时白话流于通俗的失望。
1935年,章太炎论及白话与文言的关系称:"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竟能离去文言否?"进一步认为"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白话与文言之关系》)事实上,五四时期的白话"夹生半熟"可能正是它的特点,以明清笔记加上英式散文,成为时尚之文体。
及至今日,白话已如白水,寡淡无味,好在章先生眼不能见心即无烦了。
对"疯子"及"神经病"的议论,章太炎曾有一段精彩的自解: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也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
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年7月15日)。
"章疯子"的传闻很多,民国笔记中处处可见,故不费笔传播。回头说那日得到章先生的墨宝,次日即往镇江参加一个书学研讨会。客舍中出示与诸位理论家们欣赏。张铁林兄说:你还是要收一些好的书法。影视圈中张以富藏书法见著,王铎巨制、赵之谦尺牍皆是他重金所获,一时书法圈亦艳慕不已。
我想同为收藏,只是兴趣各异罢了。而另一个理论家却说,字有问题,理由是鲁迅是章的弟子,书学章师,而此幅与鲁迅的字风格迥异。我也只能付之一笑。
太炎先生的书法以篆、行见长,倒是不曾见过他的隶书,而他的先生俞樾却是八分书法的名手。章太炎作篆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二徐(徐铉、徐锴)为宗,结字多见欹侧变化的异趣。往往参以行意,行笔洒脱,信手出之,但其篆法却极讲究,恪守《说文》。
太炎先生的行书也是迥异时流的阁帖风气,以颜(平原)为骨,撷董(其昌)之韵,偶然参以篆书笔意,古拙生辣而又极具疏朗淡逸之气。当年,有马叙伦者说"太炎不能书"(《石屋馀沈》),这正是所谓书家的看法,而这种识见至今仍代表着那些"职业书家"的大多数的认同。诚可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