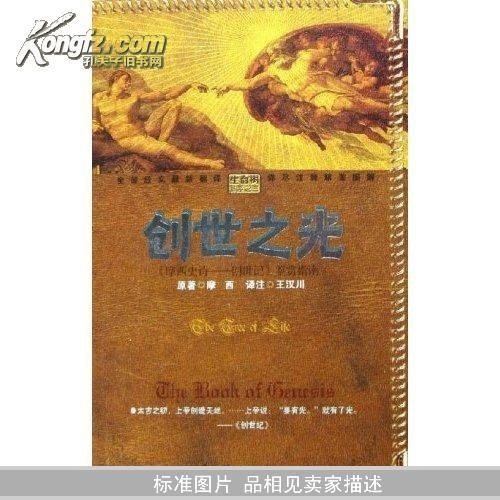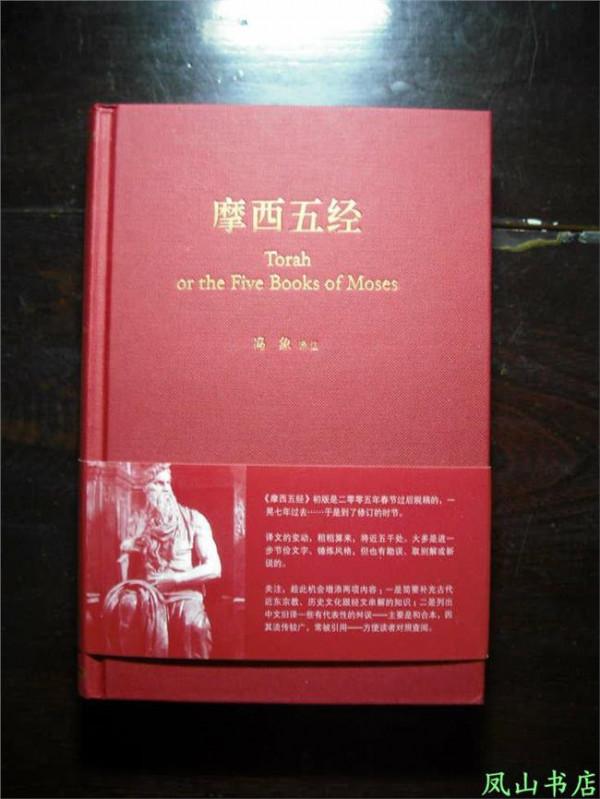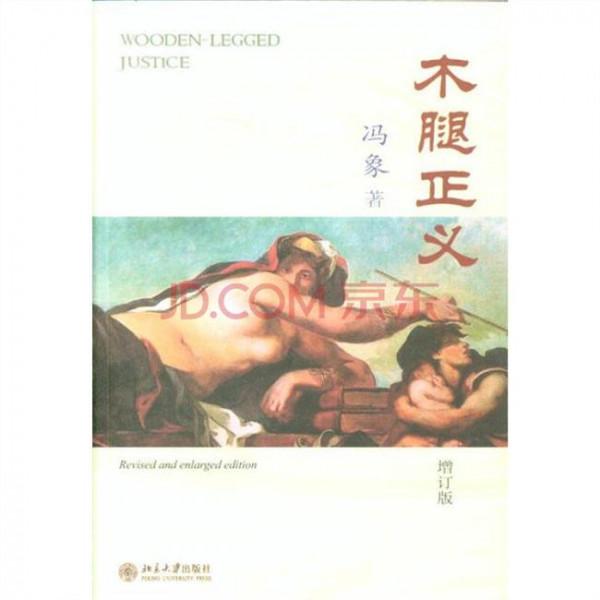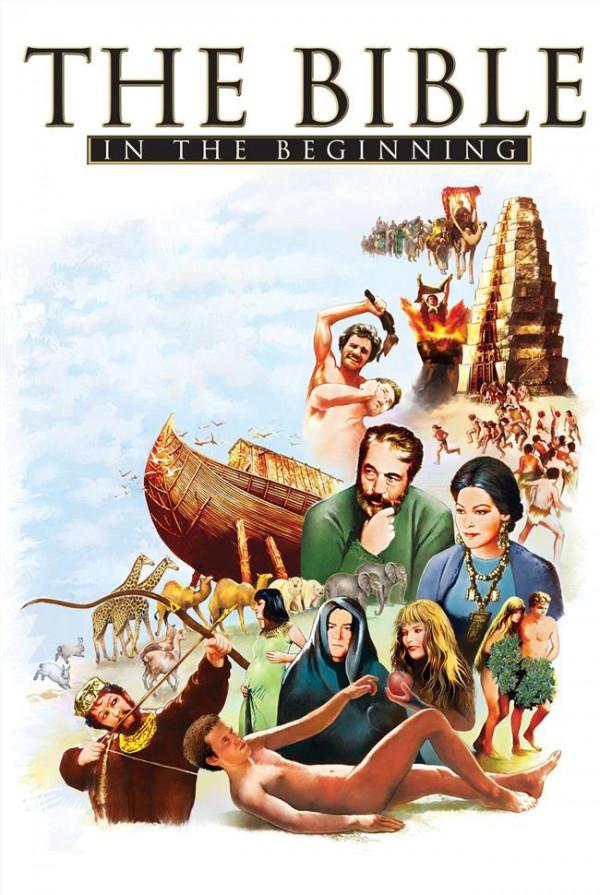冯象传奇 高峰枫:评冯象《创世记传说与译注》
国内近来又有“读经”的呼声,不免令人想到周予同作于1926年的一篇文章“僵尸的出祟”。当时江苏教育厅明令各省立学校禁止男女同校,校内禁用白话,并且特设读经一项,要求“择要选授,藉资诵习”。这项命令引起周予同强烈不满,他将读经一事指斥为“僵尸穿戴着古衣冠,冒充着神灵,到民间去作祟”。
他随即写下这篇讨伐的檄文,罗列了经学史上的几种主要观点,意在强调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经”是什么、哪些书可算作经书——实际上已然聚讼纷争了上千年。
文章的最后,周予同郑重宣布自己的意见:“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圣经》一样”(《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603页)。
周予同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当年爱国学生闯入曹汝霖府邸,火烧赵家楼,那把火就是他和另外一人点起的。这篇“僵尸的出祟”是周先生27岁时的“少作”,言辞不免激切。儒家经书当然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什么大毒草。事实上,周先生自己后来就长期致力于经学史研究,五十年代末在复旦大学开设经学史课程,自然也不是把《十三经》单纯当做粪便和尿素去检查和化验的。
周予同先生在批判当时的读经运动时,不忘顺便连带上基督教的圣经。中国有经书,西方也有自家的经书。西方的经典著作不少,但真正能称得上 “经”的只有一部书,那就是圣经。这一点向无太大的争议。就连荷马史诗也当不得“经”的称号,只是为了强调两部史诗对于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有时也说荷马的诗歌如同古希腊人的圣经。
要深入了解西方的文化,圣经自然是头等重要的书。说得直白一点,圣经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 (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76)。我们现今讨论哪些书可算是自家的经书,可否同时也能将读经的范围稍微拓展一些,将西方的经书也包括进去呢?
译经
听人说冯象准备重译《创世记》,一直翘首企盼。一买到这本《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就迫不及待地先翻阅译文,结果发现与自己的想象有一些出入。原本以为冯象写的是一个详注本,因为圣经考据学一直是西方历史考据的样板,专门名家的学者不计其数。
如果能将十九世纪以来旧约学者的既有成果分条析缕,汇聚于一书,对国内严肃的西学研究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但是冯象显然不是要写一部中文的《创世记集注》,他的译文中只在行间有简明扼要的解释,包括关键词语的训诂和犹太古代民俗、地理和制度方面的解说,全部译文加简注不过一百一十余页。而放在译文前面的是二十篇“故事新编”,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
冯象西学功底深厚,国内少有人及。此次不仅从希伯来原文重译《创世记》,而且参照圣经多种古译本(如希腊文七十子圣经、拉丁文通行本)和英文钦定本、法文圣城本、德文路德本等著名译本。译文中间穿插的注释虽然简略,但重要的文字校勘、词语训诂、以及犹太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方面的解释都有涉及。
比如该隐杀弟一段,就根据希腊文旧约译本补上脱落的一句(1:8),文义更为顺畅。又如上帝为亚当造一“般配的帮手”(2:18),冯象注出并非主仆关系,而当亚当给妻子取名夏娃时(3:20),冯象注出“取名是行主人或家长之权”,这样一来读者就对伊甸园中人类远祖的“家庭政治”和“性别政治”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就不赘述了。翻译古代典籍,能够参校不同语言的多种译本,这样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功力远胜过其他自称重新诠释经典者。
笔者不习圣经希伯来文,无法从语文学角度提出任何意见,故而对冯象的新译文忠实与否、精准与否,均无资格评说。但迻译外文经书,改胡为汉,兹事体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西学功夫仍欠缺,但自觉对汉语尚有一定的敏感。因而不揣谫陋,将一些零星感受在此稍作整理。
流传比较广的圣经中译本是“和合本”。和合本的语言古拙、雄浑,自成一独特的“圣经体”。单就语言成就而论,堪与汉译佛经相媲美。冯象在其他书中曾提到友人对圣经中译本颇有微辞:“《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佶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 (《政法笔记》,页275)。
这种批评并非完全无据。依照现在的标准,和合本的一些用语的确有些佶屈聱牙,不合当今语言习惯。但若说是洋泾浜,我却不以为然。“经”不同于寻常文字,若每一处都文从字顺,象武侠小说那样雅俗共赏,那只能算是人言,而非圣言。因此译经特别需要“陌生化”效果,特别需要读者在一些古怪、别扭的文句中多多逗留一会。
论到译经,我们切不可迷信当今的语言习惯,决不可以所谓“标准”的汉语作为译经的指导。美国学者奥特(Robert Alter)多年从事希伯来圣经的文学研究,曾出版《创世记》的新译(诺顿书局,1996年)。在此书前言中,他评论众多新近的圣经英译本,有一段话批评人们不自觉地依赖“语言习惯”,颇中肯綮。
众多现代英译本往往自诩译文生动流畅,让现代读者能毫不费力地阅读圣经。但是奥特指出,最通顺、最流畅的本子恰恰是最不得原文精髓的,这些译文为了屈就当代读者的语言趣味,牺牲了原文的节奏和神韵。
经书的遣词造句、节奏韵律不是可有可无的装点,而是经文主旨最重要的部分。众多英文译者奉若神明的所谓现代语言习惯,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毫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体,说的难听一些,实乃庸人所作的文章。
奥特提醒我们注意,伟大的作家有哪一个是俯首帖耳、甘心受规范语约束的?现代派小说大家如乔伊斯、福克纳,哪一个写的是“标准”、“规规矩矩”的英语?如果一味遵循此种平庸而陈腐的语言习惯,那么最后成型的译本就只能变成文句的疏通(paraphrase),而不是真正的翻译。
和合本的语言恰恰不够顺畅、不够现代、不够规范,因而才显得有棱角、有骨力,才能带着一种“仙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出自某一人之手,没有烙上过多个人的痕迹,自有一种伟大经典都有的非个人特征。我个人保守的看法是,和合本虽难称尽善尽美,却应当是一切重译工作的基础。我们应当竭力保留或者极力模仿此种圣经体,若另起炉灶,想重新锻造出一种既简朴又凌厉、字里行间浸透神圣气息的语言,恐非易事。
上面这些想法是为了说明重译圣经之艰巨。具体到冯象的译文,单就中文而论,我感觉晓畅明快,颇为清丽动人,读来不费气力,与其他西方古代经典的中译相比,冯象的文字更加细腻,是难得的佳译。比如诺亚方舟一段,神降下大水淹没世界,冯象将这段描写译作:“那一年诺亚六百岁,那一天是二月十七:地下的深渊突然崩裂,万泉奔涌,天穹的水闸全部打开,大雨倾盆,一连四十个日日夜夜”(7:11-12)。
这段译文颇有声势,“那一年”和“那一天”相对成文,很有史诗那种庄重的风格。
而“深渊崩裂”和“万泉奔涌”相对于和合本的“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更加朗朗上口,也更有画面感。尤其动人的是,神安排诺亚及其家人进入方舟之后,将方舟的门合上,和合本译作“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冯象却改译作“门,是耶和华关上的”(7:17),这一句翻译得着实雄浑有力,凸现耶和华主导一切的气势。
罪人关在方舟之外,义人关在方舟之中,我们仿佛能听见这“嘭”的关门声,读来心头为之一颤。
冯象的译文也有一些不足,有些段落文学性太强,过于有画面感,用词过于生动,色彩过于绚丽,灵动飘逸有加,却不能表现经文的质朴和厚重来。我只举一个显著的例子,以说明冯象的译笔有时过于华丽。《创世记》第十五章中,亚伯拉罕(当时尚未更名,仍叫亚伯兰)得一异象,神向他发话,许诺他的子孙将多如天上的群星。
随后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准备祭品。祭品摆放完毕后,经文中忽然生出一段奇异的描写(15:12)。下面分列和合本和冯象译本:
和合本: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冯译:待到红日西斜时分,亚伯兰竟昏昏睡去了。突然,一阵黑沉沉的恐惧包围了他。
若按传统小说评点的做法,在“红日西斜时分”几个字后面当批注一字:画。冯象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译笔美则美矣,却为经文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油彩,添上了一分原本没有的诗意。在“红日西斜”四字中,我看到的是西洋油画中的亚伯拉罕,而不是《创世记》古经中的犹太圣祖。
(冯象书中有大量插图,都是西方历代涉及《创世记》题材的美术作品,我猜测这些油画或许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文字。)夕阳西下,亚伯拉罕满被落日余晖,这里透露出一种浪漫情调,但这样的浪漫主义恰恰是《创世记》所排斥的。翻译古代经书,尤其是关键的段落,还是“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宁粗勿弱、宁僻勿俗”的好。
释经
经典的解释有许多方式,我们习见的形式是注疏,就是以明白的学术语言讲明经文的意思(包括词语的训解和经义的阐发)。还有一种更加高明的阐释手法,是以经文为蓝本,改写或者续写经文片断,创造出新的故事和寓言。这后一种方式不如注疏来得扎实和详备,但天资高的人往往能以大力甚至蛮力撕开经文的一角,使得本来拒斥解释的段落涌出丰富的含义来。比如卡夫卡著名的短篇《塞壬女妖的沉默》就是对《奥德赛》绝好的注释。
冯象在译文之前有二十篇“故事新编”,是将短注中容纳不了而又舍不得扔掉的材料另外写成故事。按照他自己在前言中的说法,是将“原著拆了重新敷演,融入中文的语境与文学传统”(页11)。虽云故事,但不少篇章实际上是对经文的独特阐释。
冯象给我们的不是高头讲章式的解经,他是要将个人生活史努力汇入经文的世界,将受时空历史局限的小我安放在经文广大的空间中。读经是要和经书发生碰撞,发生关联,不是硬生生地牵合经文以就己意,而是面向经文敞开自我、暴露自我,否则经自经,我自我,读经再多,也与自家身心了无关涉。
在这些故事新编中,冯象总是往来穿行于犹太经典和个人际遇之间。一方面用地道的中文重述、“改写”《创世记》中的故事以及许多离奇、甚至玄怪的传说,另一方面则穿插个人的生活遭际和师友往还(“扯上几位师长古人,以为点缀、起兴”),两条线索交错而行,相互映射,结果激荡出一种非笺注、非小说的独特文体。
比如“举目”一篇,叙述神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创世记》十八、十九章),剪除城中恶贯满盈的刁民,只放过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一家。
穿插于其间的是作者一位朋友的故事。西蒙是纽约一家金融资讯公司的副总,和作者在书店偶遇,两个人都对圣经有兴趣,言谈甚欢,始有交往。所多玛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话题,在此埋下伏笔。后来交往渐多,还相约九月十一日共同参加一个募捐活动,结果西蒙在“九一一”事件中不幸遇难,遂成永诀。
两城的覆灭和世贸中心双塔轰然倒地,冯象将两件事并置在一处,逼迫读者思考无辜人受难这样的大问题,故这一篇尤其沉郁动人。读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会感到犹太古经不再与我们隔膜,对于冯象来说,希伯来圣经不是一部死经,而是一卷活书。
可惜二十篇故事新编中并不是每一篇都能象“举目”一样打动人心。很多时候,现代故事与古代经文之间的联系不甚紧密,或者作者自有深意存焉,可惜愚钝如我者看不清其间的关联。如果个人经历仅仅作为点染或者起兴,那只能算文学创作的手段。
比如“假如”一文,本是写亚伯拉罕老管家为小主人娶妻一段故事,但冯象偏偏搬来博尔赫斯老人家(可能是模仿博氏某著名短篇),笔法虚虚实实,生动则生动矣,却难以看出对老管家井边遇利百加这段事迹有什么具体的关联。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冯象的语言。译文的语言已然十分精彩,到了故事新编,因为没有太多的限制,作者更为自由,精彩的笔墨比比皆是。作者将圣经题材融入中文语境,在文字上着力最多。我们经常能读到“耶和华合拢浮云,轻推日月”这样的句子,下面这些话都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耶和华正在宝座上筹划人类大同的未来,隐隐约约听见几声号子,便伸出小指,拨开浮云,俯瞰大地。”
“天使按下云头,厉声喝道:‘狸狸站住,神子在此。’”
“她是宫里生、宫里长的丫头,奴婢的命,那种自由自在浪迹天涯的牧人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