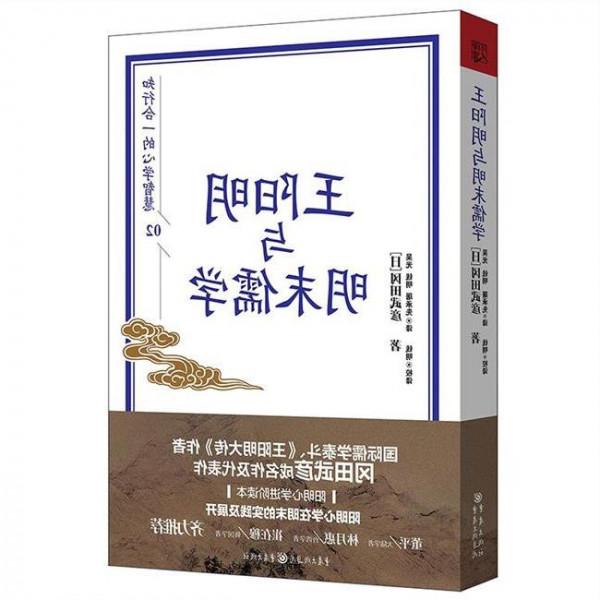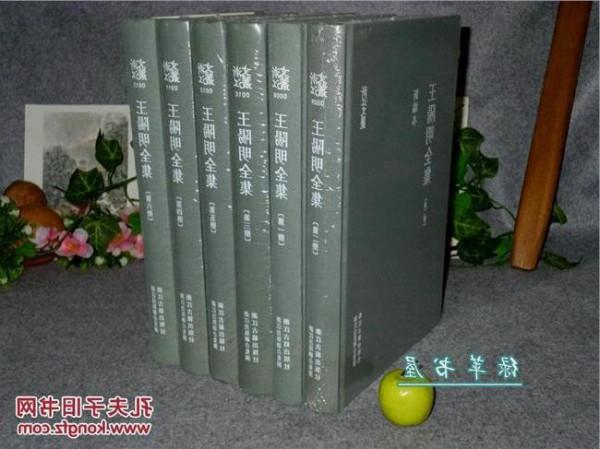王阳明知行合一名言 陈立胜:何种“合一”?如何“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新论
内容摘要 传统朱子学坚持知行之间存在一由内及外的“异质的时间差”,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多有辩难,以劳思光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则否认这一异质的时间差,但又认定知行乃是同一行动之不同的阶段,知行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同质的时间差”,知行合一只能取“根源意义”,而不能取“完成意义”。这种将知行合一的意义严格限定在“根源意义”上的做法,从阳明知行合一的义理系统、知行合一的整体论述以及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工夫论说三个方面看,均难成立。在根本上,知行不是同一行动之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行动中交互渗透的两个向度。知行合一既是根源意义上的合一,也是完成意义上的合一,更是即知即行这一跟行动一体而在的“照察意义”上的合一。
关键词 王阳明 知行合一 劳思光 异质的时间差 同质的时间差
“知行合一”是最富有王阳明思想特色的一个命题,[1]也是聚讼不已的一个命题。[2]这一命题虽经现代学者之多方阐发,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其中,知行合一之“合一”究是何种意义上之合一,又是如何合一,此问题尤值得关注。
劳思光先生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王阳明思想一章“知行合一之确解”一节中指出,常人之所以会误解阳明知行合一说,基本原因在于论者未能了解阳明“知”、“行”、“合一”之特殊语言中所指为何,所指不明,一切评论均难免张冠李戴。
而在阳明之知行词典中,“知”乃价值之知,是知善知恶之“良知”,“行”则是指意念由发动至展开而成为行为之整个历程言,而“合一”乃就“发动处”讲,取“根源意义”,而不取“完成意义”。
[3]劳先生对阳明“知”、“行”之训,确为“确解”,但说“合一”只取“根源意义”而不取“完成意义”,在笔者看来称“确解”恐未安。
本文认为传统朱子学对阳明知行合一之批评,乃是基于常识知行分际之界定必蕴涵着“知”、“行”之间存在一“异质的时间差”这一预设,而当代为阳明知行合一辩护的学者,则顺着阳明的思路否认这一“异质的时间差” (heterogeneous gap)之存在,但却又认为知行之“始”、“成”关系说明知行之间仍有时间差,只不过这个时间差乃是一“同质的时间差” (homogeneous gap)。
正是基于这一“时间差”意识,使得劳先生坚持说知行合一只能从根源意义而非“完成意义”上立论。
劳先生对“合一”的解释,有泥于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一命题之字面义的嫌疑,将知行“固化”为行动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而未将这一命题置于阳明“合一”说的整体言说脉络之中加以通盘之考量。
笔者主张知行并非同一行动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同一行动的两个不同向度,故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时间差,知行合一不只是“根源意义”上的合一,作为“主宰发动”这一“根源意义”上的“知”实贯穿于整个道德行动之始终,故亦是“完成意义”上的合一。
知行合一同时亦表现为“发动之明觉”这一即知即行的“照察意义”上的合一。
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在历史中之所以引起争议,除了这一思想跟程朱知行分际之“定论”相抵牾这一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改变了“知”、“行”二词的日常用法。
人们通常将“知”字限定在人之“内心的”、“隐秘的”生活领域、心理活动领域,而“行”则严格限定在“外显的”、“公开的”举止行动领域。
这两个领域之间界限分明,不容抹杀。而阳明讲知行合一则明确地将“知”、“行”二字的分际加以挪移:将内心的、隐秘的“知”字下移于外显的、公开的“行”之过程之始终,同时将外显的、公开的“行”字上挪进内心的、隐秘的“知”之中。
这一知行二字的“下移”、“上挪”的错位用法,导致了发对者的强烈不满。历史上,围绕知行合一的“辩难”亦多聚焦于此错位用法之辨正上面。
“知”路方能“行”路,一直是朱子学跟阳明及其后学辩论所诉诸的一个重要理据,[4]与此相关的辩题尚有“知”食方能“食”、“知”好色方能“好”好色,“知”恶臭方能“恶”恶臭等等。
换言之,在坚持知行分际的朱子学看来,“知”与“行”之间总是存在一先后的次第、一“时间差”。
这也是自古至今学者对阳明知行合一说质疑的一个要点。当初顾东桥致书阳明就是如此质疑的:“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
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厘倐忽之间。非谓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132:165)[5]从“知”到“行”有一先后次第,“毫厘倐忽之间”显然就是间隙,尽管这个间隙很短,短到只能以毫厘倏忽来形容,但毕竟还是一个间隙。
王阳明当然不会同意这种“间隙”、“时间差”说,面对弟子徐曰仁“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之质疑,阳明回应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敎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
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敎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传习录》5:33) “知行的本体”即知行的本然状态,或者说是本体意义上的知行之性质。
在这种本然状态之中,知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修身活动之中知、行是相互渗透、相互贯穿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语即说明了这一点。见到好色的同时已有好之的意志活动,闻到恶臭的同时即有恶之的意志活动,同样一旦觉悟、理解一个正价值,同时即有实现之的道德意志产生,一旦知道一个负价值,同时即有一深恶痛绝的活动产生。
“知而不行”、“明知故犯”已非“知行的本体”,因为此本体已被私欲隔断,就如同鼻塞之人,即便是恶臭在前,亦不曾闻得,是因为作为“孔窍”之鼻被阻塞一样。
值得留意的是,阳明在此论述“知行的本体”所使用的两个比喻,一者是视觉与嗅觉,一者是身体感受(痛感与饥饿感)。看见好色、闻见恶臭,这是感性知觉,喜欢好色、厌恶恶臭,这是情感意志。
依阳明,看见与闻见好色与恶臭的同时,即有一喜欢与厌恶的意志参与其中了。中文的“好恶”二字颇耐人寻味,“好”字,既是“美”、“善”之义,音为“hǎo”;又是喜爱、爱好之义,音为“hào”。
“恶”字,既是“丑恶”、“坏”之义,音“è”;又是“厌恶”、“憎恶”之义,音“wù”。
是故,见“好”即“好”之,见“恶”即“恶”之。
“痛感”的产生乃是基于皮下神经末梢受到某种外来刺激时所产生的兴奋,然后通过生物信号的形式传入大脑皮层,引起痛感。阳明“必已自痛了,方知痛”这一说法实是一同义反复,因“痛”与“知痛”本是一回事,“不知痛”何来“痛”?“不痛”何来“知痛”?在此“知痛”之“知”即是“感受”,“知痛”即是“感受到痛”。
倘因病变而致传导痛觉的神经失常,人就会患上可怕的“无痛感症”,就是针扎、刀砍均感受不到痛,病患者从不“痛”,自亦从不知痛。饥饿感跟痛感的情形很相似,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老鼠倘被切除“饿神经”,则会不再进食,面对丰盛的食物而被活活“饿”死。
显然,“知饥”与“饥”亦是一回事。
表面看来,这两个比喻是不同的:在“看闻比喻”中,“看见”、“闻见”跟“喜欢”所看者、“厌恶”所闻者,尽管说难以分开,但毕竟是有区别的,而在痛感、饥饿感比喻中,知痛与痛、知饥与饥完全就是一回事。
但严格追究,如闻到“恶臭”而不“厌恶”之,则实可以说对闻者而言,并不是闻到“恶臭”(如嗜臭豆腐一族,所谓臭豆腐实并不真“臭”),如此,闻恶臭(见好色)与恶恶臭(好好色)亦是一回事。
站在朱子学立场的传统学者,并不接受阳明的这一辩护。他们要进一步追问:即便“见好色”、“闻恶臭”跟“好好色”、“恶恶臭”之间不可分,即便知“痛”、“饥”、“寒”跟“已自痛”、“已自饥”、“已自寒”是一回事,那么,“好好色”、“恶恶臭”、“已自痛”、“已自饥”、“已自寒”究竟属不属于“行”之范畴?换言之,“好好色”、“恶恶臭”、“已自痛”、“已自饥”、“已自寒”不仍然还是“知”之范畴吗?因为严格追究起来,“好好色”、 “恶恶臭”“已自痛”、“已自饥”、“已自寒”仍然只是一种内心的意欲、或感受,因而仍然属于“知”之范畴,只有因好好色而趋近之,因恶恶臭而远避之,因痛而拊摩之,因饥而求食充饥,因寒而添衣驱寒方属于“行”之范畴。
倘若“已自痛”、“已自饥”、“已自寒”乃至“好好色”、 “恶恶臭”皆仍属于“知”,而不属于“行”,则此类“知”总跟实际的“行”有一先后之序、有一时间之间隙。
在阳明去世后不久,陇右著名学者鸟鼠山人胡缵宗在其晚年著作《愿学编》中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辨析甚力,他发难的要点就在于指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知、行二字发生了错位之使用:
然知自知,行自行也。夫所谓好色恶臭者,知之苟切,行之必笃,理也,然未及于行也。盖见色而好,见臭而恶,属知;好若色,恶若臭,属行,但未近乎色,未远乎臭,乃未可云行尔。……又云知寒必自已寒了,知饥必自已饥了。然觉寒与饥,知也;备寒与饥,行也。寒未衣犹寒也,饥未食犹饥也。将谓己自寒,己自饥,遂为行乎?今有人焉,真知夫事亲必婉容,必愉色,斯为孝也,然向不在庭,遂谓之尽孝乎?真知夫事君,必披肝,必攊胆,斯为忠也,然尚□□位,遂谓之尽忠乎?
知行合一之说,更思之不能旁通,宜曰仁诸子辨之不能决也。……吁!亲当孝,我知之也,然未温凊、未定省,行孝其何时乎?力已未竭乎?君当忠,我知之也,然未服官,未立朝,尽忠其何所乎?身已未致乎?……曰:已自寒了,然寒犹在,体未衣也,岂一呼之而体遂暖乎?已自饥了,然饥犹在,腹未食也,岂一吸之而腹遂饱乎?夫苟好善也,即谓之好已行矣,而仁义未见其如何由之也,好果行乎?苟恶恶也,即谓之恶已恶矣,而私欲未见如何克之也,恶果行乎?曰知好,好了,知恶,恶了,谓为紧切工夫,盖知好,知也,好了,行也。
然知,心知之也,心好之也,内也,好之而后行;行,躬行也,外也,行仁、行义是也。
知恶,知也;恶了,行也。亦心知之也,心恶之也,内也,恶之而后行;行实践也,外也,惩忿窒欲是也。此之谓吃紧工夫。然知,知也;行,行也。岂降衷之好、之恶即行乎?岂中心好之、恶之即已乎?谈虎神色独变,知之真也。谓已自有行在,却谓之方撄虎怒、复搏虎乎?皆不得而知也,敢质之知知行者。[6]
依胡缵宗,好好色、恶恶臭,毕竟不是因好之而走近之,因恶之而远避之,故不可以说是“行”,必须有外显的举止行为方可谓之行。同样,知饥必已饥了,知寒必已寒了,这种已经“觉饥”、“觉寒”仍属于“知”,惟有“备寒与饥”,觅食、添衣方可谓之“行”。
显然,这是对阳明将“知”下移于“行”之错位用法的一个严厉批评。
而就道德行动而言,知孝、尽忠亦必有实际行动(诸如“温凊定省”、“服官立朝”)方可谓之“行”,“好善恶恶”亦必有实际的举措(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方可谓之“行”。
要之,“知”属于“心知”范畴,是“内”;“行”属于“躬行”范畴,是“外”。
“好恶”乃属于“心”之好恶,乃“降衷”之好恶、“中心”之好恶,故属于“知”,躬行实践、惩忿窒欲方属于“行”。
知行二字自有其分际,不可泯而为一。泯而为一,难免荒唐谬悠之讥:阳明知行合一之论,乃是“以一见遂为行”、“以一闻遂为行”,是“体未衣”,而“一呼之而体遂暖”;“腹未食”,而“一吸之而腹遂饱”。
在胡缵宗看来,阳明知行二字的错位使用,导致的严重后果即是以“知”为“行”,泯灭了知行之分际。章太炎在《訄书》中对知行合一论反驳说,阳明知行合一乃是把闻虎色变谓之“行”,实是以“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这跟胡缵宗批评的思路如出一辙。
这里确实涉及双方对“知”、“行”概念之界定问题,依知行分际者言,“知”乃是心理范畴之概念,举凡心中之感受乃至身体之感受,均是“知”之范围,无论是情绪性的反应如喜、怒、哀、乐、爱、恶、欲,抑或是触发、引发行动之动机、意图,尽管在身体层面已有表现(如怒形于色),只要是它尚未外显为具体的行动,那只能属于“知”的范畴。
如见到老虎感到恐惧(知恐、知惧),此是“知”,是“心之容”,而不属于“行”,惟因恐惧而逃跑,则方是“行”。
又如,孝子亲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其中,亲丧,孝子悲哀欲绝,此是“知”,而不属于“行”,惟手足着地,嚎啕大哭(匍匐而哭之),方是“行”。
如此,知“内”行“外”、知“先”行“后”,知行之间必有分际、必有间隙。
这个间隙、这个时间差乃是一“异质的时间差”,即“知”跟“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前者属于内在的心理活动范畴、认知范畴,后者属于外在的举止活动范畴,由“内”及“外”必有一先后之次第,此种先后次第乃是两种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故可称为“异质的时间差”。
阳明讲知行合一,必要挪移“知”、“行”这种分际,必改变其固有的使用界限,故有“知者行之始”命题之提出。一个行动究竟从何开始?这确实值得思考。
以亲死匍匐哭之这一行动为例,见亲丧,悲哀志懣,捶胸顿脚,放声大哭,固是行动,但见亲丧,悲痛欲绝,手足无措,是不是行动呢?在“知”、“行”之间真的存在一严格之界限,逾此界限曰“行”,在此界限内则曰“知”?强忍悲愤(这完全是内心活动)是“知”,忍受不住而流泪连连是“行”,那么,欲哭无泪是“知”抑或是“行”?阳明还就顾东桥书中的知食、知路之比喻借力发力而辩驳说:“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
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
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倐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传习录》132:165-166)在顾东桥的质疑中,“知食乃食”、“知路乃行”,知是“认知”、“认识”义,首先要认识眼前之物是可食之物,方可以食之。
如眼前之物非可食之物,而是乌头或砒霜,自不会去食——当然有心自杀者例外。要知道天安门正南五十公里是河北固安县城,你才可以向南驱车半小时到达你所爱的地方,故“知”总是在“行”之前。
对此,阳明反驳说,人之所以要认识眼前之物是可食之物,要认识眼前的路通往天安门正南五十公里,必有一认识之动机使然,即人必先有一欲食之心、欲行之心,方起相应之认知之兴趣。
而欲食之心、欲行之心即是“意”(意愿),这个“意”还不是三心二意之“意”,而是铁心铁意之“诚意”,此“意”即是行之始。
职是之故,阳明说“知者行之始”实即“意者行之始。”阳明用作为“意”之“知”(即欲食之心、欲行之心),取代了顾东桥作为“认知”之“知”(即知食之知、知路之知),后者乃一中性之认知,此种认知虽为行动所必需,但却并不必然导致行动。
叔本华在讨论“知”( 认识)与“意”(意志)关系时曾说,意志就像是没有眼睛的瞎子,而认识则似不会走路的瘸子,认识的作用就是给意志指路,它命定是为意志服务的。
小鸟并没有什么蛋的表象,但它却会为那些蛋而筑巢,蜘蛛也没有俘获品的表象,但它会为这些俘获品结网,昆虫也没有什么预见能力,但它总是把蛋下在未来幼虫将能找到食物的地方。
因此“意志”没有“认识”也照样活动,尽管它是在盲目地活动。
认识不过是个体为维持生存的一种辅助工具而已,它是为意志服务的。人之所以有“知”,最终不过是因为他需要知,或者说人只认知他需要的。就此而论,“知食”必以“欲食”为先决条件。
有“欲食之心”方有“知食之心”。而这“欲食之心”阳明即称之为“行之始”。
需要指出的是,在朱子那里,亦可以说“诚意”是行之始——朱子曾云“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8]但格物与诚意乃是不同之两节,前者是“穷此理”环节,后者是“体此理”环节,[9]故有先后之别,而阳明直接将格物训为“格其非心”、“格君心之非”之“格”,“格”遂成“正念头”,“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传习录》7:39;137:177),格物与诚意实是同一件事,“格物”即是要诚得自家意,朱子知行先后被否定,跟阳明否定朱子的“格物”训义自有其内在之关联。
至此为止,知行合一之“知”,实是行动之动力、行动之意志(“意”),劳先生说“合一”乃就“发动处”讲,即行动是从行动的动机、动力开始的,没有纯正的动机、没有真诚的动力,道德行动就无法起始。
的确,行动跟一般的生理活动有别,行动一定是有意的活动,即有目标导向的活动,当然,在行动之中也伴有无意的活动,例如在读书这一行动之中,会伴随眨眼皮等无意的生理活动。
倘如果你有意锻炼自己能够多长时间才眨一次眼皮,那这就是行动,是有意的活动。换言之,行动一定要有目的或者说动机,没有动机、目的参与的活动很难是是行动。在这种意义上,“知”作为真切笃实之“意愿”、“动机”、“主意”,自是行动之始。
具体的行动之开展无非是进一步落实这个“意愿”、“动机”、“主意”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亦可说“行”是“知”之成。
阳明在申明自己知行合一立场时,亦反复强调,“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传习录》5:33)“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26:65)“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传习录》5:33)如是,“知”即是行动发动之开始,行动即是此知之发动之完成。然而,这不是又将“知行”看作是两件了呢?从“行之始”到“知之成”不是仍有一个“时间差”吗?当代阳明研究者通常都有此一问。
需要厘清的是,这个“时间差”有别于前述的传统朱子学所质疑的时间差(异质的时间差),它是“同质的时间差”。在“异质的时间差”中,“知”跟“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前者属于内在的心理活动范畴,后者属于外在的举止活动范畴,故先后乃是由“内”及“外”之先后,故称异质的时间差。
为阳明思想辩护的现代学者能顺着阳明的思路,坚持这样一个“异质的时间差”是不存在的,因为“知”与“行”在阳明的字典之中并不是异质的范畴,“知行的本体”原是一个,不曾间隔,“知”即是“行之始”。
但从“行之始”到“知之成”仍有一过程,有一先后关系,这也是一个时间差,只是这个时间差不再是朱子学质疑意义上的由内及外的“异质的时间差”,而是“同质的时间差”,即同一个行动,从发动到完成有一过程,行动之发动即阳明所谓“知”,行动则属于知之完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先生断定“知行合一”实是就“发动处”而论,是“根源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就发动处而论,讲根源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并且将知行合一的意义仅仅限制于这一层面,而不取“完成意义”层面,当与这里所谓的“同质的时间差”考量有关。
然而,在对王阳明知行之间存在一“同质的时间差”理解同时,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虽然“知”、“行”属于同一道德行动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可言“合一”),但它们分别描述不同的行动阶段:“知”指行动之发动端,而“行”则指发动之后的持续、完成过程。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牵于字义(“知者行之始”)的理解,这一理解既于阳明知行合一的义理说不通,又跟阳明知行合一之整体论述无法融洽,而且从工夫论角度看亦不稳妥。
就知行合一之义理而论,阳明讲“知”是“行”之始时,“知”即是一种有强烈要实现自身的内驱力、意志力,是发起行动的动力,而不是泛泛的“认知”之“知”,此劳先生于其书中反复致意的,问题是,这种“知行的本体”(实即是“良知”)之自我实现的力量是不是只是限定在行动的开端处?仅仅是行动发动之“根源”?抑或复又是一种如决河注海沛然莫之能御之力量而贯穿于整个道德行动之始终?
阳明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真切笃实”即是“诚”的意思,亦可以说是“意之诚”。此真切笃实之知(“意之诚”)必有一自不容已的力量实现其自身,我们不妨再看另外一处阳明对“欲行之心”的说法:“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为所归宿之地,犹所谓至善也。
行道者不辞险阻,决意向前,犹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识大都所在,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北走胡几希矣。’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辞险阻艰难,决意向前,别为存心,未免牵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
夫不辞险阻艰难,决意向前,此正是诚意之意。审如是,则其所以问道途,具资斧,戒舟车,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为决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识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则亦欲往而已,未尝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尝真往,是以道途之不问,资斧之不具,舟车之不戒。
若决意向前,则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10]这里,“决意向前”就是“欲行之心”,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即是“意之诚”,问好道路、知道行路方向(“问道途”)、准备好盘缠(“具资斧”)、预备好交通工具(“戒舟车”),这一系列落实行动的条件,自会在“决意向前” (“欲行之心”)的驱动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个决意向前的意志始终贯彻于整个到大都的行程之中,否则,或临歧彷徨,误入歧途,或半途而废。
“知者,行之始”,是说这个“知”决意要实现它自己,故是行动之开始,是“行的主意”;“行者,知之成”,是说这个决意要实现它自己的“知”最终实现了它自己,故“行”又可说是“知之成”,是“知的工夫”。
行之始,不是说“知”只是“行之始”这个环节上存在;知之成,也不是说“行”只是在这个“知之成”环节上存在。
知行乃是同一行动的两个向度(dimensions): “知”字彰显行动之意志力以及明察力(详下),“行”字彰显行动之展示与落实,这两个向度本是“一体两面”,这个一体两面乃存在于从行动之发动到行动之完成这一完整的过程之中。
没有这种内驱力、意志力的贯穿始终,或者说这种内驱力仅限于行动之始,那就很难抵制私意的牵引,而只能落入“知而不行”或“行之不远”的窠臼之中。
而就阳明知行合一整体论述看,阳明尚说过,“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5:33) 如将知行“固化”为同一行动的两个不同阶段,则于阳明这一说法已明显抵牾。
“知者,行之始”,其本义即是“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行者,知之成”,其本义即是“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换言之,知行的本体是不可分的,这个不可分绝不只是在根源意义上不可分,而且也是在整个行动过程之中不可分。一分开,知陷入知而不行,行即沦为冥行妄作。所以阳明在“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句之后,接着便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传习录》133:166)此明确表明离开“知”之“行”,与离开“行”之“知”,均非“知行的本体”。
知行之“合一”乃是体现于从行动之发动到行动之完成这一整体过程之中的。
阳明反复强调“行”不是“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不然,便是“冥行妄作”,故“行”始终又是“思惟省察”、“精察明觉”下的“行”。
在阳明那里,行动之“发动”的“根源”在于“意”(所谓“主宰发动是意”),“发动之明觉”是“知”。
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是行、“知”者行之始,两处“知”字实是“意”的意思,“知”字侧重于“主宰发动”这一“根源意义”,而且这一主宰发动的内驱力、意志力作为“根源”复又盎然流行于整个行动之“枝节”、“末梢”,“根源”作为行动之“本”与作为具体的行动之“末”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就此而论,“根源意义”之合一必亦是“完成意义”之合一;说行之明觉精察处是“知”,此“知”字实是“详审精察”的意思,“知”字侧重于“发动之明觉”这一“照察意义”。
[11]在意念由发动至展开而成为行为之整个历程之中,这个详审精察意义上的“知”始终跟“主宰发动”(根源意义)所开显的实际行动是一体而在的,现时地照察行动之每一环节,确保行动不受任何干扰而“自住不得”、“自不容已”地实现其自己:“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12]这说明知行合一之“合一”在“根源意义”、“完成意义”之外,尚具有“明觉”与“行动”一体而在的“照察意义”。
这一照察意义大致可从两方面把握:(1)行动因为有此始终如一的照察,故不会陷入冥行妄作之中,如行去大都,因有“知”之照察,故会问道途、具资斧、戒舟车,而不至于南辕北辙,半途而废。
(2)行动因为有此始终如一的照察,故会对行动过程之中出现的任何畏难情绪、放弃的念头(所谓私欲)、“躐等”、“欲速”的念头(这亦是私欲)当即觉察,并如洪炉点雪一样化掉一切干扰行动的私心杂念。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原本即是一“教法”、一工夫论命题(《传习录》165:234),他反复强调“知行工夫”、“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故对知行合一之理解不应有悖于阳明这一“一个工夫”之修身路径。“一个工夫”是针对朱子学的“知先行后”的两个工夫[13]而立论的: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传习录》5:34)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又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体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体亦原是如此。”[14]
前一段文字标举知行合一立言宗旨,它是针对将知、行视为截然两段,以为知就是知,行就是行,且必先知而后行这一看法而立论的,在阳明看来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其弊则会导致“行”之无限的延宕,导致“等一会”、“下一次”的拖延行为。
明明知道日攘一鸡乃不道德行为,却说,好吧,这个道理我还未彻底弄明白,先月攘一鸡,等到道理清楚一些了,再年攘一鸡。
或者干脆说,攘鸡的道理太难理解了,这要一辈子才能弄清楚,这正应了阳明“遂终身不行”那句话。后一段文字则是阐明知行工夫乃是用两个字(知、行)说同一个工夫之精义:通常人们想当然认为“知”侧重于“明觉精察”(“明”、“智”),“行”侧重于“真切笃实”(“诚”、“仁”),殊不知明诚、仁智实为一体两面,“知”时亦有真切笃实之工夫(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行”时亦有明觉精察工夫(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行二字乃是构成完整的修身工夫之不可或缺的向度,是同一修身工夫之本质性的、构成性的要素。在行动开端是如此,在行动过程是如此,在行动之完成亦是如此。将“知行合一”的意义只是限定在“根源意义”上面,从阳明“一个工夫”的说法看,也是不稳妥的。
要之,传统朱子学立场坚持知行之间乃存在一由“内”及“外”的“异质的时间差”,劳思光先生认为由于阳明将知、行做了重新界定,“知”是价值之知,是行之发动,故知行合一只能是“根源意义”上的合一。
这一看法实际上是认定知行乃是同一行动之不同阶段,知行之间仍然存在一“同质的时间差”。
笔者依次从知行合一的义理、知行合一的整体论述以及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工夫论说三个方面,阐述将知行合一限定在“根源意义”上之不妥。在根本上,知行合一既是“主宰发动”这一“根源意义”上的合一,而且这个主宰发动之为一种要求实现自身的内驱力、意志力,实贯穿于整个道德行动之始终,就此而言,它亦是“完成意义”上的合一。
“知”作为“发动之明觉”所拥有的“详审精察”的能力,又始终跟整个道德行动一体而在,故知行又具有这一即行即察的“照察意义”上的合一。
而就“知行”之一元工夫而论,知时自有行的工夫,行时亦自有知的工夫,知行合一之工夫乃是贯彻于整个修身活动之始终的。一言以蔽之,知行并非同一行动之两个不同的时间段,而是同一行动之两个不同面向(一体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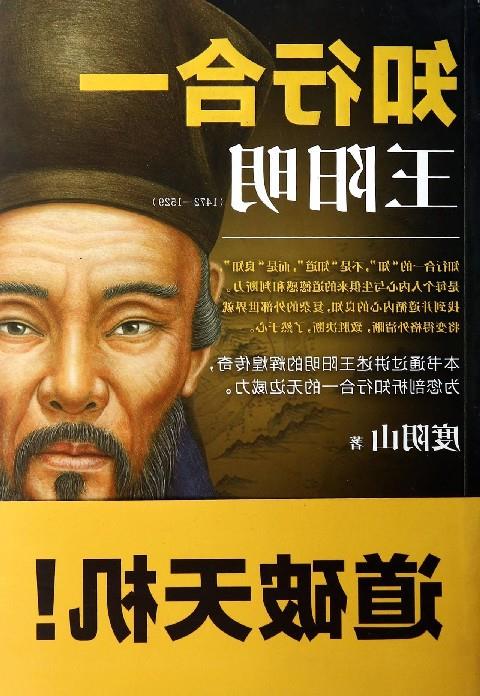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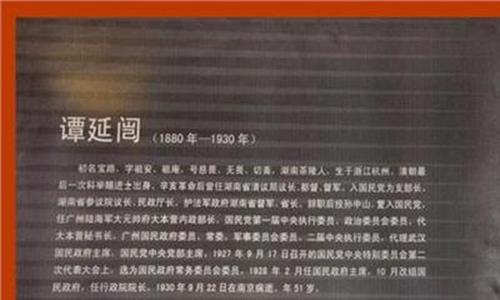





![>王阳明心学智慧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三册)[当当]](https://pic.bilezu.com/upload/c/75/c753a16bd3ff1be068f61ad7ff19b2f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