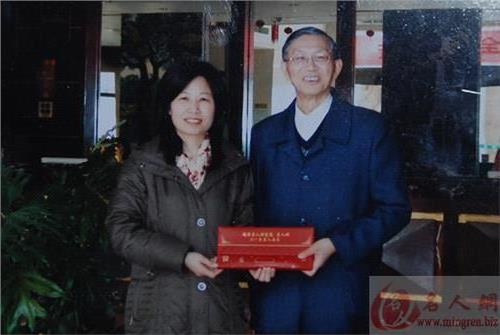于萍拜访安福三杰罗隆基、彭文应后代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1946年,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曾征询他的意见:民盟能否先参加政府,新政府调停内战后,再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他告诉将军: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内战不停止,共产党决不会参加政府。这一点是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不是我、也不是民盟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改变的!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当“和谈”破裂、国共两党决意兵戎相见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共驻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的办事机构必须在1947年3月5日前撤离。次日,各报便登出了一则《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
内称:“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上开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随即,民盟总部迁入南京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和35号办公,罗隆基本人及周新民、李文宜先生还搬进这里居住。在上海,民盟同时进驻马思南路原周公馆,作为民盟总部的上海办事处。
当文明被打落在野蛮的沼泽地时,你就不要指望那些最懂方块字的端庄、严谨与美妙的人们的嘴里,能再吐出金玉与珠玑来。罗隆基成为“右派”后,香港曾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也答应他香港和美国都可以去,并说罗隆基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1949年以后,罗隆基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他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那时已不如二三十年代纯粹,但基本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样子。进入50年代后,他成了一个政府官员,还有许多社会性的兼职,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常务委员兼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1953年后,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章伯钧一起实际上成为民盟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现在很少能见到有关罗隆基在50年代初思想的历史资料,但从有限的史料中能够发现他那时不是很愉快。以罗隆基的才能,40年代末人们看好他的前程,英国承认了中国以后,他的朋友吕孝信就听人说过,罗隆基有可能出任驻英大使。因为以罗隆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辩才都来的长处,这种传说也是有些影子的。
1949年初,当时驻上海的美国领事齐艾斯曾半开玩笑地问过罗隆基:“将来你在联合政府里能不能做外交部长?”罗当时大笑说:“恐无此可能。”齐艾斯接着说:“我们希望你能做外交部长,中美关系不致中断,我还能留在这里。”(叶笃义《我与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41页)罗隆基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可以做外长或驻外大使,只是人们觉得他那么好的教育背景和个人才能,不到那样的位置上,实在是委屈了他……
50年代初期,罗隆基可能已经感到了一点不适应,1950年民盟中央召开第四次委员会,内部争论很激烈,主要是章伯钧和罗隆基有矛盾,据千家驹回忆:“会开了一个多月,开不下去,后经周恩来出面调解,仍未解决。最后竟劳毛泽东亲自出面,找我们大家商谈,双方才算勉强妥协(毛泽东与周恩来两次调解的会,我都参加了)。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39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他们那时的情况可能也加深了毛泽东对民盟的不好印象。
1957年里,民盟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比例最高的,当时流传上面一句话:“最坏是民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79年10月,胡愈之在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说:“民盟盟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六千余人之多,约占当时盟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上册第78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民盟中央委员会中被划右派的占了29%,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43%,在中央常委中则占了36%以上。”(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74页,学习杂志社)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1957年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
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