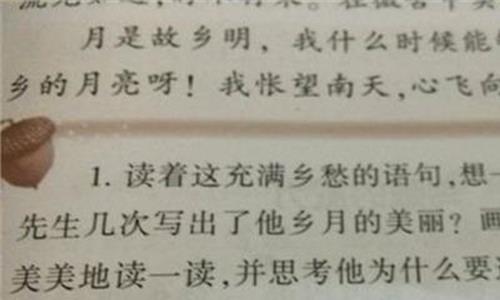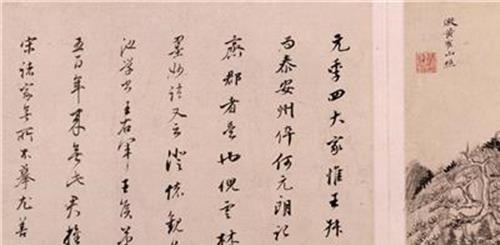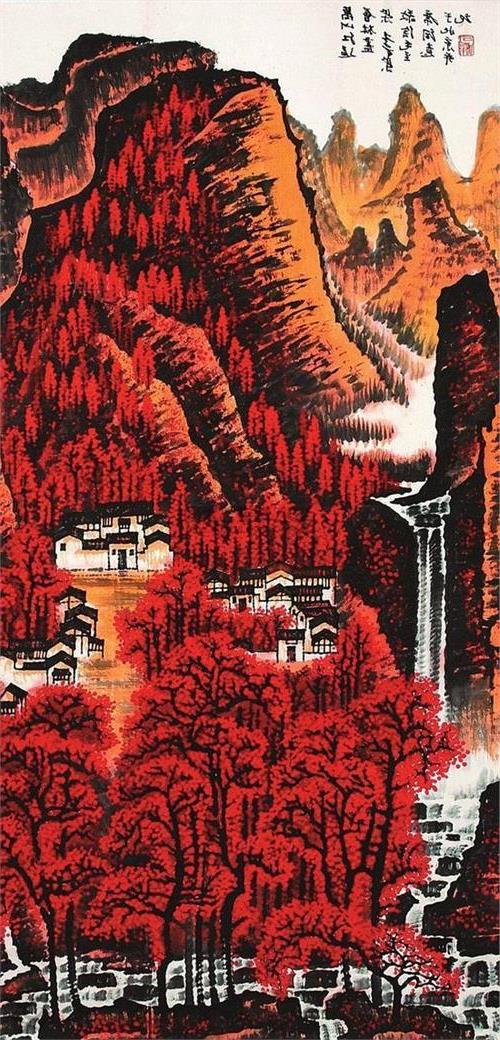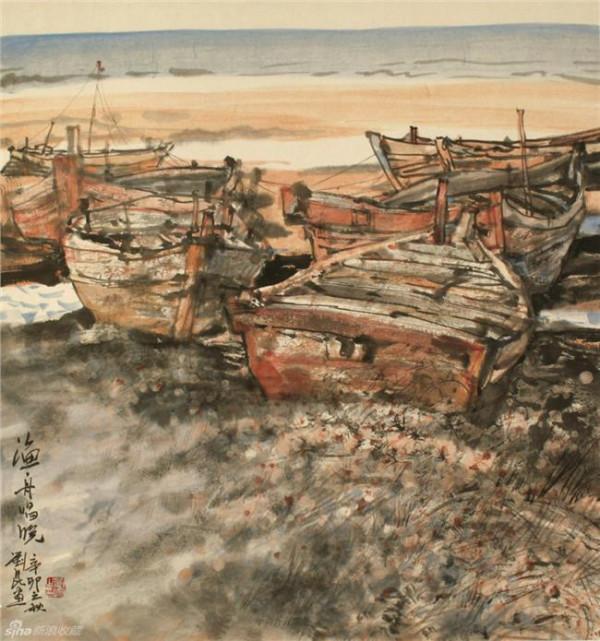王水照作品 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
此二王本杜集,实为后世流传的各种杜集之所从出,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明代大藏书家毛晋曾经寓目,惜原本已佚,但毛氏的宋椠补抄本今尚存于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先生曾以九十一岁高龄亲自主持编印工作,将其列入《续古逸丛书》的第四十七种。了解其背后的这段出版曲折,读该书时更觉意味无穷。
另一部柳集之祖,即穆修刻印的本子,就没有如此圆满的商业运作了。穆修刻售柳集事,最早见于杨亿口述的《杨文公谈苑》,该书记穆修事云:
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详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18)
此段文字又见于《东轩笔录》卷三,亦说“募工镂版,印数百帙……自是经年不售一部”(19)。而《曲洧旧闻》卷四云:“(穆修)始得韩、柳善本,大喜。……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20)则刻售者不止柳集,还包括韩集(21)。苏舜钦《哀穆先生文》云:“后得柳子厚文,刻货之,值售者甚少,逾年积得百缗。”(22)所记情况小有出入。
宋时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及书院刻等不同。一般而言,官刻较为精良,坊刻良莠不齐,但均有各自的销售渠道,书院亦有从学士子的固定购买群体,而个人自刻自售就有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了。穆修是位学者,个性又较怪戾,销售不够理想,自可理解。
《杨文公谈苑》等说是“经年不售一部”,不免有点夸张;苏舜钦说卖了一年,“积得百缗”之数。如果原来的印数如《杨文公谈苑》等所言之“数百帙”,那么每部价格也在一缗(一千文)上下,与上述王琪刻印的杜集相埒。
看来穆修尽管运作乏术,还是做到保本有余的。这说明宋时图书市场的广大、活跃,对书籍需求量的众多,当然也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发展的迅猛势头。今《柳河东集》载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谓:他在政和四年(1114)重编柳集,所据底本有四,其中一种“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最为贵重(23)。
穆修当年在汴京大相国寺出售不利的柳集,成为今日流传最广的柳集祖本之一。
宋以前雕版印刷术尚不大发达,且所印大都为日历、佛经、字书,至宋开始形成规模化产业,结束了以写本为主的流传阶段。文学作品的刻印和买卖是一种经由市场渠道的商业传播,极大地促进了诗文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和流通速度;文学作品之成为商品,融入宋代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之中,其发展和初步成熟,应是宋代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一个标志。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印本代替写本,直接影响了宋代士人的读书生活。读书是读书人取得自身社会资格的依据,而宋代读书人凭借雕版印刷术的发达,使博览群书不再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士人社会的平均知识量远迈前人。我们翻阅现今尚存的近五百部宋人别集,明显地感到其内容之广博,信息之丰盈,知识之密集,在唐人别集中就颇为罕见。
宋罗璧《罗氏识遗》卷一“成书得书难”条云:“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
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24)这一“何其幸也”的感叹一直传响到后代。元人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中说:“宋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
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尝有与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书弥多而弥易,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25)宋代士人家藏典籍的丰富,前人望尘莫及,引起宋人的自豪。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载:“曩时儒生中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纵得本而力不能缮写。今士庶家藏典籍者多矣,乃儒者逢时之幸也。”(26)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前集卷一亦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
”(27)印本的广泛流传的确避免了“耳受之艰”和“手抄之勤”的辛苦,大大改善了读书条件,这为宋代士人综合型人才的大量涌现,宋代文学中“学者化”倾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印本与写本并存,印本逐渐取代写本的过渡时期,尽管印本已显示出印刷方便、传播便捷的巨大优势,但宋代士人在观念上仍保持重写本、轻印本的倾向。他们把写本称作“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28)而印本广泛流传后,“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印本代替写本,改变了士人们的传统阅读习惯和方式,并产生了“诵读灭裂”的流弊。面对印本的蓬勃盛况,苏轼的思考与忧虑更深。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士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29)
苏轼指出,秦汉以后,纸代替简帛,书籍益多而学风日益“苟简”;入宋以来,印本代替写本,书籍更为易得,士子们反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改变了老辈们“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的刻苦攻读之风。苏轼的思考与忧虑代表了北宋部分士人排拒印本的共同心理,与上述对印本称“幸”的言论恰成对照,两者相反相成,见出人们面对印本这一新生事物时的矛盾态度。
苏轼、叶梦得指出了因印本流行带来了士子“束书不观”和“诵读灭裂”的负面作用,更多的士人关心的是印本比之写本更易产生文本讹舛的弊端。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已指出:“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原因是:“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30)一般说来,文本的准确度,印本不如写本(藏本即是写本);而福建“麻沙本”更被人们所诟病,斥责之声指不胜屈。
周{J2R904.jpg}《清波杂志》卷八“板本讹舛”条,在指出葛立方《韵语阳秋》把一首苏轼诗误作杜甫诗后,感叹道:“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3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记载一则趣闻:“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趋前质疑,教官不悟此题有错字,却强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官大惭(32)。这两则资料并没有具体指明麻沙本的什么错误,却明确无误地把麻沙本作为“劣本”的同义词,麻沙本的信誉实在不佳。
面对印本取代写本的客观情势,宋代士人所作的上述两点优劣比较,都体现出重写本、轻印本的价值取向,但其所包含的意蕴是各不相同的。以抄书为读书,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相传千余年的阅读状态,这种传统习惯甚至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
穆修、欧阳修所读韩愈作品,都各有依据旧本而不断校读、亲手抄录、历数十年而不辍终成之“善本”,他们的研读过程就是抄校过程。即使在明清以后,士人们仍然保持以抄书为读书的阅读习惯,并深受其益。顾炎武就秉承嗣祖顾绍芾的主张,倡言“著书不如抄书”,且身体力行,在四方游学之际,“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33)。
这一传统读书方法即能精读细读,有助于学子对文本的沉潜玩味、倾力求索而达到深入把握之境。苏轼等人的思考与忧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说印本流行造成了士人“束书不观”却有偏颇,两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联,实出于面对新兴的书籍形态的一种逆反心理。
至于对麻沙本等坊本的指责,事实显然,毋庸回护;但从商品经济职能等角度来观察,这些指责就有违历史公正了。官刻、私刻、坊刻和书院刻,构成了宋代书业市场的商品构架和体系,它们各自承担着相应的供需职能,适应不同层次人士的不同需求。
叶梦得说:“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34)“易成”必然导致多误,然而非“易成”又不能“几遍天下”,满足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从商业传播的辐射广度和出版速度来衡量,坊本的重要性实远胜官刻本之上。
坊间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制作、经销、发行的机制,拥有稳定的出版商、经营商和印刷工人群体,积累了世代相传的、长期的运营经验,因而它处于图书市场的强势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又有彼此互补的功效。
坊刻本的字句讹误、底本不精、印制粗糙是一目了然的,但它不仅以生产便捷、价格低廉争夺市场,而且在内容上或另觅底本、别出新招,或重新编排、出奇制胜,即便在文献版本学中也具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一笔抹煞。
请以现存麻沙本宋集的实物为依据,申说对其所受到的众口一词的指责,应该有所修正。
宋时福建麻沙镇曾以“类编”、“增广”、“大全文集”为书名,编刻、印行多种名家文集,现尚存《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今藏国家图书馆)、《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今藏日本内阁文库)、《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于刻于蕲州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今藏日本内阁文库),亦属同一类型。
苏轼集也有麻沙“大全集”本,惜今已佚。这些“类编”、“增广”、“大全文集”的名目,带有书贾射利的广告色彩。
一般说来,刊刻欠精,历来著名书目很少著录,有的还故弄狡狯,滥冒卷数,如《颍滨集》中竟有五处以一卷冒充两卷、五卷、十一卷、十二卷、十四卷者(见卷八一至八二、卷四六至五○、卷二六至三六、卷一○至二一、卷六七至八○),显不足取。
《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有牌记云:“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镵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此类书或确是书商访得之别本,或只是书商自行编纂,招徕读者。
但既然求“增”求“广”,并予分类,则搜讨必有出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实不能一概以“劣本”、“赝本”视之。如此种黄庭坚集,比之现通行之《豫章黄先生文集》即《内集》及《外集》、《别集》等,不仅篇目有逸出者,而且可校正通行三集本文字之讹(35)。《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中新发现的司马光《日记》,更是轰动学界的重大收获(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