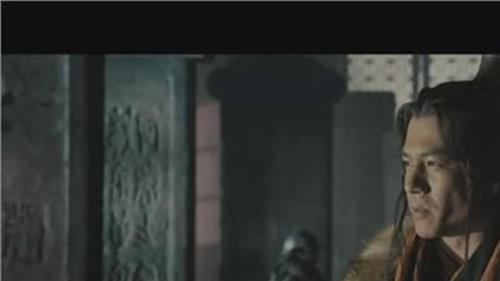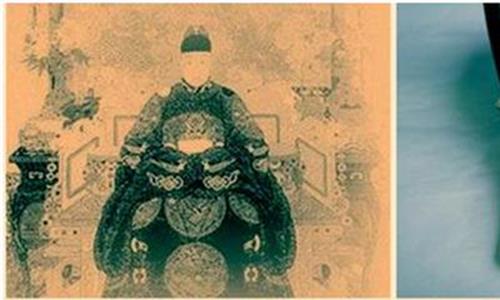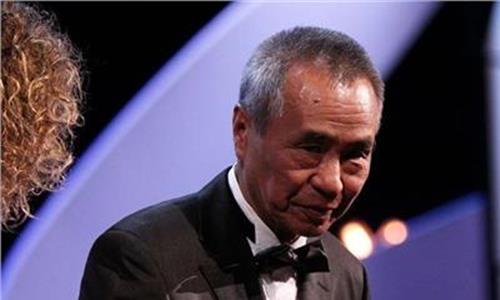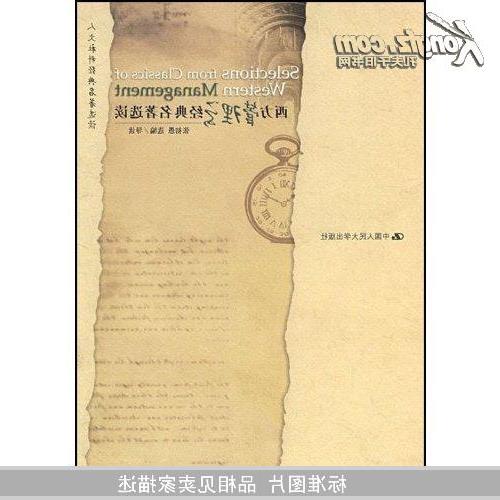怎么评价侯孝贤 侯孝贤:你们怎么评论 跟我毫不相干
大陆、香港、台湾,这三个华语地区从近代起就承袭了中国文化的不同剖面,到了现代已自成风格,早已无法用一个笼统概念简单归纳。其中经历了日据和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则要更加封闭和复杂,故而提到它时,常常抹掉它的地域特色,将其视为 " 中国传统文化 " 的储物柜。

对台湾文化产生好奇,大概要从开始看白先勇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白先勇在提倡 " 自由主义文艺 " 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他便置身于文化先峰的前线,并在华语文坛占据了的重要地位。

那个时代的台湾岛内,如同被台风席卷过一遍。国民党威权主义的高度监管开始出现裂缝,由于时局的现实,文化已然越过政治当局,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官方的外交角色。其中,真正的文化先峰是文学,由此引发的乡土运动蔓延到电影领域,而提到台湾电影,绕不过去的人便是侯孝贤。
侯孝贤
市面上分析侯孝贤的作品不少,但能够全景式扫描格局,既准确锁定历史、政治、经济和电影工业中促成 " 侯氏风格 " 的关键,使被复杂政治和文化旋涡绞缠的台湾电影被有序拆解,又引入文化分析的严格考据,将镜头、构图和布光做技术分析和数据对比的,James Udden 的这本《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可谓一枝独秀。
要对一个已经被分析得拆筋见骨的人有所挖掘,实属不易。要么在补充了新材料后拆解重组,要么跳离至另一个领域,从全新的架构里去看出些新意。
作者: [ 美 ] 詹姆斯 · 乌登。曾任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现为葛底斯堡学院电影研究副教授。长期研究台湾电影与亚洲电影。为完成本书,赴台居住多年,多次深入采访侯孝贤及其合作伙伴。
正如本书开门见山所言:没有电影人是单打独斗的,对于深入研究他们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个案研究的困难在于将个体相关的事实恰到好处地取舍梳理,陈列各方意见;可以浸入作品诞生的微环境,亦可退开一段文化和时空的距离。Udden 不满将侯孝贤等同于 " 传统中国文化 " 或 " 儒家文化 " 的通常看法,认为这是一种出于省事的粗糙和符合民族计划的政治企图。
评论家常以几个导演来划分时代,而一个导演的作品则可以用拍摄手法或主题为标准,分为不同阶段。这种改变并不总能令观众满意,但它记录了一种真实:一种环境或个人总是处于变化中的真实。
上世纪后半页的台湾局势,政治及其辐射的一系列社会现实,是引起侯孝贤电影变化的最常见因素。Udden 在分析侯孝贤电影的美学风格时,自然也不能离开对这些事实的考据。
长镜头、静止摄像机、空镜几乎已被等同于侯孝贤的个人标签,特别是擅长用长镜头来传达历史经验这点更是成为 " 侯氏美学 " 的代表。这到底是全然归功于天赋,还是和更复杂的外因密不可分?Udden 通过数据的确凿 " 证据 ",将其和历史上同样喜好运用长镜头处理历史的导演们交叉对比,从拍摄条件、电影工业和作者经验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让艺术不再浮于半空,少了些大师的神话,多了份特定环境下电影人的无奈。
作者: [ 美 ] 白睿文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
学与电影博士。《煮海时光》按创作年序,收录了侯导从影四十年来,每一部作品台前幕后的珍贵回忆。
所有精神的创作,物质是不可绕过的首要条件。这个事实听上去毫不浪漫。
六十年代的台湾,赋税高、政策忽视、生胶片缺乏、港片的冲击,加上不断变温的政治环境,电影发展一直举步维艰。设备缺乏导致机位单一、布光过硬;生胶昂贵,剪辑片比是导演在拍摄时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便自然造成了表演僵硬和剪辑混乱。
七十年代,台湾电影在港片的冲击下再次衰落,论质量和种类,前者都毫无还手余地。人们常常讶异台湾电影中文艺片占比之多,认为这源于儒家文化的独特气韵——但背后原因其实讽刺:相较于动作片,文艺片的制作成本要廉价许多。这就是所谓 " 气韵 " 最无可奈何的现实状况。
《海上花》的美学特点非常醒目,摇曳的煤油灯、精致的服装和布景,的确非常中国化,尤其是长镜头的运用,是过去故事片历史上平均时间最长的影片之一。这部并非体现台湾文化的作品,是一个现代的台湾人对于一百年前古老中国的想象和臆测。
六七十年代台湾电影面临的难题在 80 年代的 " 新电影运动 " 中依旧难以回避。
亲历过行业窘境的侯孝贤在七十年代进入电影行业后迅速成为副导演,作为金贵胶片的直接负责人,他直观地感受到限制胶片对于拍摄的局限。八十年代初,当他有机会和陈坤厚一同开启 " 新电影实践 " 时,他便试图跳脱这种节省胶片的拍摄局限,特别是当表演者皆是非演员时,镜头时间的延长可以更好的捕捉到他们最真实的表现。
所以,那些被文艺青年追捧的 " 诗意长镜头 " 的出现其实并不浪漫,它是侯孝贤对早期商业岁月的反叛。
长镜头给于表演者更充足的展示时间,而固定镜头则是侯孝贤对于疏离感的保留。就如侯孝贤所说:所有的风格是为特定的叙事而服务的——这样的镜头语言尤其合衬历史的叙事方式。固定焦段和静止镜头,就像上帝在看这个世界,平平地将面前的事物扫视一遍," 可以尽量客观,不太有什么激动、情绪在里面,这样看得很清楚,会超过当时拍这件事情的想法。"
80 年代,台湾解严,侯孝贤拍摄了 " 台湾历史三部曲 "。其中,《悲情城市》是侯孝贤作品中最受瞩目的一部,于 1989 年在台湾上映,并获第 46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以二 · 二八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林氏家族兄弟四人的遭遇和生活。
作为西方学者,Udden 的视角天然有来自另一个文化体系的客观。全文的落脚点即是现代化的世界里,东西方文化之间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如同近代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岛本身,政治和社会皆动荡不安,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早就鱼龙混杂一锅粥," 永恒价值 " 的文化并不存在,相反他们不介意文化杂质,他们有着强韧的适应性和敏锐的灵活性。这种适应性下,台湾自成一派的 " 传统中国文化变体 " 要更混合,也更有活力。
《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从个人或家族的角度出发,构成了台湾历史的编年:日据、光复和白色恐怖。处理这样厚重的主题时,侯孝贤选择和真相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启发最直接的来源是沈从文的自传。一个经历了战争、逃荒和文革的人,他虽然描绘的是人在这个世界里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但他是以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在观看。这种角度被侯孝贤用到了电影里,对电影的情感从直觉慢慢变成自觉。
2015 年,68 岁的戛纳电影节把 " 最佳导演奖 " 颁给了与之同岁的侯孝贤。站在领奖台上,侯导点名感谢了 3 个人,第 3 位便是朱天文。从《小毕的故事》开始,朱天文是和侯孝贤合作次数最多的编剧,其中《悲情城市》还斩获第 46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文化对社会的刺激远不如政治事件,但效力却更长久。拿《悲情城市》为例,尽管有人一直试图将其精简成一个政治符号,但这部作品中家族才是舞台上的主角,政治是避而不谈的暗涌。
" 我通常不会去正拍历史,而是致力于营造历史是一个氛围,透过最小的人物来表达。"缺乏电影工业,无法造景,如果是刻板反映政治,很多东西早就无从拍起," 我的角度就是人和一个家庭,二二八是早就知道的,而我更想拍一个时代变迁政权交替时,家庭的变化。如同一个平常百姓,在事情发展中逐渐有自己的判断,而非从一开始就做出价值预设," 起先是直觉,慢慢变成自觉。"
《悲情城市》的发行和上映前前后后都有着非常负责的背景。解严后的第二年侯孝贤便拍摄了它,绕过台湾当局直接从日本送往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成为首次斩获金奖的台湾电影。这个奖成了《悲情城市》的特赦令。其中关于长镜头、吃饭、空镜的运用更是侯孝贤风格的集中体现。
台湾的 20 世纪," 二二八 " 这样的政治骤变屡见不鲜,发生当下的确会产生巨大的张力,却终究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消散。如果电影只是如政宣片一样直面记录或发泄情绪,也必会很快一同沉入历史的箱底。
每个时代的意志和氛围都是不同的,而其中的人的处境和生存都有动人之处。时隔二十多年在一个社会漩涡里,回望之前的漩涡,侯孝贤想要的并不单单是记录一个历史事件," 所以我选在站在人的角度,就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去看他的一生,尽量客观地来看他所见证的时代变化。"
侯孝贤与《悲情城市》摄影师陈怀恩。侯孝贤早期使用非演员表演,这锻炼了他的现场调度能力,长镜头也给了他们充足的表演空间。随机应变和对场景的敏锐度,是那个时代客观条件对导演的限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Udden 在这本书中运用的文化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学术方法,于是在一开始便要弄清何为 " 中国传统文化 " 便尤为重要。
对中国文化的根本误解是以为它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母本,实际上先秦、隋唐、元明清,所谓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有着各种断裂和融合。到了近代,中国本土、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侨的 " 传统文化 " 起码有四种,且各成体系。
Udden 分析侯孝贤电影的阶段变化、标签形成、在国际影展乃至泛亚风格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便是为了反驳 " 传统中国文化 "、" 儒家文化 " 大而空的概况。不可否认," 文革 " 中失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得到很大程度的保存,过去的文化的确是台湾今天的一部分,但它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长出了新的枝芽,成为一个全新的版本,这些线索在文化各个领域存在,只是有人懒于搜集,有人避免承认。
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陈国富、詹宏志《恋恋风尘》是吴念真根据亲身经历编写的剧本。詹宏志是个对于侯孝贤与杨德昌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人,他促成了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及《戏梦人生》,可以说,没有了詹宏志,台湾的文化生态还真是欠缺了一点什么。他也曾对侯杨两人的风格有非常精准的评价:杨德昌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变的地方,侯孝贤看的是这个世界不变的地方。
接下来的篇幅里,Udden 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只以全景式扫描了他所有作品并辅以历史考据,以 90 年代末为节点,笔墨重点放在了他前期的作品。但在对《悲情城市》的历史或《海上花》的美学这般落到具体的逐帧分析时,Udden 通过给出数据采样,从专业角度抽丝剥茧,解构侯孝贤的 " 中国化 ",给每一种看似无解的问题一个出处,发现了一个总是处在中国本土文化阴影下,却早已脱胎的另一个更复杂、也更具可能性的新版本,此番细节已可见功力。
《最好的时光》好像是侯孝贤用片段的方式对过往的作品来了个大合集。" 恋爱梦 " 可以对应《恋恋风尘》、" 自由梦 " 对应《海上花》、" 青春梦 " 对应《千禧曼波》。被人家贴上标签的创作者总是在不断试图找到突破的出口,比如 2015 年首次尝试武侠题材,但依旧让人一眼认出 " 这是侯孝贤 " 的《刺客聂隐娘》。
《看电影》杂志在 09 年时曾做过一期 " 台湾电影 110 年 " 的特辑,钮承泽在接受访问时说道:没有一个人拍的所有作品都好看。
创作生涯必然存在多个节点,每个不同的时期总会出现戏剧性的不同,止步于 " 风格 " 或 " 个人美学 " 的坚守未免太过保守,如果一个导演可以被一种风格界定,那么他要么早已转行,要么停滞不前。
Udden 发现,当侯孝贤在 " 历史三部曲 " 后,随着主题和想法的转变开始改变标志的静止摄影机时,这种风格却被其他亚洲导演直接继承了下来,比如台湾的蔡明亮,韩国的洪尚秀,还有大陆的贾樟柯,事实上,侯孝贤的影响在亚洲电影中无处不在,甚至成为一种 " 泛亚风格 "。这种现象对于一个西方学者来说,意义不止于美学,更可以扩展到全文化领域,证明了亚洲在现代化进程中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适应性。
在新世纪开始至今的《千禧曼波》、《咖啡时光》、《最好的时光》、《红气球之旅》和《刺客聂隐娘》5 部作品,侯孝贤在以更慢的速度创作,并更加随意的运用镜头语言,除了依旧忠于胶片外,镜头时长、静止摄影这些标志性风格他都在改变,因为风格从来不是目标本身。
结合这个时代飞速的发展,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台湾文化,在世界文化壁垒被不断打破的未来,混合后的人类文化将以全新的方式出现。而不论何时,这些被封存在胶片中关于过往的回忆,和所有值得探寻的剖面都在彰显着处于其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