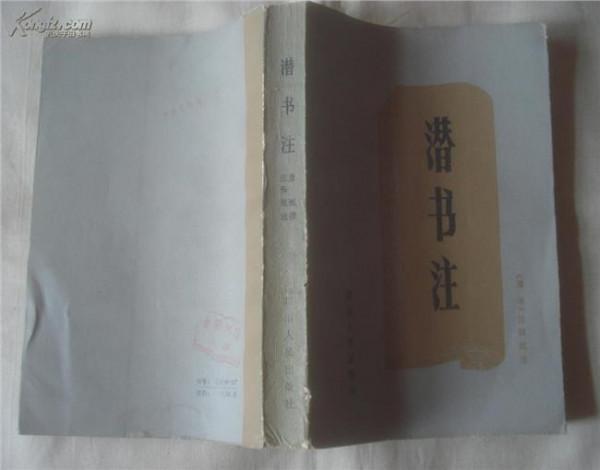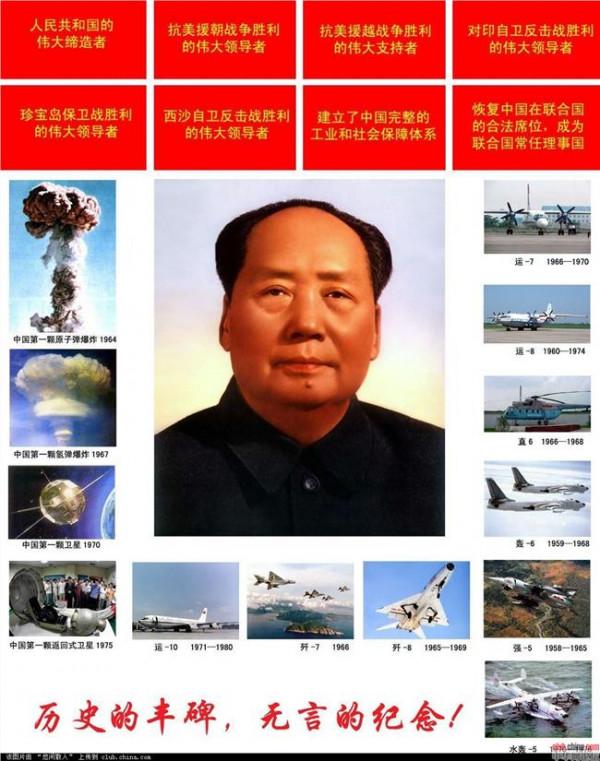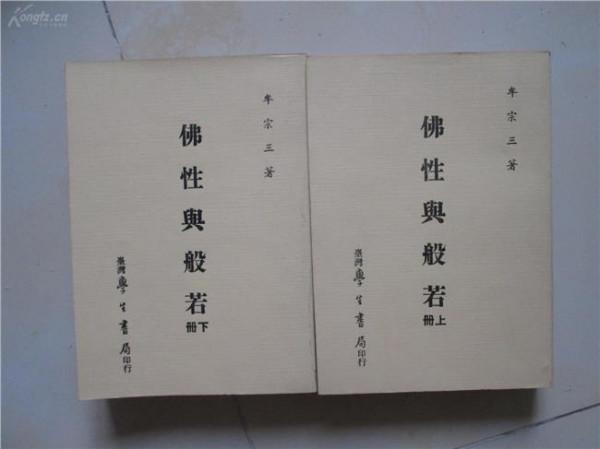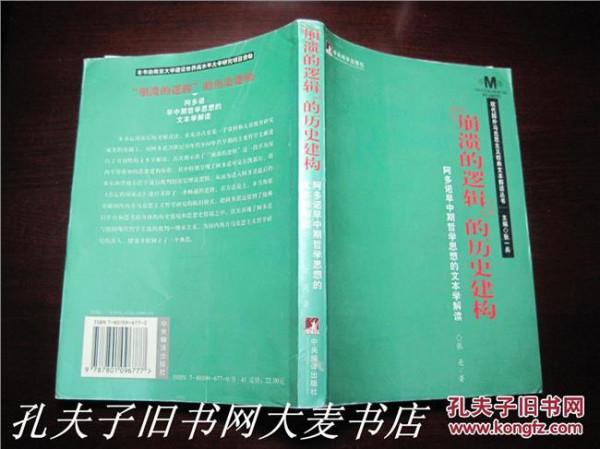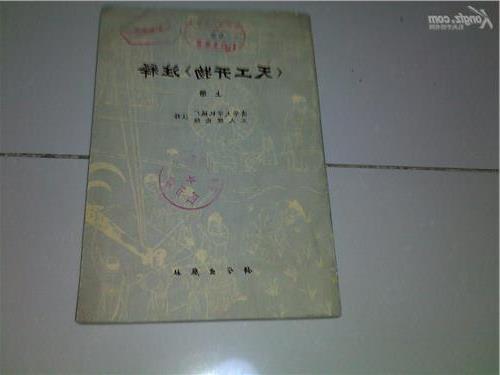方以智思想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
方以智生于1611年,卒于1671年,桐城人。他是明末复社领袖之一、政治活动家,自负要提三尺剑,纠集志士,改造黑暗世界;也是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烹炮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即所谓“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

关于方以智的进步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我们曾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作过概括的论述。在这里,仅对近年因编方以智全集而发现的他的一部富于哲学思想的著作《东西均》作一简要的评述。
《东西均》是方以智的未刊稿之一,初稿写于1652年,又在1653年加以订正。它是一部集中的有体系的哲学著作,其中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是颇光辉的。同时,它又充满着相当正确的对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以及对唯心主义和神学的严肃的战斗精神。关于后者,在这里暂不具述。
方以智在《东西均》的《开章》中,首先解释什么叫做“东西”,什么叫做“均”。他引证训诂学的论据说:“古呼物为‘东西’,至今犹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这样看来,物本身就包含着正反两面。“均”古与“钧”、“韵”等通为一字,是指旋转的陶钧,也是指调节编钟大小清浊的器具均钟,所以“均”有统一两端而运转的意思。
因此,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也就是他所说的“所以”,如果用近代语表述,书名是《物质的转变》。
方以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有和笛卡儿相似之处,是火的一元论。这在他的著作中是经常可见的,如《物理小识》卷一说:“天恒动,人生亦恒动,皆火之为也。”有时他用气吹万物而动之说,说“无始两间皆气”、“气者天也”或“物即是天”,也表现为气或物质的一元论,因此说“天与火同”,把气、火两者等同起来。
他指出“运动皆火之为”,认为火包括了“君火”、“相火”两端,前者为虚,后者为实,两端的交错就构成了自然的运动。《东西均》中虽然没有专论火的篇章,但《开章》提到“是何东西?此即万世旦暮之霹雳也”,《所以篇》中改写“氤氲”为“烟熅”,都暗示着火。《东西均》反复发挥了这一原理。
在《东西均》中,有时他甚至抛弃了曾被古人神秘化了的“天”,说“天本无天,以天在一切物中”。
但是一般他仍用气的范畴,例如:
“气凝为形,畜为光,发为声。声为气之用,出入相生,……时时轮转,其曰总不坏者,通论也。质核凡物皆坏,惟声气不坏,以虚不坏也。……气且不死,而况所以为气者乎?”这样以气即物质为第一性的命题,是十分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方以智还在宇宙生成的问题上使用形象的语言,打落了神学的创世说,他说:
“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一琉璃也。”按此处的“琉璃”是一种“虚喻”,实际上是指混然一块的物质存在。他指出,不能把物质存在和物质存在的“所以”分裂开来,更不能如道家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样,把“所以”提高到物质世界之上,成为头上安头的怪物。
道学家分立了“道”和“器”、“形而上”和“形而下”,把“道”“器”间的关系说成父之生子或水容于盂,方以智认为这是比拟失伦。他还指出了张载哲学的不彻底性,说张载的“谓虚生气”破坏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命题,是“入于老庄‘有生于无’自然之喻,不识有无混一之常”。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方以智最光辉的命题是薪火的比喻。他说:
“火固烈于薪,欲绝物以存心,犹绝薪而举火也,乌乎可?”人类的思维活动,即能思的“心”,是依存于物质存在的,“本一气耳,缘气生生,所以为气,呼之曰心”。这里用薪火来比喻物与心,比古代无神论者以烛火喻形神更为明确,在理论上提高了一步。
他强调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是一彼一此的关系,由此及彼,在于实学,学天地学万物是真学问。方以智指出,从孟子以来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应予翻改为“万我皆备于物”,因为人们把山、河大地归自己易,把自己归山河大地难。
据此,他论证宇宙的道理怎样才能够是可知的:
“天与人交,人与天交,天生人是顺,人学天是逆,交则为爻,爻即是学。故孔子只说学字,而不以悟道挂招牌。
“古文‘无’从‘天’,象气也。古文‘气’作‘?’,亦作‘炁’,从‘无’、‘火’。理,玉之‘孚尹旁达’、‘文理密察’也。天有文,地有理。曰‘道理’者,谓其路可由而文可见也。圣人何处不以示人?有真识字人,则必不受文字障矣。”这样通过训诂学来戳穿了“道”、“理”范畴的神秘的外衣,和后来的戴震是相似的。
人类的思维怎样和存在合致呢?他指出认识自然只能是如实地对待自然发展的规律,“逆”以应之,即所谓“学,逆几也”。人心不能“倔强”于天地万物,而只能顺着宇宙日新代错的运行,“以顺用逆,逆以为顺”。然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有“明”、“暗”及综合“明”、“暗”而更进一层的“合”的不断高涨的阶段。
他说:
“明天地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认识就是这样“明——暗——合”的过程,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例如他说古人的结论在当时是被认为“明”的,到了后来一定时期就成为“暗”的,后人也可以超越前人再度为“明”的。
“无对待”的真理即在“对待”之中,所以他说作为最高真理的“公符”,不能离开相对真理而直接求得,而“仍是相反相因、代错交轮之两端而一之,本无有不有也”。
上引文中所讲的“随”、“泯”、“统”三个概念,是方以智的特殊用语。这已经涉及他的有关辩证法的方法论,还应进一步地加以说明。
“随”原义为从顺,在方以智书中有时与“存”通用,义指肯定或正命题。“泯”原义为尽,在方以智书中以“泯”与“存”对立,如说“有即无,存即泯”,义指否定或反命题。“统”是综合“随”“泯”而“进一层”的“随”,方以智有时也称之为“超”,即相似于否定之否定或合命题。
“随、泯、统”的公式,方以智用形象的图式表示为“∴”。王船山在赠方以智的诗中说:“哭笑双遮∴字眼”,即指他的这一公式。
这样看来,方以智的朴素的辩证法在形式上观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是超越前人的大发现,是和当时人所公认的他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分不开的。他把这一公式运用于《东西均》各篇,体系颇为一贯。《东西均》一书的篇名,如《反因》、《奇庸》、《全偏》、《神迹》,不少是以对立的范畴来命题的。他指出有无、虚实、动静、阴阳、体用、形气、道器、生死、可知不可知等等,都是矛盾的两端,是裂一为二,二复为一。
他说:
“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一中贯于二之中,即他说的“两端中贯,举一反三”。
他试图运用这一原理去说明宇宙万物的规律。例如对于弓的一张一弛,他说:
“一张一弛之鼓舞者,天也。弓之为弓也,非欲张之乎?然必弛之,以尽其用。急时张多于弛,已必弛多乎张,明矣。”张弛是弓的两端的统一。又如对于源流二者的对立统一,他说:源一流分是一个正命题,源分流一是一个反命题,他将这两个矛盾的命题综合起来,说:“源而流,流而源,乃一轮也。
”他还用水在地球上的循环来证明,指出“水自上而流下”和“水自下而流上”犹之乎人体血液一方面流注足掌,另一方面又流入脑际,都是反复流转的。再如对于道艺二者,他指出道和艺是对立的统一,而且道在艺中,如果单从道来片面地强调,则“急之于道,而仍缓之于艺”。
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还提出了“交、轮、几”的公式。这一公式在形式上近似于矛盾转化的规律。
“交”指对立物的相交,方以智称为“合二而一”、“相反相因”或“交以虚实”的关系。他说:“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捄相胜而相成也。……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
……相害者乃并育也,相悖者乃并行也。”“轮”指运动转化,他称为“首尾相衔”、“代明错行”、“轮续前后”。他说,“举有形无形,无不轮者。无所逃于往来相推,则何所逃于轮哉?”“几”指在不息的运动中达到一个高级的阶段,他的话所谓“不息几于代错”,而“所以代错者,无息之至一也”。
在“交、轮、几”公式的运用中,他提出了不少清醒的命题。
例如涉及对立物转化的若干问题时,他说:
轮之贯之,不舍昼夜,无住无息,无二无别,随泯自统,自然而然。”由于对立物的交轮,就形成了“随——泯——统”的自然而然的发展。他甚至说到绝对和相对也是相反相因的,而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他把这叫做“公性在独性中”。
“吾尝以无对待之公因在对待之反因中。”他批评庄子唯心主义“不明公因,而定是非”。这样关于对立物转化的法则所创出的形式性的理论,是超越古人的。他根据这一原理探求“星辰何以明?雷风何以作?动物何以飞走?植物何以荣枯?”
然而他的理论不能探到质的飞跃的规律,因而不能不流露出循环论的弱点。在运用“随、泯、统”和“交、轮、几”的原理时,他在很多场合是形式的、概念的。例如他说:“中非无过不及之说,而又岂废无过不及之中乎?”在《公符篇》中,方以智反对了相对主义的怀疑论,却又提出“存泯同时之时中”,在两端之间不必要地求取平衡的中道。
特别是他所讲的“几”,即在不息的转化中达到的“至一”,更就有些神秘。这不是向高级的突变,而是安定的平衡。
例如在“内”、“外”两端之上有“中”,“高”、“卑”两端之上有“平”,“天”、“地”两端之上有“真天”,“有”、“无”两端之上有“太无”,“善”、“恶”两端之上有“至善”,这便陷于平衡论的观点。
方以智在其他书中也有循环论的“时中”概念,如说“观玩环中,原其始终,古今一呼吸也”,这不但和他所提出的物质经常处于矛盾运动的命题是相反的,而且走入形而上学思辨的歧途。恩格斯在批判近代初期的自然科学时指出,它虽然理解到平衡与矛盾,但还不能理解到“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方以智从他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中提炼出的理论,有其光辉的进步的一面,如说哲学要寓于科学,而科学更要以哲学为指导,但他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陷阱。
其次,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虽然有着光辉的命题,形成了十七世纪中国哲学的高峰,但在他的著作中还遗留着很多佛学和象数学的神秘主义的糟粕。不少术语虽然经他改造,颠倒了唯心主义的提法,但他仍不能不受这种术语的神秘色彩的约束。
例如,他把“心”的范畴分为“公心”和“独心”。“独心”是与物质对立的,但“公心”又超乎心物之上。他说:“一切因心生者,谓其所以然者也,谓之心者,公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俱在此公心中。”这个“公心”和他所说的物质自己运动的“所以然”就等同起来。
他又偷换了概念,把“盈天地皆物”的命题,改用“一切因心生”的命题,规避其锋芒。他用“以实证之”的“所以”替换了形而上学的“太极”,是前进的;而他以虚义讲的“太无”以至“公心”之类,其中虽既无意志性,也不是主导方面,但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退让。
我们说,去掉这个和“公因”相混同的所谓“公心”的死壳吧,剩下的便是干净的物质自己运动了!“所以然”已经说到正文的主题,而“公心”的注脚是画蛇添足的多余做作。看来,方以智在自负“开从来不敢开之口”时,也不能不受黑暗的鬼影所压迫。
总之,方以智在明末社会斗争和清初抗清斗争中,是一个有力的政派领袖;同样,他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中,也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盟为特征的学派的中坚。他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