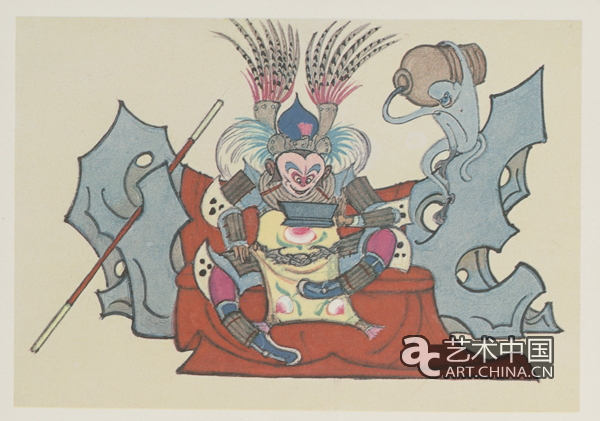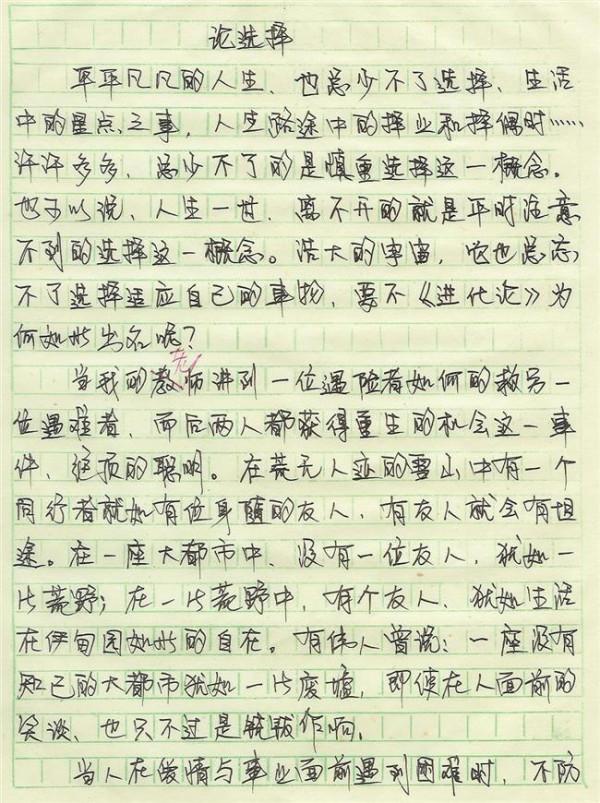张丽钧作品集 满口唐山话(转自开滦一中校长青年作家张丽钧新浪
读大学时,爱上一个唐山人,毕业后便随他来到了唐山。初来唐山,听着满街筒子的男女老少人人一口纯正的唐山话,感觉特别惊奇。“笑死我了——好像走到哪儿都在说相声、演小品!”我这样向朋友描述。我教语文,清楚地记得一个女生在课堂上用唐山话背诵朱自清的散文:“叶子出水很高,像婷婷的舞女的裙……”那读阳平的“婷婷”和“裙”都被她不由分说地篡改成了“唐山调值”。
我强忍住笑,用普通话范读,然后让她跟读,她一开口,依然是“唐山版”的“婷婷的舞女的裙”!
我结婚生子,一不留神儿,给孩子取名时竟选了个唐山人都发不准的阳平音——“然然”。我一遍遍用普通话教孩子说:“我叫然然。”但孩子从托儿所一回来,立马变成了“唐山版”的“我叫然然”。
我去买菜,有了个惊人的发现——说普通话,“西红柿一块钱一斤”;说唐山话,“火柿子(西红柿)八毛钱一斤”!——明摆着,小贩欺生啊!打那儿以后,我买菜时改说唐山话。 唐山话是那种浸润性很强的话。
在单位和本地人对话时,我竭力扳着,不让对方把自己拐带跑了。但是说着说着,我就发现坏事儿了——我让人给领沟儿里去了。 后来,跟多年未见的朋友见面,我一开口,她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啊?你怎么满口唐山话了?”我也很吃惊:“真的吗?可是,我咋儿不觉呢?”她大笑:“还不觉?都‘咋儿、咋儿’的了!
你都可以跟赵丽蓉老师一起去说‘探戈揍是趟啊趟着走’去了!” 以我老公为代表的唐山人普遍“自恋”,认为唐山是全中国最好的“地界儿”。
“你瞅,全世界的华侨都管中国叫‘唐山’!唐山揍是中国,中国揍是唐山!”我老公是拧着脖子跟我说这番话的。我赶忙点头附和,因为我明白,在这个“地界儿”跟他争辩这个问题是颇不明智的。
我老公写诗,由衷地讴歌唐山这座“凤凰涅槃”的城市。他说:“在唐山,每一朵鲜花都是顶着人的灵魂开放的。”经他这么一说,我虔敬地爱上了唐山的每一朵鲜花。 我学校的老校长是北京人,退休后回到了北京。前几天我去看她,她跟我说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天,我去超市,碰上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岁,满口唐山话,我听得着迷了!
就悄悄跟着人家走,他们看辣椒酱我也看辣椒酱,他们看洗发水我也看洗发水。后来,那男的发现我跟踪他们,冷不丁问我:‘大姐,咱们不认识吧?’我特别尴尬,忙说:‘咱们确实不认识;可是,我在唐山呆过30多年呢!
我揍是稀罕听你说唐山话——咋儿那好听啊!’” 那天,我儿子然然从英国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刚到机场接了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唐山老乡。
“我俩一见面,满口唐山话——哎呀!忒过瘾哪!” …… 我常想,莫非,唐山话里住着个魔?它咋儿就有本事把所有与它亲近过的人统统都吸附了去、俘获了去?它那初听滑稽谐谑、引人发笑的语调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深情,为什么竟有能耐长进人的血脉,让人生出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座“命大”的城市,凭着一个亲切的戳记将她卓异的儿女们紧紧维系在一起,让他们用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调值说尽了无边的苍凉与无边的温煦……目下红学研究中有一派坚决认定曹雪芹的祖籍“揍是”唐山丰润,这里有一种酒索性就叫“曹雪芹家酒”了;揣想着曹雪芹操着唐山话写“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 落絮轻沾扑绣帘……”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