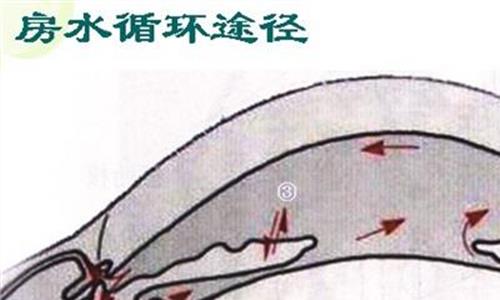高昌国灭亡 消失的高昌国:荒废在丝路上的宝地(二)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空前繁荣还使佛教的传播出现了回流的现象。由于汉唐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对这一外来宗教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种理解和发挥也在不断地向西域地区回流。十六国时期,高昌僧鸠摩罗跋提向占据北方的前秦苻坚进献梵文《大品经》,晋太元十五年法显西行至高昌传授经文。

高昌国佛教的盛行,与唐朝时着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玄奘怀着到西方佛教的发源地去求取佛经、弘扬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游之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长途跋涉,玄奘于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国境内。此时,正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统治时期,国家十分强盛,佛教已经流行开来。

但是,在高昌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研习佛法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文字和不懂的经文。而中原的唐朝却早已对佛经有了充分的知识与理解。从唐朝不远万里来了一个精于佛法的高僧,麴文泰很是高兴。

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交谈中,麴文泰被玄奘的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国师,并沐浴更衣,亲自为玄奘执香炉,率领王妃、文武大臣听他讲经说法。在听了玄奘的讲解后,麴文泰马上弄懂了许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的问题,对玄奘更加佩服了。就这样,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的时光。

这天,麴文泰到玄奘的住处去拜访,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玄奘向他辞行,准备收拾行囊继续向西天的路前行。麴文泰本来是专门来请玄奘长期住在高昌国的,协助他管理国家的,却听到了这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
无论玄奘怎么劝说,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个有着坚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会改变去西天的志向。麴文泰见玄奘执意不从,不愿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另外就是请玄奘留下来讲一个月的佛法。
玄奘见国王松了口,况且他提出的条件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宣扬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玄奘与麴文泰举行了隆重的结拜典礼并认真的将自己的佛法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之后,麴文泰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把玄奘亲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恋恋不舍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国宣讲佛法时,在寺庙内遇到了长期居住在这里的3名汉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老的已经鬓发皆白了,听说来自唐朝的玄奘法师到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光着脚就跑去相见。他一见到玄奘就痛哭了起来,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来自家乡的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时就有内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讲佛法。这件事也说明了高昌国由于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僧人,有力地说明了高昌国佛教传播的回流现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了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499年,由于政坛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坛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的。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麴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麴文泰铸造钱币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理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
“高昌王”这一称呼只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并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在《魏书?高昌传》中就记载了“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时表明中原政府对高昌国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认的。在历代的高昌国王中,也只有麴坚一人被正式册封为郡王。其他人连这样的头衔也没有得到过。为了表达这种不满,麴文泰就铸造了一批代表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钱币,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
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
“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往东经伊吾即哈密与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侧可直达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达轮台、阿克苏。另外,往南穿过沙漠可到楼兰,与丝绸之路“南道”相通直达和田、疏勒即喀什。
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诸国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自魏晋以来,中原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所控制。
高昌国内部,以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为主,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多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
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所记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的混合体。高昌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以示臣服,但在语言上却始终使用汉字,未使用过突厥文字,而是用汉字拼写突厥语。
高昌对突厥语音的译名与中原文献上所见到的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 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却音译为“吉利”,这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即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所致。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号都是用汉文记述的,但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眼睛上盖着被称为“眼罩”的金属制品。类似的东西,亦曾在欧亚草原上的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显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葬俗。
从高昌吉利出土陵墓的壁画上看出,依从突厥“被发左衽”,这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农耕定居的汉族因日常的生活方式及生产环境与“随畜逐水草”、“穹庐毡帐”的游牧民族不同,服饰上原本是不一样的。但移民高昌后,因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逐渐有所改变。
《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裤裆”,这显然不是汉族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着锦颉(jié)缨珞环钏”则明显是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高昌传》中“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以及《隋书?高昌传》中“男子胡服,妇人裙襦(rú),头上作髻”的记载亦相一致。
“高昌吉利”钱币向世人展示的这些,都是当初的铸币者未曾想到的。
高昌大事记
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军南下,帮助高昌阚氏族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国正式建立。
公元7世纪,高昌国在麴氏的统治下发展到了顶峰。
公元640年,高昌国王麴文泰不满唐朝的统治,引起唐太宗的震怒,派兵讨伐高昌,麴氏高昌灭亡。
公元866年,回鹘族的一支夺去了唐朝统治下的高昌地区,建立了回鹘高昌国。
元朝时,回鹘高昌国王见元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便归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鹘高昌国为畏兀儿王国,保留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地位,回鹘高昌国势日益衰落。
公元14世纪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领12万军队围攻兀儿王国的都城高昌城,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高昌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