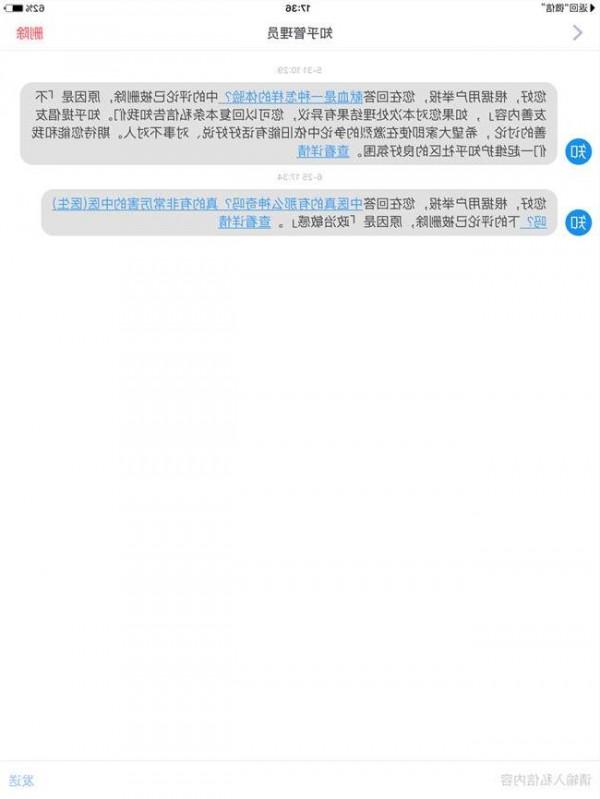宋代的朱熹与陆九渊 罗小平:朱子之理与陆九渊之心的比较研究
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宋代两位著名的理学家,“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1](《宋元学案》卷首)虽然他们都传承了儒学和二程理学,但学术倾向颇有不同,其中分歧最大的是认识论,即以何为世界的本原。前者主“理”,即以“理”为本体;后者主“心”,即以心为本体,由此成为宋代理学最受关注话语,至今学界仍然没有做出一个实质性的解答。

“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哲学思想概念,以朱熹为代表。其来源受《庄子》“庖丁解牛”的启发而引伸出条理、文路子的思维,进而推致阴阳五行不失条绪有了理的概念。至了宋代,北方理学家提出了理的命题,代表人物是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他们以“理”为世界的本体,分别创立了濂学、洛学和关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程颢、程颐之父程珦任江南东道虔州南安军副职时,周敦颐主刑狱。因周敦颐学术渊博,程珦让程颢两兄弟从其学,是理学的重要创始人。
史载:“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2](《宋史》卷四二七)

周敦颐作《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以“无极而太极”论天地之化:“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3](同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参化,化生万物。由是,太极被赋于了理的概念,在理学家的眼里,宇宙万物由理而生。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4](《宋元学案》卷十一)被称为“天生之完器” [5](同上)近于颜子程颢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其弟程颐更对天理作了发挥,提出“ 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6](同上,卷十五),而人与物同为一理,理成为万物的本原。
他们以理为世界的本体,认为“天地间无一物无阴阳” [7](同上),强调人类也应类法自然,以期“明于庶物而察于人伦,务于穷神知化而能开物成务”[8](同上,卷十四)、“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9](同上,卷十三)
朱熹继承了北宋诸子的理学思想,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有“理”就有万物,万物发源于“理”。他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10](《朱子语类》卷一)“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11](同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 [12](同上)可见,在朱熹的哲学世界里,理是构成万物的本体,有理而后有物,理在物先,甚至在万物之先。没有“理”就没有万物。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13](同上)“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同上)“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15](同上)“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16] (同上)
太极是理的总名,在此之下又各有太极、各具其理。他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17](同上)天地之间凡物都是由理而派生,由理而变化、发展。“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18](同上)理生天地、生万物、载万物。朱熹认为理无处不在,大事有大事之理,小事有小事之理。他说:“小小之物,生理具悉。”[19](同上,卷九十七)理与气同时存在,但同原而异质,“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20](同上,卷一)理是本,气是形成万物的质,“先有个理了,却有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21] (同上)“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
[22](《孟子集注》)但受禀于天理之气,物物不同。程颢说:“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23](《宋元学案》卷十五)朱熹认同此说,认为性为与生俱来的资质,但因万物各具其理,物物禀受不同,资质各有不同。
儒家重要经典《大学》,把心放在重要的位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正心”是八目中的一条,强调要从个体开始,一步一步向外迈进,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可见,《大学》为陆九渊心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孟子的仁爱思想也为陆九渊心学提供了养料。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24](《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四端”更为陆九渊的心学提供具体的参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5](同上)此即人之本心。“四端”表现人的四种处世态度或情感,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以此与仁、义、礼、智相对应。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26](同上)可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判别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没有“四端”之心,就没有仁、义、礼、智的外在表现,就无法成为人。如何实现物我观照,孟子提出的办法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7](《孟子•尽心上》)汉儒赵岐注“物,事也;我,身也”。意思是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之理由天赋予了我,而我也完全具备了这种应万物之理的性分。
程颢、程颐的心论对陆九渊也有重要的影响。程颢认为“良知良能是本心”。 [28](《宋元学案》卷十二)二程提出:“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29](《二程文集》卷八)这里强调的是心的作用,治学的方法是先要明白学的目的,才能有进取的方向。
程颐更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提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30] (《宋元学案》卷十五)可见,二程把心视为通乎物理的路径,强调要“道合内外,体万物”, [31](同上)才能万物毕照。
为此,二程提出要读书求理:“人之蕴蓄,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人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蓄成其德。”[32](《程氏易传•大蓄传》)
陆九渊之心与程颢之学有内在的联系。程颢主静,穷理方法上偏重于“正心诚意”;程颐主敬,穷理方法上偏重于格物致知。黄百家对陆九渊之学作出分析:“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33]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可见,朱熹更多的是传承程颐之学,而陆九渊更多的是传承程颢之学。
二程之后,心学的代表人物是包括陆九渊在内的江西三陆氏。史载:“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34](同上,卷五十七)梭山、复斋、象山是同一学派人物,史称“三陆子”。
陆九韶,字子美,抚州金溪人,因“学问渊粹,隐居不仕,与学者讲学梭山” [35](同上),人称“梭山先生”。陆九龄,字子寿,金溪归政(今江西省金溪县陆坊乡)人,陆九渊之兄,人称“复斋先生”。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因为心学集成于陆九渊,其学亦称“象山学派”。
三陆子的学术一脉相承,都主张由内外求的观点,强调要发明本心。陆九韶主张治学以切于日用为要,即“身体力行,昼之言行,夜必书之”。 [36](《宋史》卷四百三十四)也就是强调以心应物而行之于日用最为紧要。
陆九龄也强调要用心感应外界事物,如此才能切己之行。他说:“身体心验,使吾身心与圣贤之言相应,择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37](《宋元学案》卷五十七)陆九渊不仅继承这种观点,而且对心作了概括和哲学性的发挥,认为“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
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38](《陆九渊集》卷一)“人心至灵,至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39](《宋元学案》卷五十七)陆九渊之所以强调心,是因为人心至灵,因为至灵才会至理至明,把住了心就把住了理。
他强调“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40](《陆九渊集》卷十一)在陆九渊看来,物在我心,心外无物。
只有将客观之物纳入我心,此物才存在。他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41](《陆九渊年谱》)所以他从宇宙二字得出一个启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42](《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从上述看,朱熹以“理”为万物的本原,是宋代理学中的“格物派”;陆九渊则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是理学中的“格心派”。由于二人观点不同,形成宋代理学中最大的两个门派,以致“两家门人,遂以成隙”。[43] (《宋元学案》卷五十七)即以朱子为代表的称理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称心学派,导致继春秋百家争鸣以来又一次学术史上的争辩——鹅湖之辩。
鹅湖之辩的焦点是治学方法。朱熹的观点是外物求理,从圣贤书中体验天理,强调读书讲学的重要性;陆九渊则强调要不必读书外求,只要发明“本心”即可成圣成贤。他甚至放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44] (《陆九渊集》三十四)所以朱熹认为陆九渊教人之法太简,而陆九渊则认为朱熹教人之法支离。
鹅湖之辩,没有辩出真知。朱熹认为:“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旨。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得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45](《宋元学案》卷五十七)可见,朱陆之学是理学系统中的“殊途”,黄百家称赞他们“岂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阳有服善之诚”。 [46](同上)又说:“(陆九渊)从践履操持立脚,恐不得指为大病。
但尽废讲学,自信太过,正是践履操持一累耳。(朱熹)若使纯事讲学,而于践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胜,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47](同上)黄百家认为朱陆二人各有所偏,陆氏偏重日用操持,是其大病;朱氏纯事讲学而日用不得力,也是一大弊端,此评价实为中肯。
古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天生万物以养人,食之不为过”的朴素唯物辩证观,虽然此说没有提出世界物质的客观性,但已经表明物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宋代,朱熹与陆九渊在物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理和心的哲学概念,建构起物、理、心三者一体的哲学架构,成为自宋以来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命题而受到广泛关注。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认识,是当今我们的认识论。但在朱熹那里,却以意识为前提,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理、物是朱熹哲学的基本架构。这个架构的哲学态度是先有理,后有物;有是理,有是物。
如此,我们可以给朱熹的“理”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朱子所说的“理”,是规定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与准则。具体地说,朱子之理是规定事物性质、状态及其变化、发展方向的规律与准则。而朱子理学就是研究规定事物性质、状态及其变化、发展方向的规律与准则的学说。
事实上,朱熹所说的“理”是物之理,也就是说这个理寓于物之中,是哲学中认识论的一种方法。虽然朱熹没有也没有必要过份强调物的客观实在性,但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没有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相反,他一再告诉学者做学问,必须向外格物。
格物就是探寻客观存在的事物。他曾说“物物有个天理”“物物各有天理”。这些表述可以看出,物在前,理在后,理在物中,而不是理在物外。他说:“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48](《朱子语类》卷一)他认为大至天地,小至山花小树,是因为物理之所当然、所以然。
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49](同上,卷十五)草匍于地、鱼跃于渊、鸢飞于天,都是自然规定的现象,所以朱熹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
[50](同上,卷三)正因为万物遵循着内在的规定,自然界才有可能生生不已。可见,朱熹所说的“理”,是客观之理。因为物的客观存在,而理寓物之中,是物之理,表明理的普遍性,自然界是在理的作用下出现循环不已的生机。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理自然界就不复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朱熹之所以把理看成在天地之先,是规定万物的法则,目的在于强调“理”(规律)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朱熹讲的理才具有现实意义,这是朱子之理的本质特征。
气是形下。朱熹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51](同上,卷一)“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52](同上)理气又有先有后。有弟子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朱熹回答说:“有是理后生是气。
”[53](同上)也就是说,万物有理有气,但气是理的材料,理规定着气的变化、发展。朱熹说:“先有个天理了,却有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54](同上)气是生物之质,而理必须借助气才能显现出来。
朱熹说:“然事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55](同上)理的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于气,无天地万物,无法彰显理的外在生机。朱熹举例说:“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
[56](同上,卷十三)又说:“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57](同上,卷一)道理很简单,谷种到稻子,必须经过选种、育秧、插秧、施肥、耘田等过程,才能从谷种到稻穗,如果误了农时春播的规律和管理规律,就无法从此物(谷种)到彼物(稻穗)的变化、发展过程,而谷种变成稻子,是谷种内在的理的规定,谷种不可能变成蔬菜、水果或其它物。
上述可知,朱熹把理与气看成是构成万物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有理有气,万物方生。但二者又有区别,理是形上,是本,是无形,只能感知;气是形下,是末,是有形,可以直观。
理的不可变易性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区别事物是此事物,不是彼事物)、状态(以何种方式存在)、变化(如何演变)、发展(向何种方向发展)。在朱熹看来,万物之所以发育,就是因为理发生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由事物的性质发生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朱子之理被视为客观唯心。
朱熹强调客观之理,而陆九渊则不同,他以心为理,强调主观之心。在他看来,心是主宰天地的主体,只有发挥心官的作用,才能体察天地之理。其心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1、主观性。陆九渊之心,概而言之就是以心为先,在他看来,天地之间以心为本,只要心在,天地就在,万物就在。我心即天地之心,我心即万物之心,所以要以天地之心为心,以万物之心为心。
如果我心不在,天地不存,万物不存。可见,陆九渊以心为先、以心为上、以心为重。他从“宇宙”二字得到启发,提出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58](《陆九渊集》卷三十六),把心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具有主观性。
必须指出,陆九渊同样没有否定客观物和物之理的存在。虽然陆九渊不言物之先、理之先,但从他的话语中仍然可以看出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至少他强调的是心与物、心与物之理同时并存。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59]√(《宋史》卷四百三十四)陆九渊把宇宙与我融为一体,我之事就是宇宙之事,宇宙之事就是我之事。可见,陆九渊没有把至明的人与宇宙相隔裂,而是在客观物和物之理的前提下强调要物我观照。
基于心的主宰作用,陆九渊很关注作为万物之灵的个体与宇宙的关系,要人用我之心观照宇宙之心。他说:“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60](《陆九渊集》三十四)
在陆九渊看来,宇宙是客观存在的,而我是苍茫广阔宇宙中的一份子,置身于这个空间的我要思量如何与宇宙同为一体,我之心如何与宇宙契合,如何做一个有利于宇宙循环、万物生生的人。可见,陆九渊视我之心为宇宙的本体,万物都是由我之心派生出来的,这是陆九渊至明的精神境界。
物、理、心三者须作两段看,物、理一体,有物有理,理寓于物,都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变的客观世界;心则存之于我,更操之于我,是可变的。心的可变性,是因为心容易受喜怒哀乐情绪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容易受到利益的驱使。心的可变性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其一,以义为利,事物向善的方向变化、发展。《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证明只有诚意、正心、修身,进而推己度物、推己及人,事物就会朝着治国、平天下的方向变化、发展。
《论语•乡党》记载了一则明心的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孟子则将“四端”之心视为为政之道,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61](《孟子•公孙丑》)以仁人之心,行仁人之政,达到国家大治、天下太平。
孟子还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惕怵、恻隐之心。”[62](同上)所以,陆九渊心即理,表明他十分看重人的善心,要人们用善心对待宇宙、对待万物。要发明这种善心,就要以义为利。这就是陆九渊以心为本的哲学智慧。
其二,以利为利,事物向恶的方向变化、发展。恶是与善相对的一种态度。在理学家的眼里,宇宙之间,只有善恶两端,非恶即善,非善即恶。善心之长,恶心则隐;恶心之长,善心则隐。
陆九渊把心看成是宇宙的本体,是水之源、木之本,人要感格万物、观照万物,必须从本心开始。如果“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 [63](《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陆九渊把良心看成是立志的重要内容,他说:“人要有大志。
常人汩沒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 ” [64](同上)人要有志,就必须识察公私、分清义利之辨。他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65](同上)陆九渊还强调做事要先从做人开始,因为事在人为,人无良心、善道,必然一事无成。他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66](同上)现实中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一个路人,见地下一块玻璃碎片,袖手旁观;另一个路人见地下一块玻璃碎片,俯下身子将其拾起来扔入垃圾桶。一户人家,养狗扰民,被告到法庭,还要百般狡辩;一户人家,电视声音太大,邻居提醒,这户人家改过迁善。前者以利(省得麻烦或已之所欲)为利,后者以义(善行义举)为利。有心无心,善心恶心,结果不同。人心向善,便有善人之举;人心向恶,便有恶人之举。
在陆九渊看来,万物在与不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和心德。心在万物就在,心不在焉,何以有万物,何以有万理,所以他说:“事固不可不观,然毕竟是末。自养者亦须养德,养人亦然。自知者亦须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外行与事之间,将使人作伪。 ” [67](同上)如果没有真心实意,不在修身涵养上做工夫,而只是约束行与事之间,必然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需要指出,分析陆九渊之心,必须对他的心学思想进行深入辨析,得出正确的理解。第一,陆九渊的“吾心”不是狭隘自我之心。换句话说,这个“吾心”不是陆氏一人之心,而是众人之心,即每一个生活在广阔宇宙中至灵的个人之心。
第二,心即理不是以心代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不是除了心之外全然没有宇宙,也不是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而是强调面对客观万事万物时,要立定脚跟,容易受喜怒哀乐情绪变化的“吾心”要紧合天人合一之道。只有如此,才能够像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68](《孟子•尽心上》)
总之,在陆九渊那里,心成为主宰世界的本原,有心就有宇宙万物。要把宇宙万物纳入我心,并且有体悟宇宙之所以终万物、始万物之心,做到以心观物,以心识理,物、理、心三者紧密结合,才能在真正达到物之在我、理之在我。如果无心,物、物之理客观存在也是枉然。
由于彼此各执一偏,导致二人心中之隔,甚至引发为两大学术派别。然而,他们的争论毕竟是在儒家门墙内的纷争,虽然无法“会归于一”,但争论也只是“和而不同”。实际上,朱、陆学术是理、心会通,朱熹重物之理,也重人之心;陆九渊重人之心,也强调物之理。彼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朱熹把理看成是万物的总根源,是万物之总名,有理有物,无理无物,这是朱熹的基本观点。但实际上,朱熹并没有否定陆九渊之心。相反,他也强调心对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性。
陆九渊把心看成是万物之本,朱熹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曾肯定地说:“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69]在这里,朱熹强调心地的作用。在朱熹看来,心地就是良心,它能主宰万事万物。这一观点直接来自道南学派对程颢主静思想的传承,虽然“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的理学思想更多师承了程颐的“主敬”思想,但同时也师承了程颢的“主静”说。
罗从彦在《勉李愿中五首》中曰:“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李侗接受了罗从彦的思想,从“夜醉,驰马数里而归”,转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并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将此思想传给了朱熹。
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有口舌之争,但只是治学的方法问题,前者重外求格物,后者重内求明心,而对理与心的功用却无太多歧异。虽然朱熹把理视为本体,是宇宙的最高原则,但也承认明理须发明本心,认为人的行为受制于本心,心具有主宰的作用。
朱熹明确说:“心者,一身之主宰。”[70]朱熹强调主观对事物变化具有能动的作用。他在注释《大学》“正心”时说“心者,身之所主也”。[71]“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根本也”。
[72]有弟子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73]朱熹回答说:“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弟子又问:“此‘心’字与‘帝’字相似否?”[74]朱熹说:“‘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75]此说来自程子“以其形体谓之天,以其主宰谓之帝”。[76]程子认为虽然有形的天最高,但天之上还有一个神明就是心,它主宰着宇宙、主宰着万物,朱熹赞成此说。
心支配着人的四肢全体,支配着人的行为方向,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行为。朱熹说:“心者,身之所主也。……意者,心之所发也。”[77]心是一身之主,意是心之所发,是心的运用处。心是检验行为的依据,没有心之察识,不知所行之善恶。
朱熹说:“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也。”[78]朱熹也像陆九渊一样,强调物我一体,心正则万物生生不息。他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心之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
”[79]朱熹引用邵雍的话说:“康节云:‘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80]朱熹把性视为形之体,把心视为重城结隅之外城,把身视为括然本心之境域,把物视为可以驱使的舟车。
朱熹甚至也理心不分,以理为心,所以他主张要“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81],如此才能“使人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82]朱熹引用程子之言:“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83]朱熹也同意义刚“理在物,见在我”[84]的观点。
朱熹心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心统性情。鉴于心的主宰作用,朱熹一再强调心与理不可分,否则心是心、理是理,心理分隔,物不在是,理必不具。他说:“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85]理是否存在,关键是心是否安然明亮。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86]心还要廓然广大,才能包举万理。朱熹认为,心是仁人之心。有弟子问“心为太极”“心即太极”。朱熹回答说,理即是性,“‘心’字,各有地头说。
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这说心是合理说。”[87]又说:“天地无心处。且如‘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圣人,则顺理而已,复何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说得最好。”[88]朱熹引用程颢之说,认为天地顺四时普万物常规是心,圣人以其情顺万事之理也是心。天地之心是一个总概括,分殊万物万事各有其心。朱熹说:“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接着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
”[89]朱熹甚至直言心就是理。他说:“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朱熹把心等同于理,心的主宰作用就是理。
但心是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他说:“人心者,气质之性也。可为善,可为不善。”[90]善者,是人的天地之性决定的,不善者是气质之性决定的。天地之性的善是人的道心使然,气质之性的不善是人心使然。虽然同一个心,但也有理欲之辩,义理之心是道心,是善心;人欲之心是人心,是心之恶。可见,朱熹也是理心不分,把理看成是心,以心代理。朱熹之理与陆九渊之心浑然会通,俨然看不出朱子与陆子之间的分歧。
理寓于物,要识察物之理,必须细察于心,有个知觉处。朱熹说:“天下之物,至微至细者,亦皆有心,只是有无知觉处尔。且如一草一木,向阳处便生,向阴处便憔悴,他有个好恶在里。至大而天地,生出许多万物,运转流通,不停一息。
”[91]朱熹认为心与理会通,要发挥知觉的主动性。知觉是客观事物进入人的感官通过大脑的作用感知事物。如它的存在、性质、状态、变化、发展,都可以在感知的召唤之下得出结果,从而得出事物的整体表征。可见,朱熹不仅承认心的作用,而且也承认陆九渊说的有心才有物,有心才有理。反过来说,如果无心,何以有物,何以有理。
朱熹认为知在我,理在物;知是主观,理是客观。他说:“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94]“宾”与主相对,就是客观。朱熹强调主观与客观要统一,以我之知悟物之理。
朱熹还认识到客观之理无穷无尽,知也无穷无尽。朱熹明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有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95]要让客观之物和物之理存之我心,必须主客合一,才能穷究事物之理。
今天我们把朱熹的理学看成是唯心论,并且曾在相当一个时期对此妄加批判,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朱熹完全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朱熹还告诉人们要常常唤醒良知良能,去体察客观之物和物之理。他说:“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
”[96]朱熹认为人要明理,必须通过格物,让心致其知。他说:“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97]致知要发挥心的作用,心不正则无法观物,更无法识理,即便识得物和物之理,处事也会出现偏差。
朱熹就认为载沉载浮、载清载浊、载驰载驱,全在人之心意。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评判:“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98],这是逆人之心;“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99]这是中庸之心;“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100]这是偏执之心。三者以中庸之心最为可观。
致知在格物,读书也是致知的一种方式,而读书也必须用心。朱熹说:“盖为学之事虽多有头项,而为学之道,则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101]朱熹用自己治学的实践教育弟子。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102]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以理为本,是他认识世界的哲学思路,但这条路径也与陆九渊之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通过心的作用,察“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103]因为朱熹说的理既含盖宇宙,也含盖社会人生,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的准则,他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
”[104]有时候,朱熹也把道视为理,他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105]由此可知,朱熹不仅强调理,也强调心对理的作用,更把理引入社会人生,而人生之理是万物之理的一部分。
陆九渊以心为本,将心视为至善的本体。但是,陆九渊同样没有否定客观存在的物和物之理,相反也一如朱子强调理的重要性,强调格物致知,有助于发明本心。明代的王阳明虽然继承陆九渊的衣钵,但他同样表白:“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106]
陆九渊主张以心为本,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以物为本,他承认客观物的存在。“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强调了宇宙的存在,也强调客观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宇宙和万物的存在,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而是要将其纳入我心。
他对那种只把宇宙停留在口头上的人提出批评,认为“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107]陆九渊认为宇宙没有至灵的精神,而人却是万物之灵,不是宇宙交感人,而是人要交感宇宙,才能万物有备于我。陆九渊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108]圣人之所以圣,是因为他们有万物备于我的情怀。
陆九渊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自然界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主张人不能离开自然,相反要与天地合其德,才能乐天地之乐。他说:“今一切了许多繆妄劳攘,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精,与天地合其德云云,岂不乐哉。
”[109]“人共生乎天地之间,无非同气。扶其善而沮其恶,义所当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为之意”。[110]陆九渊认为人对自然“扶其善而沮其恶”是义所当然之事,不能把自然与人相隔离,分成彼我,更不能有超越自然的“自为”之意。
因为宇宙是客观的,万物也是客观的,物之理当然也是客观的,所以陆九渊也像朱熹一样主张要格物穷理。他说:“此理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形唬,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谓之陷溺,谓之旧窠,说只是邪说,见只是邪见。
”[111]在这里,陆九渊强调道寓于物、寓于事,要明白道的存在,必须用心识察感悟,方始有得,如果物是物、事是事、道是道,道与物、事不相干,便无法识察事物之理。
在陆九渊看来,宇宙万物既大又小,宇宙之理可以从方寸之间得到体察。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滿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112]就是说万物看似繁密,但细微之处蕴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