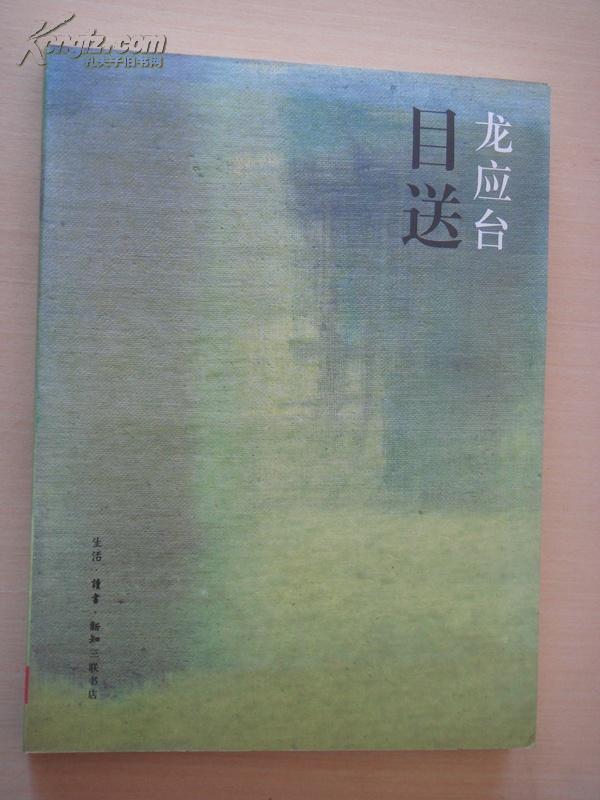陆扬北大 真正的北大 是看不见的北大
北大这个级别的大学,人文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条件。没有人文,这个学校就不成立。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认为这所学校多少和时代有点拧巴,不是那么合拍。要做到不苟流俗,狷狂自任。 ——杨立华 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不是整个移植,而是要顺着这个水分和阳光去生长。
——陈平原 今天整个的学问状态,都陷在方法主义的泥潭里。只有多读书,才能有温度。 ——渠敬东 今天的学术似乎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学术大工业的潮流之中,甚至进入网络学术工业的时代。
学者过去是手工艺人,现在是生产线上的工人。 ——王风 空闲的人文学,可能 会纵容懒惰,但是更应该给少数的勤奋者留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等待学术缪斯的降临。 ——陆胤
总的宗旨 “扩大思想史的视界”
“王汎森要来北大了!”这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在网络上、在朋友圈、在读书界流传的话题,如同一股无形之“风”,吹皱了未名湖平静已久的思想水面。终于,在北京春日难得的蓝天下,在前燕京大学鲍氏女子体育馆旧址的地下讲堂里,在北大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诸多重要学者的陪同下,人们见到了这位思想史家的本尊。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正如柯林伍德的这句名言所阐释的,思想史是历史的发动机,一切客观的史迹,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主观的意向、情感、谋划、认知、记录。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兴盛一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近年略有冷却的迹象,大概是在材料和方法两方面,都遇到了瓶颈。
在海峡对岸的王汎森院士,则是一个例外。他同时涉足明清和近代两个领域,如盐入水地活用西方思想史理论;更可贵的是,这些年他连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副院长等要职,这些行政工作并没有中断他的学术思考和写作,而是为他理解古今思想脉络提供了更丰厚的阅历。
此番王汎森院士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席”之邀前来讲座,是他第一次以正式的学术身份访问北大。王院士当年的博士论文题为《傅斯年》,单篇论文也多有涉及新文化运动及北大的内容,涉足北大校园,当更有一番特别的感想。在不到两周的访问时间中,他为北大师生呈现了三次公开讲座,在历史学系另有一次专业讲座,关于大学问题,更安排了一次题为“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的内部讨论。
与此前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进行的系列演讲稍有不同,今次王汎森在北大的三讲自成体系,并不涉及具体的研究对象,更多在方法论上作鸟瞰式的总结。一个总的宗旨,就是“扩大思想史的视界”。这种视野的扩张,又非空对空的理论爬梳,而是出自明清以降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以我为主,取我所需,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一讲“实”与“虚”“图穷匕首见”,自有清代思想史的当行本色做底子
比如第一讲“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王氏列举了观念史、心态史、新文化史影响下的思想史、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科塞雷克概念史学派等西方思想史流派。如果从一个专攻西方史学史或概念史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觉得他的系统未免过于庞杂,几乎无所不包。
然而,王汎森重点阐述“剑桥学派”与“概念史学派”及其批评者的观点,展现出一种二元的结构:一方面,是“剑桥学派”的昆汀·斯金纳等受语言分析学派影响,强调当下的语境脉络,想要了解的是思想背后的“upto”(想要干什么),任何言说都有其听众设定和文本脉络;科塞雷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学派则强调概念的时间纵深,不仅描述,而且期待,将思想视作层累的库存。
这两种潮流构成一方,都更注重思想受时间塑造的“实”的面向,都要还原语境和动机。而他们的批评者,则构成另一方。如彼得·戈登针对斯金纳的脉络说,提出思想的“具体的听众”之外还有“无限的听众”,在“潜在的意向”之外还有“当下的意向”;思想的读者不一定在具体脉络中,思想家也可能为无限远方、无限未来的无数听众说法,在“显在影响”之外自有其“潜在势力”。
又如HanBlumenberg批评概念史研究,指出意义不是概念所能穷尽,更有图像、事物以及许多不可说的因素在宣示自己。这些批评者,都是在反思20世纪西方思想史研究受到的语言学冲击,进一步要走出语言之“实”,触摸思想当中不确定的、虚的部分。
讲完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波谲云诡,王院士突然跳到清代,讲起了戴震、阮元为代表的汉学考证,以及他们的批评者: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于不太熟悉王院士思路的听众来讲,未免有点转得太快。实际上,这正是“图穷匕首见”,从此正可知道他对西方思想史流派的梳理并不是面面俱到,更不是信手拈来,而自有清代思想史的当行本色做底子。
两者实际上是一组平行结构。正是通过清代中期“汉学”与反“汉学”、训诂求义方法与性理得义方法的对立与辨证,王院士才得以重新观照20世纪西方思想史在“实”与“虚”之间的变相,又凭此使他所治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获得更为普遍意义的深度。
第二讲纵深感把思想影响机制比喻为铁路的“转辙器”
如果说第一讲是会通中西思想史方法的全局,第二讲则是回到思想史研究的具体操作层面,讲述“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这讲的题目实际上借自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的谈话录《哲学作为生活的方式》,反思以往思想史研究只注重精神创造而忽视生活实践的偏颇。
借用王院士的话说,思想有一个“纵深”,有许多“层次”,比如宋明理学的扩展,既有北宋五子、朱熹、王阳明等原初创造层次,也有它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普遍化、通俗化甚至口号化的诸多层面,最后透达“街头层次”,浸润在日常的话语、仪式、教训、娱乐以及政治、军事的实践之中。
在不同层次之间,并没有优先顺序,思想影响可以是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乃至四面八方,左突右攻,如风行水上,不可遏止。但这种对生活纵深的强调,并不是回到那种僵硬的社会决定论或反映论,它是在思想和生活之间,一种更复杂的影响机制。
王汎森一向善用譬喻,他把这种影响机制比喻为铁路的“转辙器”——生活对于思想,未必能如社会决定论所说的那样,完全发动或阻止其前进,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转变它的方向。
第三讲穿透力追求在钟摆两端之间得其中道
王院士在北大的最后一讲题为“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已经不仅仅着眼于思想史,而是对整个中国史学甚至人文学趋向的回顾和展望。
王氏直言这一讲的内容是一个刺激的产物,某位海外的中国史名家居然放言历史研究中“人名越少越好”,一切都要回到制度、回到结构。针对这种观点,王院士回顾了清末民国“新史学”以来史学研究中“人”的隐去和“事”的兴起,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政治经济学等西方现代史学范式的指引下,个人变成团体,人物中心变成问题本位,英雄创造让位于历史趋势。
而在195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史学对人的“去中心化”,年鉴学派认为人是历史的“泡沫”,注重长时段、结构性力量和集体心态,直到福柯宣告“人的死亡”,史学研究中“人的消亡”更是愈演愈烈,造成许多偏颇。
结合梁启超的“首出人格者”论和钱穆对人的“前势力”的关注,王汎森指出当前中国史学需要一个“人的复返”,但这种复返不是对20世纪史学新潮的反攻倒算,不是要回到二十四史,更不能假装“人的消失”这一过程没有发生过,而是需要在“人的作用”和“结构作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这讲内容实际上与第一讲的思想史方法论桴鼓相应,都是在语言结构的“实”和思想流风的“虚”之间做文章,都是在反思20世纪人文学的语言转向、结构取向,又不因此就投向另一面,而是追求在钟摆两端之间得其中道。思想史研究背后,有深邃的哲学向度,这是王氏思想史研究为常人所不及的地方。
王汎森院士此次在北大的三次演讲,分别由邓小南、杨立华、陆扬教授主持,知名教授罗志田亦前来对话;最后一次关于北大精神的论坛,则由陈平原教授主持。可以说这次活动,是在“大学堂讲席”项目牵头,历史系、出版社参与主办之下,北大文、史、哲三系的一次跨学科盛事。由此也可想见,王汎森及其思想史研究在华语人文学界的穿透力。
嘉宾互动只有多读书,才能有温度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只有真正的打开自己,才是真正不封闭的,是不陷入狭隘与封闭的状态的。只有这样的学者,他的研究才是充满着生机,充满着生命力的。这样的人,做的是有真正的人的价值贯彻其中的学问。
北大这个级别的大学,人文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条件。没有人文,这个学校就不成立。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认为这所学校多少和时代有点拧巴,不是那么合拍。要做到不苟流俗,狷狂自任。
陆扬(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虽然在座的认为王汎森先生主要是一个思想史家,但是这个定位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以我个人对他的了解,以及对他著作的阅读。他实际上真正关注的是思想的力量在历史中如何发生作用,这个非常重要,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
他特别重视思想的潜流和潜力,一般我们往往会被一些主流吸引,我们历史研究往往会追逐主流,他的研究则特别关注潜流,以及思想的层次。他非常注重不同语境下面的思想,注重不同的人群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其实在整个史学中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普通的个体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消失了。
我不认为事和人是矛盾的,你写东西的时候到底写事还是写人,是紧张的,然而不是对立的,可以互相配合,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所讲的相生相克。
我们有时会把文化和传统看成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好像可以替我们负责任,这也许是一种新的思想。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社会上对于北大的议论,过去容易神话,现在容易丑化,不必太在意。每时每刻都被大家挂在嘴上,那就必定是夸张的,要以平常心来面对。
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不是整个移植,而是要顺着这个水分和阳光去生长。
学者要大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2015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发声。大学是办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如果学者不发言,那大学很可能就横冲直撞,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学者应该努力影响大学的发展的路径。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大应该培养三种人:有志之人,有学之人,有趣之人。现在大学里面有趣的人少极了,要有天天都能过着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自得其乐的生活的人。
今天整个的学问状态,都陷在方法主义的泥潭里。只有多读书,才能有温度。
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今天的学术似乎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学术大工业的潮流之中,甚至进入网络学术工业的时代。学者过去是手工艺人,现在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学术文体的单一化,将会造成对于学术个性的伤害。要知道不同的学术文体承担着不同的学术功能。
陆胤(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
不能让看不见的现实,不断去冲击看不见的理想。习俗和内心,看得见的制度和看不见的精神,本来应该是联系起来的。
空闲的人文学,可能会纵容懒惰,但是更应该给少数的勤奋者留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等待学术缪斯的降临。
王汎森的轰炸
张一帆(中文系博士生)
刚刚过去的十天,我的生活是以王汎森先生为圆心的。说是圆心,是因为我的工作全都围绕着他来进行,但是和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很多直接的接触,还保持着一段距离。在每一次演讲过程中,我负责播放幻灯片;而在演讲结束以后,我回到宿舍对照录音和速记稿整理他演讲的内容。
对于王汎森先生本人,此前我只在讲座中见过他一次;对于他的著作,我虽然曾经零散有过一些阅读,但是一来毕竟不是历史系出身,二来我在日常工作中所关心的时段也与他的研究不同,所以完全说不上有深入的了解。这种不熟悉所造成的结果,是我在这十天里相当于接受了一场“王汎森的轰炸”。像是笨手笨脚的虚竹去见无崖子,一瞬间被传了七十年的功力,不由得不感到头晕目眩。
学问当然没法这般传递,读到博士阶段,常年接受导师的敲打,早就不敢再做“一夜暴富”的美梦。之所以要用这样蹩脚的比喻,实在是因为这一场轰炸带来了太多信息,以至于鼓动我无知所以无畏地接受邀约。
王先生第一讲的主题是“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他所提到的流派与著作,我虽然了解并不深入,但是此前大概也读过一些。我过去的感觉是,阅读与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不直接相关的著作,似乎是为了追求抽象意义上的所谓“修养”,不仅读不大明白,有时还带有一点负罪感。
然而通过王先生的演讲,我发现对于学者而言,“修养”与“技艺”之间似乎并不是完全截然二分的。王先生当然有他更大量的阅读,仅就这一场而言,听他从二十世纪西方各个思想史流派入手,好像是蜻蜓点水,但是每点一下,都像是打开了通往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一扇窗户,带来一点新的光明。
这一个印象在他这一讲的结尾得到印证,他从西方直接转入清代学者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却让人有水到渠成之感。
对我而言,这一讲更像是一种如何读书的示范,告诉我对于不同的知识,应该如何确定它的位置,是远是近,是详是略,从何种角度进入,最终的结果是要可以与自己此前的研究相印证。当然这也要求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足够的体悟。
另一点突出的印象,是我在三次演讲以后的座谈会上获得的。我听他在讲大学问题,讲他行政管理的经验,脑袋里常常会蹦出来之前刚刚在演讲中听到的观点,甚至某些具体的词句。比如“经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他讲对于不同的思想史流派他的态度“不是取代式的,而是扩大式的”,比如他讲到对待历史,“除了关注实的部分,还要注意虚的部分”。
这些从学术中得来的经验,似乎很自然地被他贯彻到日常生活之中(又或者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所以有这样的学术经验?二者总是相互补给营养的吧)。
我感觉到他对于生活也像是把学术看作他的生活方式,而他对于各种意见的态度也是扩大式的。而如果将人文学术与整个社会对照起来,那么相比于“实的”社会而言,他所孜孜以求的人文学术不也正是“虚的”部分吗?
掐头去尾,说一点印象,饾饤之见,自己先原谅了自己,毕竟还处在被轰炸后的状态吧。本来写到这里,即使不限篇幅,也实在不该再多说一句了,可是既然已经横冲直撞,那就索性一次做个彻底,最后说一点我从王先生演讲中得到的与我自己的本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相关联的体会。
我以为王先生演讲中所提到的历史之中“虚”的部分,他对于概念之中时间层次的划分,以及他在《执拗的低音》中已有论述,在这一次演讲中也有发挥的“风”的理论,其实都在指向现代文学所关心的许多核心话题。
对于以上三者而言,若要我想出一个最能借来概括的意象,我以为当是鲁迅笔下的“死火”。这也是我在被轰炸之余,仍然感到有一阵沁人清风吹来的原因。王先生的演讲,其妙用不仅在于使听众增加对于思想史的体认,更启发我以别种眼光重审自己的专业。只是补充了这样粗陋的意见以后,就不仅暴露出自己不懂思想史,恐怕回到原来的专业也不大好抬头见老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