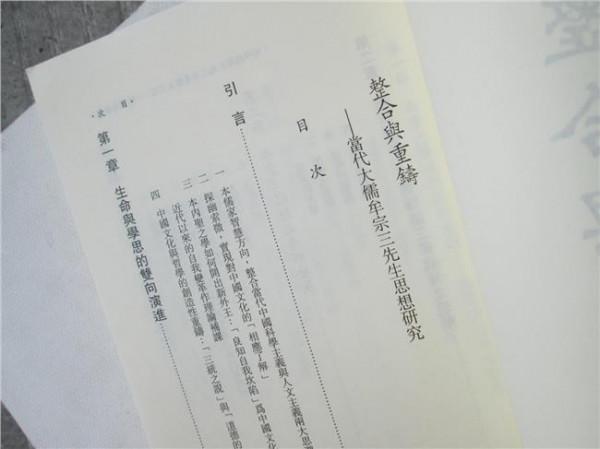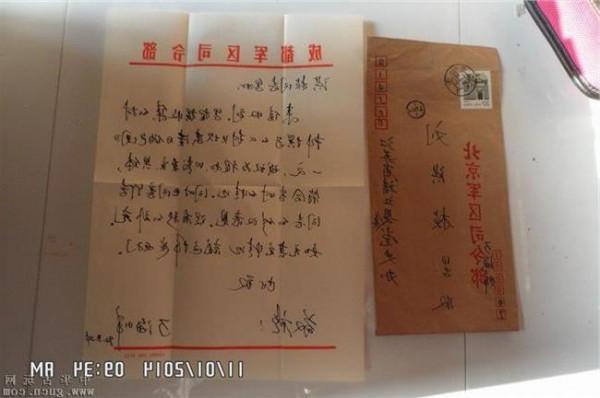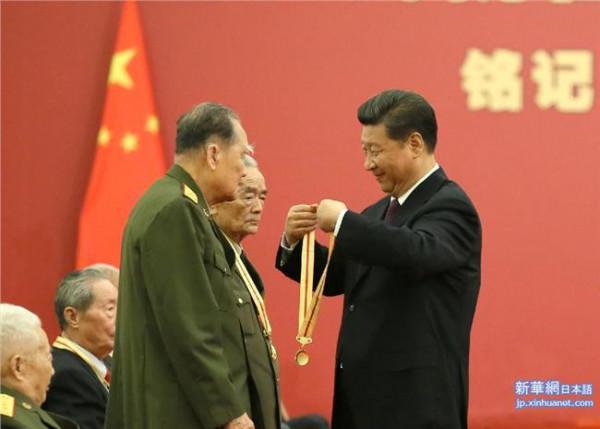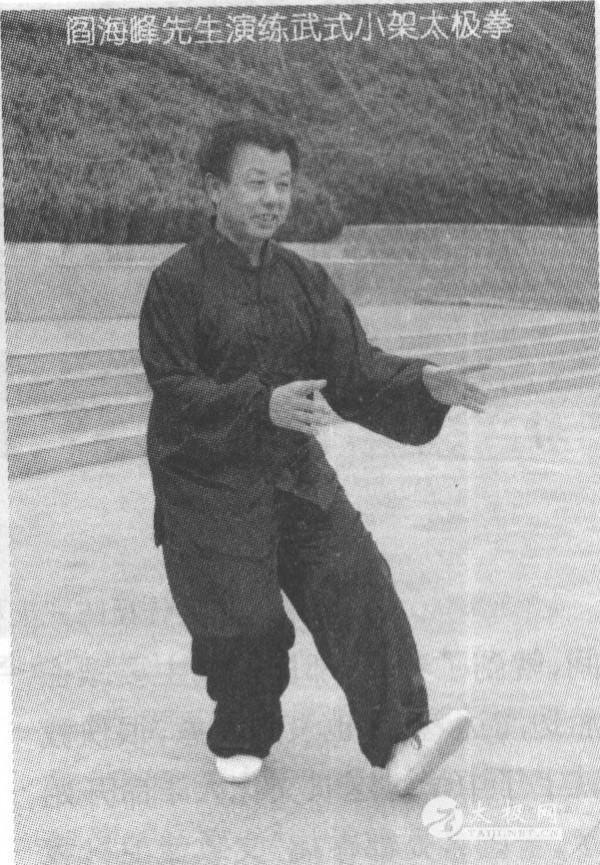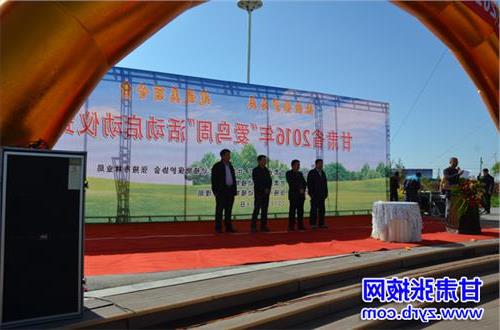牟宗三与佛教 景海峰:圆教与圆善:牟宗三哲学的核心思想
“圆教”与“圆善”无疑是牟宗三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牟复杂而深邃的宏大思想系统的最终指向和最后归宿。对于这样关键的中心思想之分析,可以从全系统撑开了来看,循着原点(“自由无限心”或“智的直觉”),从“良知的自我坎陷”入手,依“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的对列格局,抽丝剥笋,层层逼近,显现“圆教”的义旨和“圆善”的内蕴。
也可以抛开了知性领域,只从“智的直觉”所指涉的实体界(道德的实体和形而上的实体)入手,来说明“圆教”与“圆善”何为。
既可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着重从概念的联系和思想的层次脉络来推演;也可以多用一些哲学史、伦理学史的实证性事例来给予说明。总之,环绕“圆教”与“圆善”的问题,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话语路径。这里,我们只是紧紧把握住“圆教”与“圆善”这两个概念本身,从道德实体的层面作一些分析,并提出阐释性的批评意见。
一、何为圆教?
“圆教”一概念源自佛家,本是佛教徒根据佛法义理之深浅、释迦说时之先后等,将佛教各部加以剖析类别的判教说辞。教判在南北朝时代即有“南三北七”之分。十家之中,西魏统法师首立顿、渐、圆三教,对上达佛境、“说如来无碍解脱究竟”、果德圆极秘密自在的圆教做了初步的说明。
[1]延及隋唐,教判大盛,开宗立派各家无不以教判来衡准权实、判说高下、显扬自宗。在形形色色的教判理论当中,天台智顗判五时八教,立藏、通、别、圆四种和华严法藏阐释小、始、终、顿、圆五教,以及十宗,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在理论上也最为规整。
天台以圆教为佛说之极致,“一教圆,二理圆,三智圆,四断圆,五行圆,六位圆,七因圆,八果圆”。八圆归摄于理圆,所谓理圆,就是“中道即一切法,理不偏也”。
[2]此非空非有、即真即俗、不歧离于空假中圆融三谛的中道实相,即是圆照一切的最高胜境,也就是天台教判中,“但化最上利根之人”的圆教。贤首五教之判,虽将天台之圆教改为顿、圆二教,但为自家争尊胜义远大过理论上的创新义,所以就教判理论的原创性和对圆教观念的阐释力度而言,显然天台宗最为殊胜。[3]
牟宗三引证和诠释“圆教”观念,最早见于<佛家体用义之衡定>一文。这篇作为附录收入《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的长文,已明白宣示了他对天台的偏爱:
就义理之发展说,天台之判教实比较如理如实,精熟而通透。华严之判教以及其所说之圆教,是超越分解思路下的判教与圆教,天台之判教以及其所说之圆教,是辩证圆融思路下的判教与圆教,是通过那些分解而辩证诡谲地、作用地、遮诠地消融之之圆教。[4]
华严宗以《起信论》之超越分解的路数为其义理根据,如来藏统摄一切,具净染法,就净法说是既统且具,就染法说是统而不具,故要随顺众生而分解地说,需经阿赖耶识之“一曲”,此“一曲”便不是“直具”,同天台宗之性具说便大有区别。
所以牟宗三认为,只有自始不离“介尔心”的性具、理具之圆,才是真正的圆教,而华严宗层层推进、有分解地说之圆教不能算是真正的圆教。自此,“凡分别说者皆不能圆”成为牟氏构建体系、分判中西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理据,从《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到《圆善论》,从《佛性与般若》到晚年诸讲,不管是独创性的著作还是释解性的著作,这一点都格外醒目。
按照牟宗三的理解,“在诡谲的圆融下所表示的综和”方为圆教,这也是了解天台圆教的根本枢机。圆妙、圆满、圆足、圆顿、圆实、圆伏、圆信、圆断、圆行、圆位之《法华》圆十义所涵盖的天台教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约观法言,为一心三观,由此开出三眼、三智、三谛”。
明“即空即假即中”,将龙树中观思想吸纳于圆教,既不背缘起性空之基本义,又将空宗之融通淘汰精神行于圆教之中。二是“约解脱说”,为一“不断断”,预设了“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即“一念无明法性心即具三千世间法”。
所以“三千世间法皆是本具,皆是性德,无一更改,无一可废,无一是由作意造作而成”。三是“约佛果言,即为法身常住,无有变易”,体现了圆满。[5]由此,牟宗三强调只有天台宗达致了“存有论的圆”,是真正的圆教。
此圆教最接近于空宗,但又不同于空宗的无系统相,超越了般若之“妙用的圆”,而形成一系统。“唯此系统又不是分解地建立,故既与讲阿赖耶缘起者不同,亦与讲如来藏缘起者不同”,[6]故为综和的圆成,也是最后圆满的消化。
关于天台圆教的模式,牟宗三归纳出了五点:“(1)于一切染法不离不断,于一切净法不取不着。(2)法性无住,无明无住。(3)性具三千,一念三千,法门不改,即空假中。
(4)性德善,性德恶,法门不改,佛不断九。(5)性德三因佛性遍一切处,智如不二,色心不二,因果不二,乃至种种不二”。[7]此五义成圆教之圆、实、满、遍。圆则无偏,实则无虚,满无倾侧,遍无遗漏。此“曲线诡谲的智慧”可以说是代表了圆教的最高典范。
牟宗三不厌其烦,以浩大篇章诠解天台宗义,彰显其圆教性质,目的全在解决“智的直觉”一大关键问题。检视其学思历程,早年所受逻辑实证论之影响在40年代即已稍然消退,这一方面固由于熊十力的启发和感召,另一方面逻辑公理系统确实无法解决人生困惑的问题,于所究心之“道德主体”也了不相涉,所以由“认识心”(知性主体)向“智的直觉”(道德主体)的理论转向必然要发生。
50年代,是牟所谓“吾之文化意识及时代悲感最为昂扬之时”,[8]现实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这一转向的体系建构之进程。
所以当60年代牟浸润于先儒文献之中,试图借鉴西哲,尤其是消化康德,以为儒家道德理想建立一新的本体系统之时,这样的基本问题才赫然浮现在他的思虑之中:究竟什么是道德主体?道德主体的依据是什么,基础何在?道德主体性如何认识、把握、证成?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对中西的比较,牟宗三最终抓住了“智的直觉”这一枢机。
认为理解中西哲学之差异,肯认中国哲学之独特价值,特别是护罩住儒家道德义理的辉光而不至于在现代社会被完全遮蔽掉,端在此一理念的阐明。他说:
无论儒释或道,似乎都已肯定了吾人可有智的直觉,否则成圣成佛,乃至成真人,俱不可能。……如若真地人类不能有智的直觉,则全部中国哲学必完全倒塌,以往几千年的心血必完全白费,只是妄想。[9]
所以,诠释和证成“智的直觉”就成为牟宗三后期全部哲学的基础。作为证明“智的直觉”之可能的一种标示性方式,牟宗三特别致力于对圆教的说明,圆教的面目清楚了,“智的直觉”也就得以证成。“若不能将此典型之圆教展露明白,‘智的直觉’之真实可能即不能透体露出”。“故须详展一圆教典型以明‘智的直觉’之实义”。[10]这就是他偏好天台宗,花费巨大心血在这上边的根本原因。
当然,牟宗三所说的圆教,不限于天台,更不止于天台,只是天台宗特别典型,着笔较多面己。就广义言,中国哲学儒释道各家均属于圆教;论道德主体的挺立儒家圆教更在天台之上。早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牟即以“圆教”与“圆境”概念来范定和阐明孟子的道德精神主体,谓“夫圣人,人伦之至,圆教固其宗极。
而迷离惝恍,悟此圆境,本非难事。圆境既悟,说空说有,说有说无,亦为极易之联想”。[11]整部《心体与性体》可以说都是在讲儒家的圆教,《圆善论》更是将儒家之圆教推至宗极:“圆教种种说,尼父得其实”。
只不过儒家之圆教入手与佛道不同,也不是天台宗那种“诡谲的圆融”之方式。它是由道德意识入手,道德意识即是一“自由无限心”,亦即“智的直觉”。
牟宗三把儒家的这种方式称为“道德创造之纵贯纵讲”,即“圆境必须通过仁体之遍润性与创生性而建立”。儒家之称圆教,亦因其道德实践“能启发人之理性,使人依照理性之所命而行动以达至最高理想之境”,故为教。
[12]同样,道家也是一圆教系统,“亦有圆教之理境”。[13]和中国哲学之儒释道三家相比,西方哲学恰恰不具有这般圆教的品格,其主流思想都是走“分解的方式”之一途,不论是英美式的经验实在论,还是德国式的先验唯心论。
所以牟宗三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甚至认为英美哲学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哲学问题”,因而对哲学“无正面的贡献”。这种惊世骇俗的判言,背后所依据的就是圆教理论。按照圆教的思路,在牟氏的新教判中,西方哲学理所当然地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中国哲学重又矗立在九霄云端。这一与时论相悖的判词正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