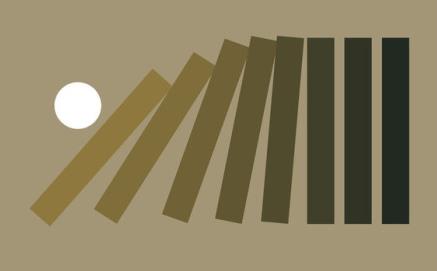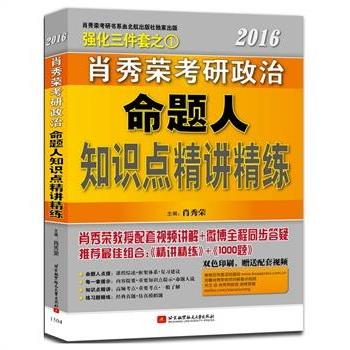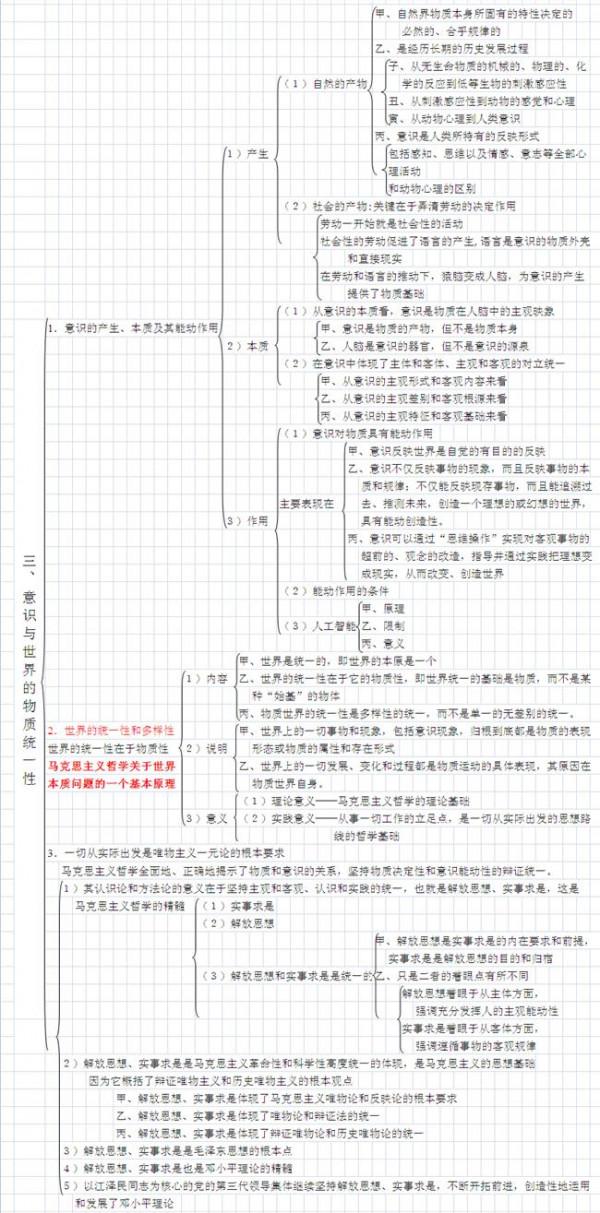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主体的变化
五四运动留给现代中国的精神遗产,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这一运动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与延续至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但只有经过五四运动才开始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并在与其他思潮竞争中成为主流思潮。

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一大转折点。这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一点,就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四运动前的20年间,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思想世界有了最初的传播,这时的传播主体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这些人物无一是马克思主义者。1899年,马克思的中文译名第一次出现在《万国公报》所刊译文《大同学》中,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在文中被称为“安民新学之一家”,这说明当时的中译者多少看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今天的人们往往将这篇译文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思想世界的开端标志。但不论文章的原作者英国社会学家企德(Benjamin Kidd,又译颉德),还是文章的中译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早期报人蔡尔康,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进入20世纪后,一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如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培、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传播马克思主义。
这些人物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非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共同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是作为一种学理介绍,至多是部分地吸取其思想,而不是作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
1915年伊始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影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其中将“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并列作为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原因、思想起源与政治诉求,谈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由思想到运动的贡献,称:“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
”但是,陈独秀在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只是针对西方近世文明弊端而论,并不是主张在中国也立即加以实行。因此,他在五四运动前大力倡导的只是“科学”与“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以1919年1月出刊的第5卷第5号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为标志的。这时的李大钊,尽管已经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呐喊,但他对于世界历史大势的认识,还是基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形成的民彝史观,而不是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他说:“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这里所说的“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也就是他所尊崇的“民彝”,即人民大众自身存在的向善本性与合理追求,这与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上革命发生原因的理解是不同的。
只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李大钊才最终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由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撰写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于1919年9月和11月相继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较准确、较系统的阐发,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自李大钊开始,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从投身这一运动的新青年中,走出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物是革命志士,他们经受了五四运动的锻炼,决心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用革命的手段开辟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些人物又是知识精英,他们往往既有相当厚实的旧学功底,又有在新式教育中所获得的西学新知,其中不少人还有到国外求学的经历,对新思想新学理的追求与探索是他们的文化性格。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为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优秀人物。
作为革命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批新青年追随响应,发起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中一些人以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学问家,他们为这个党、这个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奠定了哲学基础,使这个党、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起来,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进程。
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称得上开天辟地、前无古人。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就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换与更新,由马克思主义者取代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当年亲历这一段历史的毛泽东对此作了回顾与总结,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在这里,他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作用。
由于主体的转换与更新,由于这些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人物同时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与思想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五四运动前所不曾有过的新特征、新形态、新气象。
首先,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作为一种学理介绍,或者只是从中作部分的思想吸取,而是理解为学理与信仰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就已自觉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深受南陈北李影响的蔡和森与毛泽东,通过法中两国之间的书信往返,富有远见地提出并探讨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问题。
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这就使得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书斋里的学问,不再只是一种仅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的理论,而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是一个有思想、有理论、有哲学基础、有奋斗理想的革命党,与旧式起义的农民、近代的资产阶级政党明确地划清了界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征、形态和气象,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主义、自己的哲学时所赋予的品格:“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其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那就必须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革命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明确提出的,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这个问题就已引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探讨。特别是1923年春夏之交,联合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讨:李达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主张“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来讨论一番”;陈独秀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讲演,其中专门探讨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的问题;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中,强调必须“认清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认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
这些思考和探讨在中共三大上成为了全党的共识,用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的话说,就是“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由此而有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和1925—1927年的大革命。
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缺乏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的这些思考和探讨还存在种种不足,以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但他们毕竟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那种以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照抄照搬马列本本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看法,实是对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探索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
再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扬了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以自己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发奋的研究工作,着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专门性阐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批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一个总特点,就是对唯物史观作了多维度的阐释,使中国人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李大钊著《史学要论》和《史学思想史》,从历史学视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发;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研究;杨明斋著《评中西文化观》,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李达著《现代社会学》,综合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瞿秋白著《社会哲学概论》,则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理解,由唯物史观扩展为辩证唯物主义,首次在中国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说。
正是这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活跃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李大钊牺牲后,鲁迅就曾对他的著述作过高度评价,认为:“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只是由于这些年来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遮蔽,他们的学术成就未能得到应有的研究和中肯的评价,以致人们只看到他们革命家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学问家的一面,错误地把他们当作是一代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物。
最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人数不多、力量弱小,不仅遭到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而且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挤压,但他们却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正义性,以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无畏的理论勇气,敢于同其他思潮进行激烈的竞争。
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掀起的一阵阵轩然大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韬光养晦、躲风避浪、失语失声,而是直面论敌、勇敢迎击、据理力争。对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同仁,他们不怕思想分歧,李大钊首先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对于国内学术界的大人物,他们敢于进行论战,李达年仅30岁就写出了批判梁启超假社会主义的名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对于西方来的世界级大哲学家,他们也不盲目迷信,陈独秀就写信给来华讲学的罗素,告诫他不要在中国发表“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言论,“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新文化运动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想争论,如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无政府主义问题论战,都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参与,都留下了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和声音。
毛泽东曾深情回忆这些峥嵘岁月,赞扬李达就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李逵和鲁迅,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
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正是通过这些激烈的思想竞争,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和理论力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赢得了群众,争取了青年,成为了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思潮。
总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所呈现出的这些新特征、新形态、新气象,都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新主体直接相联系的。换言之,正是有了这一新主体,所以才有了这些新特征、新形态、新气象。正是这样,研究这个特殊的群体,研究他们革命与学问相交织的人生,研究他们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个性化努力和共同性奋斗,研究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怀抱的“初心”,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中吸取在百年后的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都是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的工作。
[作者简介]李维武(1949- ),男,安徽合肥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