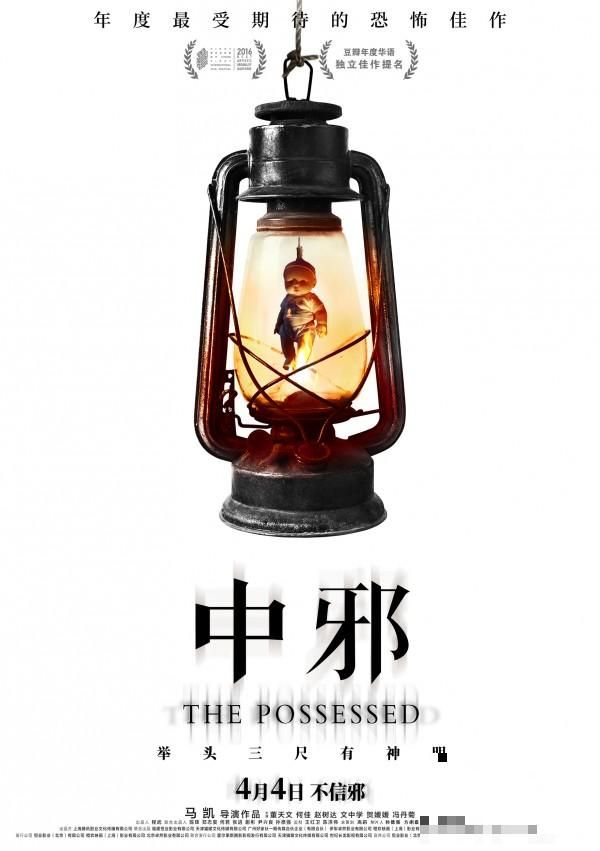肯尼迪遇刺瞬间照片 谎言之躯:特朗普解密肯尼迪遇刺档案
高度保密、充斥着专业术语的档案资料,显然无法满足公众投射在肯尼迪遇刺案上的饱含猎奇色彩的窥探欲。对肯尼迪之死的反复咀嚼已经无关真相,而是各色人等推演和展示其固有成见的宣传阵地。

神话与悬疑
这一次,《纽约时报》、TMZ(著名娱乐新闻网站)以及奥利弗·斯通终于不必再指责唐纳德·特朗普了。相反,他们应该感谢“推特狂人”那颗富于八卦气质的心脏——10月25日,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飞往1963年那起离奇刺杀案的现场达拉斯途中,特朗普发送了一条推特:“大家期盼已久的肯尼迪档案明天就要解密了!真有意思!”那一刻,总统的心理状态俨然就是一个刚刚抓拍到了香艳镜头的“狗仔”娱记。

是的,2800余份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机密文件将在10月26日晚间由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通过互联网对外公开。这是特朗普基于国会1992年10月26日通过的《肯尼迪总统遇刺记录存档法案》做出的决定,也是他对自己竞选期间承诺的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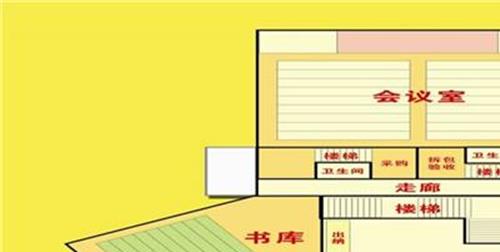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关于那场众说纷纭的奇案,至少在档案学上早已没有多少“曝料”空间:到今年秋天为止,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31.9万份、500万页厚的政府记录已经有88%全面对外公开,另外11%也在经过情报机构的部分涂黑处理后陆续解密;而特朗普下令“除去面纱”的,只是这批庞杂文牍中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1%。

它们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在古巴、南越和多米尼加实施秘密行动的收支账目,联邦调查局(FBI)对刺客奥斯瓦尔德的粗略背景评估,以及多位CIA和FBI负责人涉及案件调查的内部谈话速记。
自然,情报机构依旧会跳出来宣示他们的“主权”——大约有300份文件在CIA和FBI的抗议之下,获准进行6个月的额外审查,但最迟在2018年4月26日也须确定最终的公开时间。很难想象在特朗普可以“任性”解雇FBI局长的今天,情报机关还能在故纸堆中藏匿什么惊天大秘密。
无须怀疑,没有人会逐字逐句地读完这500万页记录。有关肯尼迪之死的种种假设和臆测,也不会随着最后1%档案的解密而告一段落。在美国,“肯尼迪热”首先是一个传播学事件:这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战争英雄、天主教徒,在电视时代蓬勃兴起之际登上政治舞台中心,享受到了此前的历任总统从未体验过的高频率曝光和偶像式待遇。
从1960年大选期间和尼克松的辩论直播开始,总统及其家人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的个人形象和治国方略被牢牢捆绑到了一起。
当人们谈起“新边疆”和登月计划时,自然也会联想到JFK(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首字母缩写)发亮的古铜色皮肤、骄傲的少年气质以及演讲中斩钉截铁的口吻。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坚定立场,和第一夫人杰奎琳时髦的发型、服饰一样都是坊间热议的焦点。
甚至当第一夫妇的幼子帕特里克不幸夭折时,全国民众像他们一样表达了哀痛之情。因此,在达拉斯的枪声响起之后,三大新闻网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连续70个小时不间断地转播与总统的后事有关的一切新闻,包括身着血衣的杰奎琳的一举一动、白宫中的守灵之夜、继任总统约翰逊的演讲,以及92国代表陪伴下的庄严出殡。
这一纪录直到2001年“9·11”事件后才被打破。
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下,整整一代人在他们心目中建立起了“永志不忘”的心理暗示。出生于“婴儿潮”前期的美国人,几乎每一个都能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在1963年11月22日听到那则突发新闻时的心理感受,这一现象甚至催生出了一个专门的术语“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以描述伤害性的突发事件在一个庞大人口基数中造成的集体印象。
不仅如此,JFK的亲信顾问、与他私交甚笃的媒体人以及他的家族成员在随后若干年中对所谓“肯尼迪时代”的建构,直接造就了影响延续至今的卡美洛神话(Camelot Myth)。其中的代表作即是JFK的演讲撰稿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在1965年出版的《一千天:JFK在白宫》。这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描绘了一幕转瞬即逝的光荣悲剧:如亚瑟王一般的肯尼迪勇敢地守卫属于美国人民的卡美洛王国,却在短短1000天之后惨遭杀害。
通过这种渲染,公众愈发自视為刺杀案的“共同被害人”——那个与肯尼迪之名联系在一起的“美丽新世界”,那段美苏关系正在缓和、对越南的干涉尚未扩大、民权运动和理想主义蓬勃兴起的动人时光,随着神秘枪手射出的三颗子弹戛然而止。
随之开启的是关于林登·约翰逊和迪克·尼克松的丑陋记忆,是底特律骚乱、金牧师遇刺、将近6万人战死于越南以及水门事件。
因反差感导致的过激情绪,最终以阴谋论的方式获得宣泄:人们倾向于相信,是一个权势滔天的黑暗阵营谋害了那位年轻的王子。这个阵营中包含有副总统约翰逊及其南方同伙,中央情报局和他们雇佣的古巴枪手,脑满肠肥的军工联合体(MIC)代表,以及参与案件调查的司法官员。他们的势力长存,以至于真相一路被掩盖至今。
和传统阴谋论者站在对立阵营的那个群体则以祛魅者自居。他们试图论证:从来也不存在一个以肯尼迪命名的黄金时代;相反,那位年轻总统身上的道德缺陷和他层出不穷的施政失误,每一样都足以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在政治生涯前期,肯尼迪曾经受惠于他的家族与帮派势力以及麦卡锡参议员之间的私谊,随后却对此讳莫如深。
他一度汲汲于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但在猪湾入侵时出尔反尔,自此与整个情报系统反目。他是推翻南越吴庭琰政权的幕后决策者,政变、阴谋和暗杀被他当作常规政策加以采纳。
甚至连遇刺案件真相的扑朔迷离,也被解释为肯尼迪本人咎由自取——长期以来,为了掩盖总统不良的健康状况和混乱的私生活,白宫实施了一系列信息封锁和欺骗措施,最终为其所反噬。但主张“咎由自取说”的这派人士,同样无法将现有的证据串联成具备充分说服力的逻辑链,因之只是滑向了另一种阴谋论、进一步淆乱了舆论场而已。
肯尼迪总统与第一夫人杰奎琳在达拉斯,这是遇刺前不到一小时的照片
截至2017年,美国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出版物累计已经超过了4万种,却没有任何一种足以令大多数人信服。当对奇案的反复咀嚼成为生财之道后,任何新信息的加入,都不过是给这锅浓汤添进了新佐料。死者已矣,生者关心的首先是自己能从中榨取出多少“剩余价值”;毕竟,这已经是一盘千万美元级的生意了。
枪手与子弹
2016年造访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时,位于胜利广场拐角处的一幢公寓楼引起了我的注意。本地出版的导游手册专门有一页记载:1961年前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及其新婚妻子曾在这幢奶黄色小楼三层的一个单间居住,当时他是“地平线”无线电器材厂仅有的一名外籍员工。手册同时还配上了奥斯瓦尔德60年代初的照片:墨镜、花格衬衫、羊毛夹克,在一群灰头土脸的苏联工人中显得相当洋气。
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指出了事情的反常之处: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最终抵达达拉斯之前,不止一个人曾经预测会有极右翼分子对总统采取攻击行为,但谁也没有料到真正开枪的却是一个极左分子(至少表面上如此)。
但此人又远远称不上老谋深算:除去50年代后期在海军陆战队练成的一手好枪法外,奥斯瓦尔德的一切举止都显得笨拙而不合常情,既不像合格的谍报人员,也不具备阴谋家的素质。
1959年,他曾在莫斯科的酒店中割腕自杀,以显示自己对“精神祖国”俄罗斯的忠诚,这才获准取得政治避难资格。但到了1962年,当奥斯瓦尔德已经在明斯克得到一间不错的公寓、享受着和同事相比明显高出一筹的收入和生活待遇时,却又为了博取关注而决定迅速返回美国。
有怀疑主义者认为,这个无厘头叛逃者的行为是受CIA指使,但过程中的细节显然违背了谍报工作的一切法则——甫一抵达莫斯科就把自己搞成了新闻人物,但又没能获得苏方的充分信任,也始终学不会俄语。CIA会需要如此不专业的一线雇员吗?
10月26日公布的最新一批档案,还揭示出苏联之行给奥斯瓦尔德留下的其他印记。在暗杀行动之前一个多月,1963年9月28日,此人曾出现在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要求领事科斯季科夫(另一个身份是克格勃官员)帮助他取得访问古巴和苏联所需的签证。
10月1日,奥斯瓦尔德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的警卫,询问办理进度,他那蹩脚的俄语被负责监听电话的CIA探员识别了出来,并做了录音。10月18日,古巴使馆在苏方的建议下批准了奥斯瓦尔德的签证申请,但他并未立即成行,而是掉头返回了常住地达拉斯。11月11日,奥斯瓦尔德最后一次致函科斯季科夫,宣称:待不久后他抵达哈瓦那之后,将与苏联外交人员做进一步交谈。
冒冒失失找上门去,毫无保密意识地用电话和信函联络苏方外交官,符合奥斯瓦尔德的一贯人设:交际能力低下,心血来潮,渴望制造“大新闻”。鉴于1959年那次叛逃远未收获他臆想中的轰动效应,这位不甘寂寞的神枪手现在又企图进入敏感地区古巴,期盼哈瓦那当局以及背后的莫斯科能重新重视他的价值。
某位美国大人物的性命或许就是他预备交出的“投名状”——1963年4月10日,奥斯瓦尔德曾闯入美国陆军退役少将埃德温·沃克位于达拉斯的家中,试图暗杀这位以激进反共著称的军人,但在匆忙中未能击中目标。
他随后逃之夭夭,一直未被逮捕。直到肯尼迪死于非命之后,警方才确认:击中总统的子弹和7个月前在沃克家中找到的弹头发射自同一支步枪:奥斯瓦尔德在当年3月邮购的6.5毫米口径卡尔卡诺M91/38型卡宾枪。
沃克案件的延迟告破,实际上已经挑戰了后来阴谋论者的一项揣测:奥斯瓦尔德是被有心人故意“遗忘”在可以俯瞰总统车队的位置上的。事实证明,尽管FBI达拉斯分局早已将这位有叛逃记录的军人列为重点监视对象,但他们投入的人力从未达到充足程度,对奥斯瓦尔德的危险程度也估计不足。
这位算不上老练的枪手在9个月时间里不紧不慢地配齐了武器,尝试了一次不成功的演习,还和苏联人、古巴人以及亲卡斯特罗的民间组织“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PCC)进行了公开接触,而FBI和CIA只在几个孤立的场合捕捉到他的踪迹,从未将所有这些信息拼合成面。
由此观之,日后情报机关竭力要求将案件调查资料长期封存,掩盖自己“黑手”角色的可能性倒还在其次,更大的概率是使自己的监控漏洞不至于暴露,而为苏联所乘。
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在被捕两天后死于达拉斯的警察局
无论如何,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当肯尼迪夫妇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夫妇乘坐的敞篷“林肯”牌轿车驶过达拉斯市中心的埃尔姆街时,奥斯瓦尔德就举着他那支价值19.95美元的卡宾枪,站在街道右侧教科书仓库大楼六层的窗口。
对沃克少将的行刺失败之后,这位神枪手特地花7美元购买了一支日本产的高倍瞄准镜。第一发子弹击中了路边,碎片飞溅到一位目击者的脸颊上。接着,12点30分30秒,第二发子弹从背部打穿了肯尼迪的脖子,从他的喉咙下方穿出后又钻进了前方的康纳利州长体内,击伤了后者的右胸和右手。
由于总统佩戴着矫正长期背伤用的支架,他在被击伤后没能及时趴下,此时第三发子弹恰好从正后方打进他的后脑,鲜血、脑浆和头骨碎片顿时溅满了整个车厢。这也是致命的一弹:当车队紧急驶入附近的帕克兰纪念医院时,肯尼迪已经身亡。半个多小时后,遗体被抬上“空军一号”专机,飞返华盛顿。
尽管穿入后脑的子弹造成肯尼迪死亡一事已无疑问,但因为第一发子弹的弹头始终没有找到,调查人员的意见很快出现了分歧。负责现场勘查的FBI在事件发生后第17天整理出了一份初步报告,认定三发子弹都击中了汽车,其中第一弹和第三弹命中肯尼迪,第二弹命中康纳利,但第一弹的弹头丢失。
而由新总统约翰逊任命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以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为主席)在1964年9月27日发布的报告否认了这一推断,理由是:经过对奥斯瓦尔德所用步枪的试射,证实这支旧式卡宾枪精确射出两枚子弹所须的最短间隔时间为2.
25秒。但从现场目击者亚伯拉罕·扎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用家用摄像机拍下的26秒长的视频画面分析,总统背部中弹和康纳利被击中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缺乏必要的间隔。
因此给两人造成非致命伤的是经过多次折射的同一发子弹。报告同时还认为,奥斯瓦尔德的行动纯属个人行为,与苏联和古巴政府无关,也没有受到美国情报机关、政府部门或任何团伙的指示,只是一个“精神不稳定者”实施的偶然犯罪。
一发子弹造成两人受伤的推论,也被称为“魔术子弹”理论(Magic-bullet Theory)。由于其不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自公布之日起就受到广泛抨击和质疑。不止一名目击者宣称,在专车前方的草丛附近还有其他身份可疑的人出没,也许就是和奥斯瓦尔德配合的第二名枪手。
1969年,司法部长克拉克组建的一个医疗专家小组对“魔术子弹”理论表示了附和。但到了1979年,当众议院组建新的特别委员会重新检视案件的调查证据时,一种新的可能性被提了出来:“魔术子弹”理论依然成立,但“有很大可能”现场总共存在两名枪手:奥斯瓦尔德开了三枪,另一名藏在草丛中的刺客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目标。
委员会同时再度确认,苏联和古巴、FBI和CIA都与暗杀行动无关,但多个政府部门在保护总统时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并且不能排除极右翼团体或犯罪组织的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卷入了暗杀。
最终,委员会得出结论:“基于可获得的信息,本委员会相信肯尼迪总统可能死于一场阴谋。但委员会无法确认阴谋的内容,或者可能存在的第二名枪手的身份。”这个模棱两可的表态等于承认沃伦报告的判断存在严重缺陷,立即成为诸多阴谋论者趋之若鹜的对象。
肯尼迪被枪杀后两小时,副总统林登·拜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中)于空军一号飞机上,在肯尼迪夫人身旁宣誓就任总统
“真相”重要吗
1991年,由知名反战人士、以政治观念左倾而著称的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JFK》一举揽下2.0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并收获8项奥斯卡奖提名,美国再度为“肯尼迪热”所席卷。该片以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参与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过程为主线,提出了迄今为止知名度最高的一种解释:由于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拒绝支持CIA对古巴全面开战,同时计划逐步减少在越南的军事介入,肯尼迪成为军工联合体、情报机关和流亡古巴人社团的共同敌人。
他们在1963年11月22日的达拉斯安排了三名枪手,同时朝总统的座车开火,毁掉了JFK继续执政并争取连任的希望。军工联合体的代言人约翰逊随后入主白宫,精心扭曲和破坏了调查过程,捏造出“魔术子弹”理论等说法,并将知晓内情的奥斯瓦尔德等人灭口。
胸怀正义的加里森经过多方调查,终于发现了中情局的线人与古巴黑帮以及暗杀密谋之间的隐微联系,并对一名参与者进行起诉,但无功而返,加里森本人的前途反而因此毁于一旦。影片结尾出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字幕:根据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所有与本次案件有关的记录要到2029年才会公开。
影片主人公原型吉姆·加里森当时已经身患癌症,命不久矣。多年来他固执地相信,肯尼迪之死并非意外,甚至不止是一起政治谋杀,而是一场事实上的政变——军工联合体和情报机关勾结,杀害人民选出的总统。加里森言之凿凿地宣称,行动的直接指挥者是时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查尔斯·卡贝尔退役空军上将,因为肯尼迪曾放言称要拆分中央情报局。
暗杀开始前,卡贝尔秘密抵达达拉斯,在枫丹白露旅馆坐镇指挥;他的弟弟厄尔·卡贝尔正是达拉斯市长,知晓总统当天的全部行程以及车队抵达埃尔姆街的确切时间。
CIA雇佣的流亡古巴人团体是枪击的直接执行者,达拉斯政府、警方以及副总统约翰逊是共同谋划者。作为酬赏,厄尔·卡贝尔在1965年当选为众议员。而加里森本人因为坚持公布真相,遭到黑恶势力的诬告,在1973年被控受贿而丢掉了检察官的职位。与谋杀者有关的权势集团依然控制着美国,并且竭力阻止民众知晓真相。
自然,加里森的调查活动并不像他本人宣传的那样证据充足。他在新奥尔良的多位旧同事认为,一名被加里森当作重要证人的保险业务员佩里·鲁索由于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意识并不清醒。而加里森主张的“三名枪手”假說,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调查组的认同。
但刺客奥斯瓦尔德的死于非命,的确使整个事件充满了阴谋气息——暗杀发生后两天,当他被荷枪实弹的警察从警局押往监狱时,一名声名狼藉的当地黑帮小头目杰克·鲁比(Jack Ruby)拔枪冲上前,将奥斯瓦尔德当场打死。
而鲁比随后在法庭上宣称,自己的行动纯属遭人陷害,“那些当权的、别有用心的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人们,绝不会把真相公布于众”。1967年,鲁比患上肺癌死去,咽气之地和JFK以及奥斯瓦尔德被白床单盖上的地方一样:达拉斯市帕克兰纪念医院。
由于奥斯瓦尔德的神秘死去以及鲁比在法庭上的发言,“灭口论”很快被怀疑主义者奉为圭臬。到了1968年,当JFK的弟弟、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在加州被一名刺客枪杀之后,围绕JFK之死的阴谋论更是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有小报危言耸听地“统计”了JFK身边亲信人员以及遇刺案目击证人在1963年之后三年间的死亡率,宣称灭口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但仔细甄别即可发现,其中许多人当时并不在总统身边,而那些受到调查的当地黑帮分子,死于非命的概率原本就比正常人高出一筹。
而一些流传已久的段子,随后也被陆续辟谣。例如,不止一位目击者发现在欢迎总统的队伍中有一个打着雨伞的人,而当天达拉斯天气晴好,因此这个“伞人”被认定是给暗杀小组发信号的同谋。
但到了1978年,“伞人”路易·斯蒂芬·维特主动站出来作证,表示此举是为了抗议JFK之父约瑟夫·肯尼迪在“二战”前担任驻英大使时支持“绥靖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手持雨伞是张伯伦的著名习惯。
而宣称中情局官员、“水管工”霍华德·亨特——水门事件中的特工组指挥官——曾在暗杀现场出现的指控,则是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新谣言。1989年,达拉斯警方公布了1963年11月22日逮捕的疑似涉案人员的资料,证实那只是几个普通的流浪汉,其中从来没有出现亨特。
但《JFK》引发的讨论热潮,的确使这笔尘封的历史旧账再度被悉数挖出。为了彻底澄清政府在案件中应付的责任,1992年美国国会援引《信息自由法》,通过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记录存档法案》,决定成立暗杀记录复核小组,在未来25年内彻底公开与该案有关的一切政府档案。
在1992年当年,《沃伦报告》包含的98%内容即已向公众开放,仅有尸检照片、总统的脑部X光片等归于肯尼迪家族名下的物证仍保存在海军档案馆中。而随着最后1%档案在2017年的最终解密,很难想象在故纸堆中还能发掘出任何关于54年前那起谜案的新解释。
以“草根福尔摩斯”自居的普通猎奇者们,关心的早已不是所谓“真相”,而只是肯尼迪家族身上笼罩的传奇气息和娱乐色彩。从这层意义上说,即使最后一个被涂黑的单词也获准解密,阴谋论也依然不会消失。而肯尼迪身后的谎言、喧嚣和风波,也早已和那位英年早逝的亚瑟王本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