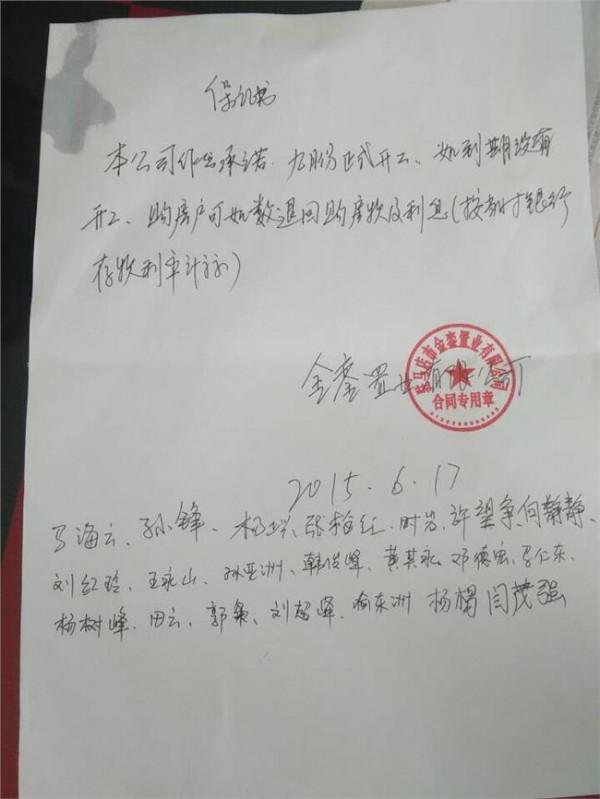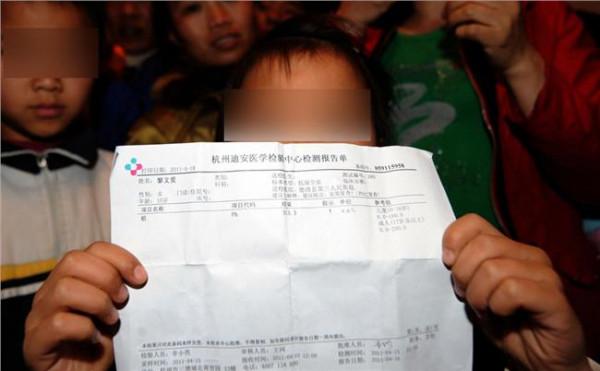我是林平之
在西湖地底漆黑湿闷的苦牢里,我已经住了很久,很久。黑暗于我是无谓的,因为我是一个瞎子。他们说,这是报应。
孤独于我也是无谓的。每天,一个聋哑的牢头会拿来两顿饭,那是这个地下世界打碎宁寂的唯一机会。除此,就只有水蛇滑凉的躯体划过地隙的声音,就只有老鼠于暗处窥测眼珠转动的声息。

孤寂与黑暗,都打不败我。在此之前很久,我的心就死了。死去的那一瞬,闽南鲜浓山花的艳丽,夺去了我的眼睛。
在我睡得那张铁床上,有奇怪的字符。我知道,那是吸星大法。那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是练此脱困的。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凡是那个人喜欢过的,我都不喜欢。

一点点都不喜欢。
我按着自己的肋骨,一根根数下去,有三根还没有生长完好,也许它们将永远破碎,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注定埋骨于此,骨头好一根坏一根,又如何?
但我知道,按碎骨的长势,再有七日,莫大先生就将下到地牢来,将我一顿拷打。也许又有几根骨头要断了。我不禁叹了口气,不明白这些大人物,为什么如此心地阴毒。

他们想要的,我早已给了他们。武功,权势,名利,流传千古的侠名。但是他们依然要将我关在这暗无天日之地,依然要疯狂拷打,并不一刀杀了我。我知道,他们需要一个人,一个明了真相的人,看他们诓骗天下的得意与骄傲。而他们,又为此恐惧羞赧。
我是他们的俎上肉,也是他们的鬼画符。
那个人只来过地牢一次,是他将我关进这里。他讲了一个江湖的故事,一个叫上官金虹的枭雄,将小李探花杀死后,埋在自己办公的地方,每天踩着生平大敌的尸骨,以此自警。
他说,我是他平生的大敌,也受过我平生的大恩,所以他不杀我,只将我埋在这波涛浩淼的地底,埋在丹青史卷的千夫所指里,让西湖清水洗不净我的污秽声名。
他说,历史都是胜利者写就的。
我不与他辩驳。作为福威镖局最后一代继承者,我有自己的骄傲。我亲手将火把丢入镖局,看它烧成白地,那是我曾祖林远图公毕生事功的象征,作为独孤九剑最纯正的传人,我要将祖上的荣耀原封入历史,不被任何魑魅魍魉觊觎染指。
我大肆放火的间歇,余沧海的一双鱼眼死死盯着我,就像我要烧灭他的什么毕生珍爱似得。这个青城山下的矮子,做了无数蠢事,但我和他居然有了奇怪的羁绊。他在青城山修炼,我在西湖底刑求,居然都和那个叫白素贞的蛇女有了联系。虽然在当时,我看着被我五花大绑在福威镖局旗杆上的余沧海满是怨毒的眼睛,并没从滔天炙焰里预料到未来。
但她确实是个如白蛇一样温婉的女子。也是她,在我将刀刃划入余沧海亲子肚腹的一刻,她的眸子里闪过一阵异彩,我仿佛看到了宇宙万星在一枚芥子里绚烂绽放的壮美,一瞬息的冲动驱使我去做个英雄。
我那时并不在意,背后一双阴鸷双眼闪过的寒光。
我离开了福威镖局,随她北上华山,彼时五岳剑派声誉日隆,嵩山左冷禅,衡山莫大,衡山定闲,泰山天门,华山岳不群,五派领袖的私人势力都已坐大,福威镖局对五岳剑派的节制越来越松动,作为独孤九剑的执剑人,江湖所有剑派的宗主,我需要压抑野心勃勃的属下们的骚动。
这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独孤九剑可以战胜敌人的掌中剑,却无法斩断爱人与朋友的心中刃。那个猥琐老迈的华山大弟子令狐冲,总是醉醺醺不像样子,在被岳不群责罚的时候,我吩咐放过了他。当陷阱向我袭来,令狐冲讷讷的试图暗示我。但谁会在意一个可怜的酒鬼呢。就这样我走进了自己的命运。
陷阱实在平庸的可笑,倾心的女子,肝胆的朋友,一点毒药,一分猜忌,就像江湖世世代代上演的故事,大侠们总是轻易掉进去,从无长进。前朝金风细雨楼楼主戚少商前辈,曾将之谱成歌谣《逆水寒》,我自小就能吟唱,却始终不能参悟其中被背叛的孤愤。
当我懂得时,劳德诺正将沾血的剑刃划过我的腿筋。
我在家乡的山谷野店初遇她的时候,伴在她身边的,就是器宇轩昂,英气姿发的劳德诺。我倾慕她,也敬重他。而现在,他们掌握了独孤九剑的秘密,我从他们身上,嗅到了一股浓重腐烂的味道,像从秃鹫的爪下抢夺腐肉的鬣狗。我皱起了眉。
她的芊芊玉指抚平了我的眉头,我一点都不怪她,恨她。只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她伴着我,并不言语一声,但心思我都已知悉。人在江湖,本该如此,不为秃鹫,便成鱼肉。
当李寻欢被上官金虹杀死时,当萧秋水被唐方出卖毒杀时,当神雕大侠在华山思过崖密洞里困死中原五绝独霸天下时,正义从来缺席,胜者就是正义。
从此,江湖就成了他们的江湖,江山任凭描画,史书任其篡写。
独孤九剑变成华山派武学的正朔,福威镖局传承的是邪恶的辟邪剑法。那种毁身绝嗣的练功法门,据说出自大内九千岁之手,林氏一族于是成为魏忠贤的余党,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清算。史笔如椽,永难翻身。
他们杀死了五岳剑派的掌门人,她杀死了岳不群,劳德诺杀掉了左冷禅,他们各自的父亲临死前想必会惊诧难瞑,但也许不会,因为他们一向就是如此被教育的。
他们囚禁了魔教任我行,扶植了一个傀儡,起名东方不败,从此一统江湖。就是在那时候,他们发现独孤九剑功法里有巨大的隐患,劳德诺将任我行囚禁在西湖湖底,逼他交出吸星大法,来化解自己的命门。他们拷打他,摧折他,用传自建奴女真部落的十大酷刑整治他,任我行顶住了。当他们决定将他的独女任盈盈嫁与华山酒鬼令狐冲时,他终于屈服了。
但任盈盈终于还是嫁给了令狐冲,这个沉溺在酒盅里的糟老头子,成为中原武林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傀儡,他被塑造成潇洒不羁宅心仁厚的武林天骄,占尽天下命望。但华山大弟子与魔教圣姑度过了一生悲惨的婚姻,他们甚至无法交谈。令狐冲浓郁的关中口音,与任盈盈的贵州土话总是格格不入。
劳德诺将我扔入了西湖地牢,抛给我一册竹简,我摸着篆刻的文字,书名叫《笑傲江湖》,这是他聚集江湖上百位百晓生的集体创作,这个大IP后来听说卖了很多钱。但我彼时疑惑的,是他们为何要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抹黑我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将自己也描画成跳梁小丑,并死于非命,是何道理?劳德诺一笑,告诉我,天下从来都是隐匿在幕后的势力掌控的,泰西之地有共济会,两千年来掌控欧陆数十国国运,其势力根深绵长,党魁鸿运高照,其信徒遂自称为小粉红。
“舞台上的无非戏子,我们要做开剧院的人。”劳德诺临走前说了一句,从此他再也未曾踏足地牢。
我没有习练铁床上他刻下的吸星大法,在我被废去经脉之后,独孤九剑的反噬之力已经瓦解。我不明白创下这套剑法的神雕大侠为何要制造这样一个命门,但也许,他只是单纯的不想后来人好过。
我就在地牢里永远住了下来。往昔的骄傲与尊严,都已离去。我是一个杀害妻子的阉人,一个心地歹毒的瞎子。那本《笑傲江湖》也说了一点真话,他们阉割了我,毒瞎了我的眼睛。木高峰与余沧海在最初的计划里,是作为弃子赢取我的信任。当天下已定,仿佛作为某种偿还,木高峰被刺聋双耳,割去舌头,永远在地牢与我为伴。
而余沧海,在一把大火里,与福威镖局一起灰飞烟灭。是的,我并没有亲自烧掉福威镖局,那把火,是胜利者才有资格放的,而我只能在梦里。所有与《笑傲江湖》相悖的真相都被抹去了,即使一时抹不去的,也会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消解。
劳德诺说,他的胸怀是天下权柄,而不是一个江湖。未来,他与他的继承人们会扶植女真,逐鹿中原,待主宰江山,势必大兴文字狱,以举国修书为名取缔天下禁书,篡改笑傲真相,指鹿为马,信口雌黄,让天下人且愚且懦,大丈夫纵行于世,岂不快哉。
劳德诺说,他要做一个独夫,称孤道寡,高处不胜寒。
劳德诺说,他杀死了她。“让历史更真实一点。”
劳德诺说,“没有了,从此世间再无劳德诺。”
我的心底一片平静,掌心冰凉,却无哀伤之色,在华山之巅,她将七星海棠点燃的那一刻,我的心就死去了。毒烟熏瞎了我的眼睛,我察觉她是有意为之,不愿再与我四目以对。她总是有一分歉然的。
她的手指在我的眉宇间摩挲,一点点熨平了我心中的块垒。我感到她伴在我的身边,轻轻的叹息,对我说:“你这又是何苦?”
我露出了平生最完美的一个微笑,如闽乡春天里遍野盛开的山花。在她触到我眉心的一瞬,我运起残余的功力,将独孤九剑的命门转入她的经脉。从此,她只能眼睁睁看着神功在手,却无法运用。
在她距权力最接近的一瞬,我永恒的阻绝了她的欲望。
劳德诺杀死她的时候,其实她早已被我杀死了……
“姊妹,上山采茶去……”闽南柔婉的山歌在华山陡峭锋锐的山壁间流转,一个俊俏的身影轻盈跃动在山溪花草间,清瘦的后生缀在不远处,眼神脉脉着随行。那时天穹朗阔,白云如衣,少年人如诗的怀抱,看世间无一处不澄澈透亮。而那终究是一个梦。
我的视线一点点漆黑下去,永远的黑下去。最后,我终于失去了她。